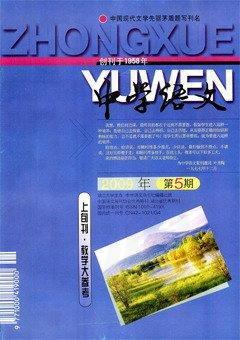淺論寫作中真實與虛構的和諧統一
馮齊林
我們知道,寫作中存在著兩種真實:生活真實和藝術真實。所謂生活真實,即社會生活中實際存在的、我們用眼睛看到的、用耳朵聽到的一切生活現象。它既是真實的,也是雜亂、無主題、表面化的。如果寫作照搬現實,它就成了一本大賬簿,粗糙不堪。寫作要對生活去粗取精,提煉虛構,從而達到藝術真實。藝術真實的真,不是與生活一模一樣的真。藝術的美,就在那“似與不似之間”。可以說,虛構是生活真實向藝術真實轉化的中介。因此,寫作的創造性就在于虛構。
生活是源泉,離開生活就沒有寫作。虛構是建立在生活真實基礎之上的。只有占有豐富的現實生活的材料,并對其進行提煉、加工、升華,才有可能寫出好的文章來。真實是寫作的生命,但事事皆實,會失于平庸;虛構是寫作的本質,但事事皆虛,會過于誕妄。可見,在寫作中,要做到實者虛之,虛者實之,實在是大有學問。那么,怎樣才能處理好真實與虛構的關系,寫出最美的文章?
一、體驗真實,合理移情
葉圣陶指出:“生活就如泉源,文章猶如溪水,泉源豐盛而不枯竭,溪水自然活潑地流個不歇。”生活中的世相性情、生活情趣、滾滾紅塵、尋常巷陌等等都可以成為我們思想的載體和心靈的感悟,都可以成為寫作的素材。寫作的方式取決于作者的生活方式。有什么樣的生活方式就有什么樣的寫作內容。我們要以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靈去觀察生活、理解生活,并且隨時把眼前所見、腦中所想用自己的筆記錄下來。我們不但要記錄生活的向陽面,而且也要敢直面生活的陰暗面;不但要看到瑣碎生活的表象,而且也要透視其間的真諦和本質,做到我手寫我見。作家的創作也都是以真實的現實生活為基礎的。托爾斯泰創作《戰爭與和平》時,特意到當時的戰場上考察。他自豪地說:“我的小說中歷史人物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有根據,不是虛構的。”我國古典四大名著、魯迅的小說也都來源于現實生活。對生活的真切感受,是取得真實性的主觀條件,是寫作的基礎和出發點,是使讀者產生情感共鳴的前提條件。
生活真實上升為藝術真實,還需要作者情感的真實投入。情感具有一種推己及物的功能。錢鐘書先生在《管錐編》中指出:“史家追敘真人真事,每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幾入情合理。”在寫作時,我們的思想情感一旦為某一對象所激活,就會誘發無窮的想象。在想象所虛構的世界之中,我們會把自己想象中的人物或事物都看作真實存在的,并對他們傾注自己全部的感情。“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與他們同悲苦,共歡欣。
福樓拜的書信中曾有一段話談及他寫《包法利夫人》的經過:“寫書時把自己完全忘卻,創造什么人物就過什么人物的生活,真是一件快事……我騎馬在一個樹林里漫游,正當秋天的薄暮,滿林都是黃葉,我覺得自己就是馬,就是風,就是他們倆的甜蜜的情話,就是使他們填滿情波的眼瞇著的太陽。”只有在寫作中和自己筆下的寫作對象產生了感情共鳴,才能作大膽的嘗試,逼真地描繪人物情狀,寫出人物思想感情的真實,內心世界的真實。
二、細節真實,創設情境
巴爾扎克說:“在細節上不是真實的話,它就毫無足取了。”細節描寫直接關系到作品反映生活的真實性和典型性。這就要求作者在寫作中,無論寫人、敘事、繪景、狀物,都能借助富有表現力的藝術語言,凸顯細節。例如,施耐庵寫《水滸》里的時遷時,就曾故意把銀子放在梁上,而他自己則暗中觀察真正的賊偷銀的全過程:先學了幾聲老鼠叫,接著像跳蚤一樣往梁上一躥,便偷走了銀子。施耐庵抓住了這些行竊的細節才塑造出了一個具體生動又真實可信的活靈活現的“鼓上蚤”形象。但是我們還要注意,細節如果不符合生活常識就會給人以胡編亂造的虛假感覺,會讓人反感。例如,湖北鄂州市某一考生在中考作文《琴聲感動我心》中寫道:“我沿著聲音的痕跡,來到了一間破舊的小屋前。……‘爺爺,我累了。彈琴真快樂,雖然我看不見,但也可以用心去感受,是么?一個蒼老的聲音:‘是的,你彈得十分動聽。我看見你的手指多么靈活,就像在那琴鍵上跳舞一樣。……是一位盲人!而那位坐著的老人竟是位聾人!我的心再次被深深地感動著……”試想,一間“破舊的小屋”放著一架鋼琴,“聾人”能聽見聲音,這可信嗎?不令人反感嗎?所以,文章中的細節一定要真實,一定要合情合理,要符合人們的認識習慣和規律。這就是與實際生活相符合的真實性。
細節的真實具有符合生活真實的特征。然而,還有一種違背生活真實的細節和情節,其時空、環境及人物關系的設定也是荒誕的,卻并未損害作品的藝術真實。如:《聊齋志異》里的鬼魅狐妖,卡夫卡《變形記》中的人變甲蟲,杜麗娘死而復生,竇娥三誓……這些現象在現實生活中絕不可能發生,然而卻能使讀者彌覺其真。為什么呢?因為它服從于一個假定的邏輯,經得起推敲,讓人感到它的前因后果能自圓自洽。
對作品來說,藝術真實體現為一個獨立的、統一的、自洽的文本世界。寫進文章中的亦真亦假的內容經過形式的改造、加工,獲得了真實的生命。
在寫作中僅一味強調“真實”,杜絕“虛構”,把“虛構”一概看作胡編亂造;或者擔心“虛構”會導致“捏造”,會形成“假大空”文風。我認為這種強調是片面的,這種擔心是多余的。絕大多數文章總是或多或少摻雜著虛構的成分。“完全是真實的照搬,也可能‘假;完全的虛構,也可能‘真”;“虛構不一定虛假,真人真事也不一定‘真”。
總之,文本的真實性不在于它的事實性,而在于它的邏輯可能性。為了取得以假為真的效果,可以通過想象,借助比喻、夸張、擬人等藝術手段,虛構一個符合邏輯的藝術情境,使筆下的人物生活在這個虛構的生活圈子里。人與人之間的矛盾關系及事情發展的結局等等也得以一一呈現。盡管它可能與生活實際極不相符,但這時,因為文章本身具有了一個自足的藝術結構,一種固有的假定的真實性,正所謂事之所無,理之必有,從而達到藝術的美與藝術的真的和諧統一,讀起來也就真實可信了。
[作者通聯:湖北鄂州市華容區臨江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