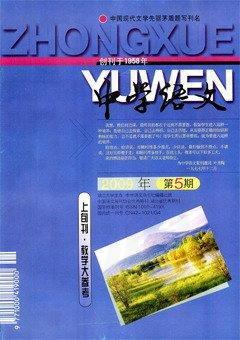“桃花源”里尋“美”
侯麟耀
李澤厚在《美學四講》的審美形式中提到,美有三個層次,最低層為“悅耳悅目”,接著為“悅心悅意”,最高層為“悅志悅神”。以下結合《桃花源詩并記序》談三步解讀。
初讀:最初(第一次)閱讀(當然是專心致志、原汁原味地閱讀)給讀者印象最深的某種感覺(它也許是閱讀期待的順向共鳴;也許是期待遇挫,出乎意料的同時又豁然開朗的興奮;也許是疑竇叢生的困惑,當然都必須是基于閱讀整體上的感覺),往往是極其重要的乃至是最重要的,要緊緊抓住它不放。
首先標題的“桃花源”就可能讓讀者產生聯想。一般桃花給人的印象是春天盛開的,美麗絢爛的,同時花期又是短暫的,因此初讀標題能讓人將其與美好的事物聯系到一起。它的魅力來源,有本身時空交疊賦予詩歌的張力,給人以無限的想象空間;有把場景定格在人面桃花交相輝映的那一瞬,產生強烈的畫面感。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認,它仍然和文人心目中的桃花意象有極大關系。“人面桃花相映紅”“桃花笑東風”這兩幅畫面使人聯想到溫馨恬靜的田園生活,就可能會產生“悅耳悅目”感官上的美感。其次,文中首段的描寫,特別是桃花源里桃花林的描寫及二、三段中村落、房舍、良田、美池一直到男女耕作、老幼歡樂的情形都印證了標題的“桃花源”可能是美好事物的想法。武陵漁人——一切似可考據,確確實實。他緣溪行,經桃林,復前行,見小山,從口入,由狹至朗……移步換景,行徑鮮明,引著讀者來到了桃花源境。先是一幅遠觀圖:土地平曠,屋舍整齊,綠田、碧水、青竹,道路縱橫,雞鳴狗吠……,美妙無比,可遇而難求。農村生活,往來種作,悉如外人;黃發垂髫,怡然自樂。忙碌,樂融融,既是人間樂園,又是世外仙境。至此,作者讓我們隨著武陵漁人找到了并遠觀了這個桃花源。隨后,漁人走入其中,源中人大驚。畫面活動了,熱鬧了。桃源外,人相問答,設酒殺雞,主客相宜,桃花源的安寧歡樂更逼真了。不是必然出現卻實在地出現了的“桃花林”就應該有其特殊含義,它應該能夠傳達關于“桃花源”世界的其他記述所不足以傳達的信息。
再讀:從文本自身的特殊矛盾處入手作整體分析。基本的切入點就是“人人心中有,個個筆下無”。矛盾就是這個文本內外部的各種關系,重點是其中的共性和個性,尤其是個性。換句話說,矛盾就是差異,要看出作品與眾不同之處以及作品內的藝術世界與外部的客觀世界的不一致之處。
進一步思考感官上“悅耳悅目”的美感是如何產生的,可能會產生以下幾個問題:①為什么標題是“桃花源”而不是“菊花源”或者“菊花林”?②為何這樣的桃花源會給人以美感?美在何處?
先來看第一個問題——為什么不是“菊花源”?菊和酒是陶潛生命中最為重要的兩樣東西。《宋書·隱逸傳·陶潛傳》曾提到:陶淵明嗜酒如命,當時顏延之和他交往,每到陶家“必與其酣飲致醉”后“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那么沒有酒的時候,菊花就成為另一種寄托:“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值弘(即江州刺史王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后歸。”菊花品格是受到他肯定的。在他的理想世界里,何以沒有出現菊花的身影?如漁人去的時候,武陵源正是“菊黃佳釀熟”的時節,殺雞設酒賞菊豈不更加愜意?作者“桃花”而含“菊花”,應該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們可以假設一種最直接的、聽起來甚至是有些荒誕的原因。其一,如果是菊花的話,只能是“菊花地”或者“菊花源”,而不能是“菊花林”。其二,林的作用在于遮蔽和屏障,所以才能“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孔,仿佛若有光。”如果是菊花,遠處的山當一目了然,就不大可能獲得“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驚喜。同時,林又有引導的作用。漁人因為“欲窮其林”,才發現原來別有天地。如果不是“林”遮蔽了其他的山、其他的世界,他不一定能發現這個特別的地方。所以選擇木本植物形成的林,是情節上所必須的。
第二個問題,從景物描寫的角度看,《桃花源記》也獨具特色。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是它顯著的藝術特點。作者把自己的情感如汨汨甘泉般傾注在景物描寫中。在作者筆下,不是純客觀的景物描寫,也不是單純為追求形式美而寫景,而是飽含深情去描寫景物。《桃花源記》全文處處跳躍著作者的感情脈搏。在描寫武陵漁人發現桃花林時,作者巧妙地用了“忽逢桃花林”, 一個“忽”字,給下面的景物描寫著上了一層神奇美妙的色彩。“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廖廖幾筆,就勾畫出了一幅迷人的圖景。這神奇美妙的桃林風光讓漁人“甚異之”,所以漁人按捺不住強烈的好奇心,“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后便得一山,最后來到桃花林的盡頭。作者寫漁人進入山洞后,眼前“豁然開朗”,展現在他眼前的是一片漁人從未見過的景象: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簡潔生動的幾筆,就把桃源仙境般的生活和自然景象描繪得十分優美動人。從漁人發現桃林,進而發現并進入桃源,這一路上,有山有水,樹木蔥蘢,落花鮮美,從遠景描寫到近景,從自然風光描寫到生活環境,處處惟妙惟肖。這色彩清美的景物描寫,筆淡而意濃,猶如一首酣暢淋漓的詩,猶如一幅清美的山水畫,這顯然是陶淵明理想世界的自然景色。在那軍閥割據、士族爭權、民生凋敝、路有凍死骨的東晉天下,山河破碎、田野荒涼,面對這樣凄慘的景象,有誰能不產生“感時花濺淚”的痛苦?眼前的桃源卻是滿眼蔥綠,繁花似錦,土地肥沃,屋舍整齊,生活安寧快樂,這就形成了多么鮮明的對比!作者在他所幻想的理想世界里,自然景物描寫融進了作者的靈性和理想,從而使桃源景色的色彩與時代產生了鮮明的比照,作者把他追求美好生活的情感完全傾灑在“桃源圖”上了。不難看出,作者是力圖用這樣的自然風光來代替現實社會的全貌,寓意十分深廣。因為現實中作者無法實現美好的理想,所以才把美好的理想寄托在筆下的景物描寫上。這種情與景的交融確實蘊藏著一種迷人的感情氛圍。也正因為作者寓情于景,才使得作品中的景物色彩清美、情調優雅,品味起來清醇、甜美,起到了鼓舞、啟迪和陶冶審美感受的作用。作為一個可以緩解精神苦悶、忘卻塵世煩惱的世外桃源,作者不愿讓任何“外人”去破壞。美就美在桃花源不管是真是假,是虛是實,都是作者心中的真實。
重讀:必要時,要運用恰當的知識、方法等理論武器。以下分別借助桃花意象及陶淵明的思想傾向輔助解讀文本。
先來看桃花的意象。除了上面所說的屏障和引導作用外,桃花林或許還有另外的功能———《花鏡》中說:“桃為五木之精,能制百鬼,乃仙品也。”中國一貫有春節掛桃符祈祥的習俗。陸游有詩云:“半盞屠蘇猶未舉,燈前小草寫桃符”。根據桃的這種品性,是否可以揣測:桃花在桃源故事中實際發揮的是避邪的作用,在為這個理想的世界隔離著外界一切污穢和邪惡的侵擾?也可以從神話傳說中來尋找答案———陶淵明《桃花源詩并記》其九:“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志。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余跡寄鄧林,功竟在身后。” “鄧林”神話出自《山海經·海外北經》:“桃林方三百里,在昆侖南夸父山北。”又曰:“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 所謂“鄧林”就是“桃林”。它是逐日英雄求索理想并為之殉道的遺物和表征,它位于已“至虞淵下”逼近昆侖神山而與凡世的分野處,也是理想和現實的分野處。桃林再過去乃是另一理想世界。
實際上,在“桃源”故事的情節中,除了那片桃花盛開的桃林外,并沒有其他暗示季節的因素。洞里面的世界,時間概念也不是很明確。它只說:里面的景色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里面的人“往來種作”,衣著“悉如外人”——具體是哪一季節也沒點明。但是后人用到“桃花源”的典故時,卻總說是春天。李白一再吟唱:“行盡綠潭潭轉幽,疑是武陵春碧流”;“春風爾來為阿誰,蝴蝶忽然滿芳草。秀眉霜雪顏桃花,骨青髓綠長美好。稱是秦時避世人,勸酒相歡不知老。”陸游也提到“千載桃源信不通,境湖西塢擅春風。”因為桃花在春天開放,所以經常被用來表現春天的場景:“波隨月色凈,態逐桃花春。”“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 “桃花源”那一片盛開的桃花,傳達的正是充滿希望和生機的春天的意象之美。那么,桃林不同于菊的另一層用意是:用它來代表一個不同以往的嶄新的世界。
再來看寫之人。文為心聲,桃林本身代表的就是一種理想的境界,那么創造這理想境界的人又是怎樣的呢?陶淵明出生在潯陽郡柴桑縣的一個鄉村,在那里,他度過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時代。他從小就和美麗的山水田園景色朝夕相處,漸漸養成了淳樸坦率的性格。少年時代,家境已經衰落,致使他少而貧苦,食不果腹,冬天還穿葛布的單衣。但是,他的精神生活是相當豐富的。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這些儒家、道家的經典之中;史學、文學等類的名著,激起了他很大的興趣和豐富的想象。儒家的經典教導他有所作為;道家的哲學又教導他有所不為。如果說,基督教是憑借上帝的信仰來跨越生死界限,佛教是通過輪回轉世來獲得解脫,那么,陶淵明和莊子一樣,都是通過“自然”這個橋梁來完成生與死的超越。莊子認為,如果懂得了天地萬物生成轉換的道理,把自己納入到宇宙的整體循環之中,就會坦然地面對生死。陶淵明與莊子都選擇了“返回自然”作為解脫生死的途徑。莊子講“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陶淵明則講“復得返自然”,但在如何“返回自然”這一點上兩者是有區別的。莊子是向往遠古之世的,他的“返回自然”是讓人回到遠古那種人與自然渾然一體的史前階段。而陶淵明的“返自然”并非把人拉回遠古,而是要在現實的社會里,讓人與自然在田園背景中實現新的合一。因此,他選擇桃花源作為其理想生活的“空中樓閣”是水到渠成之事。
陶淵明向往的是理想的世界,是充滿生機的地方,是純凈美好的地方,同時也是凡人所不能輕易侵犯的很圣潔的地方。而桃是驅邪避災的植物,桃花象征著春天,象征著外貌美麗、內心貞潔的“美人”。桃花林就是那可望而不可即的“鄧林”,是神仙與凡世、理想和現實的分野處。所以,大概也就在陶淵明的“桃花源”里可尋找到超凡脫俗的“美”了。
[作者通聯: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