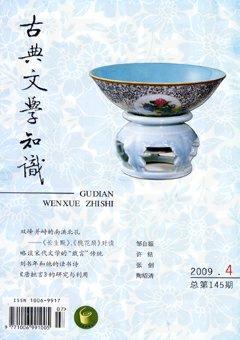古直及其文學批評
古 風
一
古直(1885—1959),字公愚,號層冰,別署遇庵、征夫、孤生,廣東省梅縣龍文鄉滂溪村人。他是我國現代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作家和古典文學專家。
作為革命家,古直于1906年即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同盟會”成立的第二年年初就加入了該會,此后就追隨孫中山先生積極進行民主革命活動。1907年冬,他與鐘動、李季子、曾晚歸、曾伯諤等人組織“冷圃”學社,傳播革命救國思想。1911年初,任汕頭《中華新報》編輯,在該報刊發《告廣東父老兄弟書》,鼓動反清革命。辛亥革命爆發一個月后,他與鐘動等人發動了武裝起義,一舉光復梅縣,任梅州軍司令部秘書長。1912年,他在擔任中國同盟會汕頭分會秘書長期間,創辦了《大風日報》,并擔任社長。1913年1月16日,《大風日報》發表了題為《萬惡政府》的社論,揭露袁世凱種種倒行逆施的罪行,成為廣東討袁斗爭的先聲。結果報社遭到查封,古直也被反動當局懸賞通緝,只好避居香港。1919年,他先后擔任廣東軍政府陸軍部秘書、封川縣縣長和高要縣縣長。1920年10月,他看到南北軍閥內戰不息,百姓蒙難,自覺無力改變國家命運,遂辭官歸隱,退出政壇。解放后,曾擔任廣東省政協委員。
作為教育家,古直于1908年響應中國同盟會“教育興國,辦學育才”的號召,與李季子在梅城北崗創辦了梅州學校,成為梅州地區最早的公學之一。次年2月1日,他在梅州學校開學典禮上致辭說,“國群盛衰,關乎志節;志節隆窳,系乎學風”。當時的形勢是“長夜漫漫,狂瀾滔滔,此誠憂時之士之所痛心,大雅君子之所嘆息者矣。予為此懼,爰咨諏同德,倡立茲校”。“予望諸生:第一,當以高尚思想,尊其人格。夫學先求是非,先致用,用以親民,非以干祿”;“第二,當以專厲精誠,研求學問”。“蓋學之為物,可以立身,可以持世,可以救國,可以平天下”(《梅州高等小學入學辭》,1909)。這充分反映了他“教育救國”和“德慧智術”全面發展的教育思想。這所學校不僅培養了早期共產黨干部熊銳(與周恩來、趙世炎等人在巴黎成立了中國共產黨旅歐總支部。1927年4月22日,被廣州軍閥秘密殺害),后來葉劍英、古大存、李金發、林風眠、黃藥眠、曾憲梓等人都在這所學校接受過基礎教育。1912年,他又在家鄉創辦了滂溪小學。1914年創辦龍文公學。1925年至1939年,任國立廣東大學(孫中山先生創辦,1926年易名為中山大學)文科教授,1928年起擔任中文系主任,1935年擔任研究生導師(當時只有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中山大學是教育部批準的首批設立研究院的學校)。解放后,曾擔任南華大學教授。
作為作家,古直于1909年年底,在由柳亞子等同盟會員發起成立進步文學社團“南社”剛一個月,就立即加入,是廣東最早的“南社”社員之一。他先后創作了《轉蓬草》(1916)、《新妙集》(1922)、《東林游草》(1928)和《解放詩鈔》(1958)等詩集,編有《層冰堂詩集》四卷(1934)和《層冰詩存》;有散文數十篇,編有《層冰堂文集》五卷;此外還有54副對聯,編有《抱甕齋聯語》一卷。他的詩歌都是情系國運,有感而發,真實地表現了他一生的心路歷程。諸如,1910年日本入侵并占領了朝鮮。朝鮮籍“南社”社員申圭植聞訊自盡,以示抗議。他寫了《哀朝鮮》一詩,歌頌其“身死國亦從”的愛國精神。1911年廣州起義失敗后,他寫了《感事》詩“滾滾珠江水盡冤,巫陽不下復何言”,“黃花消息教誰問,死抱枝頭為國魂”,悼念死難烈士。1931年,“9?18事變”后,他寫了《寇來二律》詩云:“坐擁貔貅百萬師,寇來蕩蕩竟如飛。翻哀今日偷生勇,不及當年浪死宜。”抨擊了蔣介石當局的不抵抗政策。1938年臺兒莊戰役勝利后,他聞之歡欣鼓舞,馬上給李宗仁司令長官寄去一首詩,“賴你精忠能貫日,憑君恩好與同仇”,贊揚其抗日精神。解放后,他看到自己曾經為之追求、為之奮斗的政治理想,終于在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下實現了,所以心情特別愉快。1956年7月1日,他寫了《七一生辰口號》詩,“請看太陽溫暖下,世間何物不光輝”;“河清時節近中年,愛日長依共產天”,熱情歌頌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由此可以說,他是一位忠誠的愛國詩人。
作為古典文學專家,古直從事學術研究也比較早。1910年他在主持梅州學校期間,就開始研究清人汪中的詩文。但是,他的大部分著作是在36歲辭官退政之后陸續完成的。他研究古典文學的面比較寬,著作也很多,大約有40多種,其中正式出版的有16種(不算重版、再版),著名的有4、5種。諸如,研究漢代文學,有《漢詩研究》(1928)和《漢詩辨證》(1929);研究唐代文學,有《韓集箋正》(1936);研究宋代文學,有《黃山谷詩注補正》;研究金代文學,有《元遺山詩選》;研究清代文學,有《清詩獨賞集》(1944)、《王漁洋詩選》、《汪容甫文箋》(1923)、《黃公度詩箋》等。其中,研究的重點是魏晉南北朝文學,諸如研究作家的著作,有《諸葛忠武候年譜》(1924)、《曹子建年譜》(1928)、《陶靖節年譜》(1922)、《陶靖節年歲考證》(1926)等;研究作品的著作,有《曹子建詩箋》(1928)、《阮嗣宗詩箋稿》(1930)、《陶靖節述酒詩箋》(1922)、《陶靖節詩箋》(1923)、《陶集校勘記》(1923)、《陶詩卷第考》(1932)等;研究理論批評的著作,有《文心雕龍箋》(1937)、《鐘記室詩品箋》(1927)等。其中影響最大的是《鐘記室詩品箋》一書,行世者已有上海聚珍仿宋印書局1928年、臺北廣文書局196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三個版本,共印行五次,成為古直的代表作。此外,古直學術著作以選集行世者,只有《層冰堂五種》,收入《曹子建詩箋》、《阮嗣宗詩箋》、《陶靖節詩箋》、《陶靖節年譜》和《層冰文略》等。該書有1934年刻本、1935年排印本和1984年臺北編譯館本等三個版本,影響也較大。如果將這些著作全部列舉出來,那將會是一串長長的名單,真可以說是著作等身了!
總之,這就是古直,一個革命家的古直,一個教育家的古直,一個作家的古直,一個古典文學專家的古直。他的這四種身份都是名副其實的,富有建樹的,令人欽佩的。這四種身份由一條精神主線貫穿著,就是“憤時救國”。他參加革命是如此,他辦教育是如此,他寫詩作文是如此,就連他研究古典文學也是如此。譬如在學術研究的選題取向上,他對于陶淵明的偏愛,對于黃遵憲的欽慕,都與此有關。人一生中要成就一種事業都挺不容易,但是他卻成就了四種事業,而且都做得如此之好。因此,古直先生也算是一位奇才!
二
古直先生既是作家型的文學批評家,又是學者型的文學批評家。作為作家,他“以文章為性命”(方孝岳《題〈層冰文略〉》)。其詩出唐入宋,氣韻高邁;其文眾體兼長,味道醇厚,每得時賢好評。作為學者,他融合漢宋,字句義理皆在人上,所以“心光所到,往往發千載之秘”(陳三立《與古公愚先生書》)。古直先生以作家和學者兩種眼光來進行文學批評,故能入其內,體察細微;又能出其外,燭照宏通。每發一言,皆中肯綮,堪為定評。
首先,談他對于文學作品的批評。古直先生通于文獻,熟于掌故,精于注釋。所以,他對于古代文學作品的批評,往往眼光四射,言不虛發,發則中的。譬如歷來人們常以“平澹”論陶淵明的詩,他認為這不全面。“夫公(指陶淵明)詩百三十篇,似平澹者,獨有田園諸什。然一索其實,則清剛之音,仍復流于弦外。若夫飲酒述酒、荊軻三良、雜詩貧士、擬古讀山海經七八十首,聲情激越,蓋嗣宗、越石所不能尚。而乃以平澹概之,豈知公者哉?”(《陶靖節詩箋序》,1924)他對于清代客家詩人宋湘、李黼平和黃遵憲的詩評價也很高,說:“三先生詩,光焰萬丈,江河不廢。”(《客人三先生詩選序》,1930)其中,他尤喜愛黃遵憲的詩,推崇備至。說:“詩至晚清,疲苶益甚。曹蜍李志,厭厭欲絕。風雅不忘,是在善作。黃公度先生于是崛起其間焉。觀其镕鈞百家,斟酌樂府,有語皆鑄,無能不新,屹乎如華岳倚天,浩乎如百川赴海。陽開陰闔,千匯萬狀。雖不遽云上薄風騷,下掩杜韓。蓋棺論定,則固曠世獨立,絕于等倫矣。”(《黃公度先生詩選箋序》,1926)在散文方面,古直先生更偏愛駢文,因而對于駢文有較多評論。他選編了《客人駢文選》三卷,并對所選八家駢文逐一評論。如評張九齡為“文場元帥,庶幾稱情之贊”;評李黼平為“清轉華妙,較思樸而更遒”;評吳蘭修為“揚手繡亂,雅無衛服”;評張其翻為“有體有常,漢魏于焉欲至”;評溫仲和為“篤好斯文,征揚雄之吐鳳。彌綸群典,酌劉氏之雕龍”;評丁惠康為“文采風流,庶幾侯生。手談一賦,蓋病蚌成珠矣”;評鐘動為“以枚發之體,據精征之辭,控山引淵,亦玄亦儒”;評謝貞盤為“性悅松菊,心慕柴桑。山居既賦,池草忽春。無聞作啟,有目知工”(《〈客人駢文選〉題辭》,1931)。他對于清代乾隆朝駢文名家汪中評價說:“今觀其《廣陵對》、《哀鹽船文》、《自序》、《吊黃祖》等篇,至誠激發,溢氣忿涌,形貌不同,而皆合于《小雅》、《離騷》之致。文質彬彬,然后君子。夫惟大雅,卓爾不群,容甫謂之矣。”(《汪容甫文箋敘錄》,1924)他還評價友人鐘動“其為文也,彷徨縱肆,條決繽紛”,“志隱味深,委宛清瀾”(《鐘季子文錄序》)。由于古直先生本人詩文就寫得好,所以這些批評便是內行的批評,知甘知苦,撓癢撓痛,非常到位。
其次,談他對于文學批評的批評。鐘嶸《詩品》是我國古代第一部詩歌批評專著。古直先生的《鐘記室詩品箋》四卷(1928)對此進行了深入研究。他對于傳世的鐘嶸《詩品》版本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認為,“陶公本在上品,《御覽》尚有明證。……以此推之,魏武下品,郭璞、鮑照、謝朓等中品,安保不是后人竄亂乎?”(見該書《發凡》)此論一出,震動學界。陳延杰本來在古直之前就出版了《詩品注》,但他完全傾倒在古直的觀點之下。后來,他對自己的《詩品注》進行修訂時,對古直的陶淵明“本在上品”的觀點作了更為充分的論證。盡管錢鐘書先生在《談藝錄》(修訂本)中早就指明了這種觀點的錯誤性,但其影響還仍然延續到了八十年代。古直還對于鐘嶸以“源流”論詩提出了異議。認為:“詩人篇什,如眾華釀蜜,每源雜而難判。夫十五國風,貞淫不同,美刺亦異。自非季札,誰能鑒微?則曰:某詩之體,源出某某者,亦其大較而已。”(《發凡》)不必太拘泥。這些觀點在學界影響較大。古直先生此書也得到了學界的好評。許文雨評說:“古君此《箋》,實宗《文選》李善之《注》,條記舊文,堪稱閎蘊。”(《評古直〈鐘記室詩品箋〉》,引自許文雨《〈鐘嶸詩品講疏〉〈人間詞話講疏〉》,成都古籍書店1983年影印本)曹旭評說古《箋》在“諸多方面,均有開拓,精義實多”。“平心而論,在當時的箋注中,古《箋》應算是力作,是較完備的注本,是這一時期《詩品》研究的重要收獲”(曹旭《詩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因此,《鐘記室詩品箋》是古直的代表作,其影響至今不衰。2007年,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古籍出版社隆重推出“世紀人文系列叢書”,在該叢書的“大學經典”部分,出版了由曹旭整理集評的《古直〈詩品箋〉》。可見此《箋》在今天仍然是比較好的版本。還有件事值得一提。1927年10月,胡適在《現代評論》第6卷第149期發表《〈孔雀東南飛〉的年代》一文說,從《詩品》將陶淵明放在中品、沒有提及樂府歌辭和《孔雀東南飛》等來看,鐘嶸的文學鑒賞能力不是太高。同年冬天,古直讀了胡適的文章后,在《鐘記室詩品箋?發凡》之后,又特意續寫了兩段文字。他對胡適的觀點提出了批評。他指出:“胡氏以此責嶸,可云不考。時至六代,詩、樂久分,彥和《文心》亦區‘明詩、‘樂府為二。嶸主品詩,不提樂府,亦何害乎?夫胡說難持如此,本可勿論,而慕名之士,或遂信之,故辨析之如右。”(曹旭整理集評《古直〈詩品箋〉》《發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這里讓我們佩服古直先生的有兩點:一個是他言之有理,其見識不在胡適之下;另一個是他有堅持真理的勇氣。因為,當時胡適在學術界是具有影響的人物,一般人是不敢輕易批評他的。這從其得意門生顧頡剛于1927年4月28日給胡適的信可以證明。顧頡剛在信中說:“在這一方面,我們固然為先生鼓吹,使先生的力量日益擴大,就是反對先生的人,他們也不敢說什么話,即使說來也是極淺薄的,比之蜉蝣撼大樹而已。”(胡明著《胡適傳論》下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版)古直不僅敢于批評胡適,而且針對當時學界盲從胡適言論的“慕名之士”,負起辨明是非的責任。這兩點是批評家應該具備的基本素質,也是現在文學批評界所缺少的。
再次,談他對于文學理論的批評。劉勰的《文心雕龍》是我國古代第一部比較全面系統的文學理論專著。古直先生十分重視《文心雕龍》這部書,常放在案頭,隨時披閱。他除了多次引用之外,還對于研究《文心雕龍》的學術史進行梳理和評論。他說:“《宋史?藝文志》有辛氏《文心雕龍注》(指辛處信的《文心雕龍注》十卷),其書久佚。明代校者十數家,梅子庾慶生、王損仲惟儉,其尤著也。清乾隆間,黃昆圃叔琳,依據增益,以成注本。紀文達昀,嘗糾其繆。先友李審言詳,復有補正之作。然黃注疏舛甚眾,補不勝補,正不勝┱。……黃氏注、李氏黃注補正之外,治此書者,尚有孫仲容詒讓、黃季剛侃。孫著札迻,考據精審。黃著札記,持論閎通(記自《神思》以下)。侃弟子范仲沄文瀾,依傍師說,復著講疏,雖乏妙善,亦照隙隅。”(《古氏叢書敘錄》)1937年,古直先生在中山大學任教期間,還撰寫了《文心雕龍箋》五卷。這可能是一部很有價值的書,然而今天研究《文心雕龍》者卻很少有人知道此書。原因是這部書稿在古直生前就遺失了。據古直兒子古成業(現居廣州)回憶說,當年,有一位古直的朋友將《文心雕龍箋》書稿借去,就一直沒有還回來,至今下落不明。這是一件十分遺憾的事情,也是《文心雕龍》研究的重大損失。現在,我們熱切希望有知情者能夠幫助找到這部書稿,那將會是學界的一件幸事。
總之,古直先生的文學批評,涉及到文學作品、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等方面,是一位完整意義上的文學批評家。古直所批評的對象主要是古代文學,其批評觀念和批評標準也都是來自傳統的。雖然他早年偶涉西學,但是西方文學批評對他一生幾乎沒有產生任何影響。因此,古直先生的治學方法是相當傳統的,也是一位相當傳統的文學批評家。需要指出的是,關于古直文學批評的研究,目前還未引起學界的重視。最近,宗親古小彬和古向明編輯了《國學家古直》一書(香港新聞出版社2008年版),求序于我。故特撰此文,聊以為序;并拋磚引玉,希望學界對于古直先生的文學批評予以更多的關注。
(作者單位:揚州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