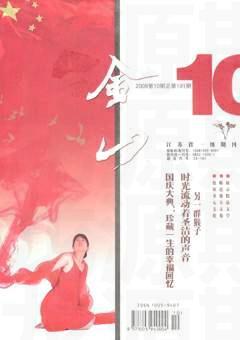追思“二老”風范 感悟“三辭”、“三不”
余耀中
2009年7月11日,是一個令人難忘的日子。一日之間,季羨林、任繼愈兩位年高位尊的學者,相繼離世,前后僅相距4個小時。“二老”于同一天告別人世,同一天駕鶴西行,是一種巧合,也給人們留下了不盡的雙重思念。逝人已去,風范長留,人們之所以深情地敬重二老,深切地懷念二老,不僅是因為二老的學識,還因為二老高尚的道德品質。季老的“三辭”,任老的“三不”,伴隨著二老的學識、品德將流淌在歷史長河中,傳頌在人們的心目中。
“摘去三桂冠,還我自由身”。季老親切而又感人的話語,仿佛仍在耳邊回響。他生前,一辭“大師”,二辭“泰斗”,三辭“國寶”,已被視為美德,傳為美談。
季老為何一而再,再而三,三辭三桂冠?起初,有的人感到不可思議,有的人感到迷惑不解,更多的是,只知其然,很想知其所以然。“三辭”的深處,珍藏著季老的心境,心境之中有他為人為文的崇高境界。他在《病榻雜記》中,真誠地道出了,他自己是如何看待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頭上的“國學大師”、“學界(術)泰斗”、“國寶”這三項桂冠的呢?他,虛懷若谷,遠離名利,淡泊明志,不圖虛名,他坦坦蕩蕩,誠誠懇懇,一一作辭,面對“大師”這頂桂冠,季老如是請辭:“環顧左右,朋友中國學基礎勝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竟獨占‘國學大師的尊號,我連‘國學小師都不夠,遑論‘大師!”;面對“泰斗”這頂桂冠,季老如是請辭:“我這個‘泰斗從哪里講起呢?在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中,說我做出了極大的成績,那不是事實。說我一點成績都沒有,那也不符合實際情況。這樣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現在卻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這個‘泰斗又從哪里講起呢?”;面對“國寶”這頂桂冠,季老如是請辭:“我所到之處,‘國寶之聲洋洋乎盈耳矣,我實在是大惑不解,是不是因為中國只有一個季羨林,所以他就成為‘寶。但是,中國的趙一錢二孫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個,難道中國就有13億‘國寶嗎?這種事情,癡想無益,也完全沒有必要。我來一個急剎車。”
季老三辭桂冠,完全出于真心實意,并非是虛情假意般的半推半就,更不是掛在嘴邊的客套話,在三頂桂冠面前,他淡然相對,坦然相辭,泰然如松,他說:“三頂桂冠一摘,還了我一個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歡喜。”季老的胸襟,受到世人的崇敬,社會的贊許,2006年“感動中國”活動的頒獎辭,對季老的評價如是說:“智者樂,仁者壽,長者隨心所欲。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貧賤不移,寵辱不驚。學問鑄成大地的風景,他把心匯入河流,把心留在東方。”
再說“百年孤燈、皓首窮經”的任繼愈老先生,他以低調的人生處世為人,他平生說的最多的一個詞,就是“低調”。
任老,1987年任北京國家圖書館館長,歷時18年,其間,他精心組織和領導了中國最大規模的傳統文化資料整理工作,完成107卷的總字數超過一億的《中華大藏經》;影印出版了鎮館之寶《文津閣四庫全書》;開展了總字數約7億字的古籍文獻資料《中華大典》的匯編工作。可是,任老在他卸任時,并沒有侃侃而談他工作的成就和業績,只是淡淡地說:“我想了半天,也沒覺得我做了什么事,工作都是大家做的。我給圖書館玻璃的門上貼了個條,省得大家撞到玻璃上,這可能就是我做的工作吧。”多么低調的人啊,多么低調的話語,聲聲入耳,比起那些空空洞洞,不著邊際的“高調”來,這種“低調”,“低”得使人震撼,震撼于心靈之中。
任老退休之后,仍然堅守“低調”,他選擇了“出世”的態度,樂守善道,甘于寂寞,低調做人,埋頭做學問。他的“三不”尤為感人:第一,不赴宴請;第二,不出全集;第三,不過生日。這“三不“聽起來普普通通,想起來耐人尋味,低調的話語中,深藏著任老的人生境界和人生哲理。
任老因何不赴宴請?并不是他的性格古怪,也不是他疏于交往和禮儀,而是因為他不喜歡把時間浪費在學術之外的地方。
任老因何不出全集?他有自己的獨到見解,他覺得:“人的學術是不斷發展的,昨天之我與今日是有差距的,怎可以‘全定論。”這是他換一個獨特的視角看出書,舍棄了求“全”的一種思維。
任老因何不過生日?七十大壽,八十大壽等等的生日,都沒有專門慶祝過,他是自己給自己“立規矩”不過生日。世間上,不乏有“大生日大做”的,甚至也有“小生日大做的”。一生務實求真的任老,對自己的生日,有自己的思考,有與別人不同的思考,他曾經對家人坦誠地道破個中的原由,他說:“不過生日,是因為在這樣的時候,人們都會說起違心的話,比如‘長命百歲,沒有必要。”求真的人,總是面向真實,任老的“不過生日”,原來是在堅守著一個“真誠”的心境。
季老的“三辭”,任老的“三不”,這是兩位老先生人之為人的一種自我選擇,雖然內涵不盡相同,但是,為人的品德,學人的風范,則是共同的,且又是相通的。“三辭”是為了堅守真實的自我,“三不”同樣是為了堅守真實的自我,兩位老先生用一個“真”字點燃了自己的人生,用一個“真”字鍛造了自己閃光的人生。世人如是說,兩位老人自己也如是觀。人們都用贊美的目光來看季老的樸實平凡,說他更像一位學界的“門房”、“校工”、“鍋爐工”,而季老呢,他面對自己豐厚的著作和豐碩的成果,只是淡淡地說道:“我寫的東西不會有套話、大話、至于真理是不是全部講出來,我倒不敢說。我只能保證,我講的全是真話。”對于任老,清華大學顧秉林校長的一番感言,言出了人們的心中之言,他說:“任老一直提倡沉潛篤實的學風,主張在學術上,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幾分把握說幾分話。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這正是一個真正的學者,一位杰出的宗師,最特有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