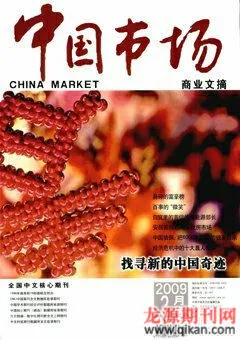在中國長大的加拿大人
盧克說,如果不是因為毛澤東,就不會生活在中國;如果中國沒有在三十年改革開放期間擺脫毛澤東的陰影,他如今也不會生活在中國。

盧克,1949年出生在北京的加拿大人,在這里,他與改革開放一起長大。文革期間,他曾經在北京一家金屬加工廠工作了幾年,這聽起來好像沒什么大不了的。
然而,盧克并非僅僅是工業生產線上一位無名之輩。他曾經是一位名叫庫魯克的盎格魯加拿大少年,如今他仍然生活在中國,是一位中年商人。回憶起喧囂的青年時代,他表示,那時自己從來沒想過最終會在中國做生意,尤其沒想過進口酒。“那被視為異想天開。”
如果不是因為毛澤東,盧克不會生活在中國。因為他的父母相信“新中國”,并來到中國工作。但他補充說,如果中國沒有在三十年改革開放期間擺脫毛澤東的陰影,他如今也不會生活在中國。
他回憶道,那不是因為物質的問題,而是那時有很多不必要的警惕,很多好事者不讓鄰居安穩睡覺。
在盧克的成長時期,中國實際上對西方人并不熟悉,這樣,他和他的家人就受到特別的關注。有時候,這沒有什么害處:他和家人獲準到鄉下去的時候,驚訝的路人堵塞了街道。有時候則是災難:在文革期間,盧克的父母都被當成間諜關起來,而他則被派去工廠。
盡管盧克上的是中國學校,和本地人一樣說中文,而且取了個中國名字,但他的外貌令他與周圍格格不入,很受約束。他回憶道:“我們的活動范圍半徑是15公里。”當時,出北京的路有藍白標記用中文、俄文和英文注明:沒有獲得許可的外國人不得越界。
現如今,那些警告早已消失,而盧克的生活也被改革開放深深改變了,所以他極為珍視“開放”。
“在成長過程中,我常常意識到我會成為中國朋友的包袱,要是和我在一起的時候被人看見了,對他們而言會是一個問題,對于那些不把這放在心上的人,我總是很感激。”他表示,如今中國最令他感到高興的變化之一就是,他可以和人們交談,而那些人也不用因為和外國人聯系而深感憂懼,“現在不用害怕了。”
如今有超過40萬外國人在中國生活,大部分是被商機吸引過來的。除非是在小城鎮,“長鼻子”已經不再罕見,而且這種對外國人的傳統稱謂幾乎已經完全停用了。
談到以前的同學,盧克表示,“世界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他們的子女有一半在國外生活,這不會令他們震驚。而在那個時候,他們唯一的旅行就是下鄉。”
這種愿意嘗試新事務的新開放精神推動了他的業務——家進口酒公司。中國數量日益增加的富裕消費者對外國奢侈品的胃口很大。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對外國影響不那么害怕了。盧克記得,他每次從海外回來就給父親帶一臺新的短波收音機,讓這位老英國人收聽他所鐘愛的BBC,這在以前會構成偷聽敵方電臺的罪名。
如今,盧克和其他人一樣,可以在互聯網上收聽BBC,而且不必擔心隔墻有耳。(摘自:《基督教科學箴言報》2008年12月19日 編譯:何樂)
點評:424年前,意大利人利瑪竇從中國肇慶的一個小碼頭上岸,他給中國人帶來了一張剛剛繪制好的世界地圖。從此,中國人知道地球是圓的。
如今,在首都機場T3航站樓里,每天都有幾十架國際航班從世界各地降落;每天都有數千名外國人自由地來到北京,學習、工作、旅行或者定居。
數年翻云覆雨,有些事實,回頭看來竟如此有趣。傅高義先生在他的《共產主義下的廣州》一書中,提到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對待外國人的政策:“在廣州的大部分外國人已經離開,大多數在1949年后留下來的外國人懷有一種更為理想主義的堅持,他們是傳教士、教育工作者、福利工作者。“
留下的這些人,來自世界各地,因為不同的緣由戀上中國。生活在這里,他們不僅是游客或看客,而且是主角,在他們眼中,這個國家的發展如同正在上演的一部紀錄片。不管是從小就長在中國的“洋土著”,還是被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市場吸引而來的創業者,每個人都在這部片子里演繹著不同外表下的中國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