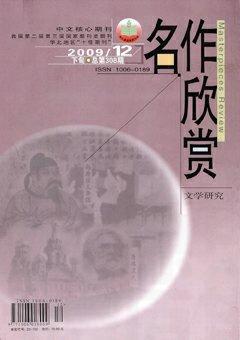燭照城市底層的溫暖與尊嚴
袁 萍
關鍵詞:王安憶 《驕傲的皮匠》 城市底層 溫暖 尊嚴
摘 要:《驕傲的皮匠》講述了一個底層的外來者在融入都市日常人生過程中如何獲取安穩、守護尊嚴的生活故事。王安憶消解了以往有關城鄉敘述中基于道德或文明視域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用一種溫暖的筆調,營構出都市世俗化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空間。
王安憶的《驕傲的皮匠》應該是2008年度最好的中篇小說了,在不久前由北京文學月刊社和中國小說學會組織的兩次年度排行中都名列中篇小說的榜首。從上個世紀80年代的《流逝》到90年代的《長恨歌》,再到新世紀的《桃之夭夭》,王安憶一直留戀著她的上海故事,經營著她的弄堂人生,雖時遭詬病,仍樂此不疲。她說:“上海是我唯一的寫作源泉,我只能尊重這個事實。如果只能寫上海的話,就必須挖掘這個城市的資源,對于上海來說,小市民的生活是那么巨大的源泉和材料,你怎么能無視它的存在?所以,這個小市民的寫作,以后還會繼續的,不可能改變。”{1}《驕傲的皮匠》仍然是關于上海普通市民的弄堂人生,王安憶用一種溫暖的筆調,營構出都市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空間。小說講述了一個底層的外來者在融入都市日常人生過程中如何獲取安穩、守護尊嚴的生活故事。
一、城市底層的溫暖敘述
在王安憶以往的上海敘述中,故事的主人公大多是負載了都市滄桑的名媛佳麗,如《流逝》中的歐陽端麗、《長恨歌》中的王琦瑤、《文革軼事》中的胡迪菁、《桃之夭夭》中的郁曉秋等,作者常常借人物命運的起伏演繹城市歷史的變遷。《驕傲的皮匠》與王安憶以往的上海敘述不同,小說中的主人公不再只是負載著都市滄桑的上海人,而是承襲了鄉村記憶和城市變遷的外來客。這是一個敘述都市的新視角,王安憶消解了以往有關城鄉敘述中基于道德或文明視域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小皮匠根海的身份有著較為復雜的文化意味。一方面,他來自蘇北農村,一家老小在鄉下,與鄉村有著血緣聯系的他并沒有完成精神上的遷徙,孝順、純樸、善良等鄉土中國的傳統道德操守仍然頑強地矗立在他的精神深處。另一方面,他住在上海,在城里謀生,與這座城市有著較為久遠的淵源,他的皮匠家族見證了這座城市的歷史變遷,因而在他身上又顯見許多現代城市文明的印痕。
張愛玲說,“人生的所謂‘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飲食男女這兩項”。作為新一代的“海派傳人”,王安憶深知“人生安穩的一面有著永恒的意味”。《驕傲的皮匠》用的是“人生安穩的一面”做底子,近乎瑣屑的生活場景,隨處可見的尋常人物,王安憶用“尋常人”的視角,攜帶一點懷舊的感傷,在市井人物的尋常生活中找尋一種溫暖的詩意。皮匠街頭做活的場景在平凡的世俗中蘊含著生活的魅力。王安憶用鏡頭式的語言描寫了兩代皮匠做活時的動人場景:“皮匠攤跟前的小馬扎上,常常坐著一個女孩子,脫了鞋的腳踩在另一只腳的腳背上,等待皮匠做完她的活計,這情景看起來挺溫馨的。”時過境遷,物是人非,仍然是在這塊“方寸之地”,當年的老皮匠換作了小皮匠,小女孩換作了老太太,作者又一次描繪了小皮匠與岳母街頭靜坐的場景:“岳母守在小皮匠身邊,看著小皮匠接活做活”,“弄堂前馬路上的景色,曾經在她男人眼睛里流連過,女婿手里的活計,就是她老頭子的手藝,似乎覺著將來有靠頭了一些”,“一老一少,也沒什么可說的。就是這么緘默著”。皮匠攤前的“緘默”中流露出的不只是相互依賴的信任和親情,更有動人的人性光輝和日常生活的詩意。小皮匠吃飯時的“家常一幕”更是溢滿了安穩人生的溫暖。當鄉下親戚到來的時候,“小皮匠家的飯桌不是第一,也是第二。東西都是從鄉下帶出來的,草雞燉湯,六月蟹攔腰一剁兩半,拖了面糊炸,蝽子炒蛋,鹵水點的老豆腐,過年的臘肉或者風鵝,還有酒。要是小皮匠的父親在,就兩個人對酌,單小皮匠自己,就是獨飲。他喝一陣子,吃了一些菜,女人就給盛上滿碗的飯,重新熱了雞湯。雖然是盛暑,可他們家鄉的習慣,葷湯是要吃大滾的,吃出一身熱汗,內里的濕熱便發散出來。果然,風吹在身上,沁涼了許多。月亮也升起了”。為了在小皮匠的日常生活和城市棲居中烘染出諸多令人感動的溫暖和詩意,王安憶不惜篇幅地絮叨著瑣屑的生活。當然,這些溫暖和詩意不只是來自小皮匠身后深厚綿遠的鄉土親情,也有他日夜置身其中的城市友善。
小皮匠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城市異鄉人或漂泊者,作者在一開始便交代了他與這座城市的“歷史淵源”:從城郊墓園到中心街區,從山東巡捕到浦東商人,從老皮匠到小皮匠,“倘若要說明這塊方寸之地為什么屬于小皮匠,大約就要涉及這近代城市的發展史了”。值得注意的是,王安憶在這里并沒有按照她以往的慣常路數,不厭其煩地借弄堂舊識演繹都市滄桑,而是以親切平淡的語調把小皮匠與這座城市的“歷史淵源”娓娓敘出。小皮匠從他的皮匠家族那里繼承了與這座城市先天的血脈親緣。皮匠雖然來自鄉村,漂泊在街頭,“可總也漂泊不出這條街。他已經在這里做熟了,這里的人都是他的老主顧,他不能輕易放棄”。在這種底層生存中,皮匠安之若素,與城市形成了不離不棄的和諧,“皮匠攤設在臺階上退進去的地方,很妥帖也很諧調的樣子”,“這條街上的人,也習慣了他的活計,有時候他回鄉下去幾天,人們就將活計留著,等他回來做,并不會去找隔街的那個皮匠”,“他又不礙事的,各部門對他的驅趕其實也不認真,漸漸地,就形成事實”。王安憶在溫暖平淡的敘述中,消解了底層生存的艱辛和粗糲。這一敘述指向顯然不是為了追憶這座近代城市的“逝去年華”,而是為了使她筆下人物獲取在城市詩意棲居的合理身份,從而使得小說卸去了歷史文化的厚重,而具有了日常生活的溫暖。
二、都市邊緣的尊嚴守護
鄉下來的小皮匠不僅在這座倨傲虛榮的城市里獲得了日常生活的溫暖,而且還贏得了“尊嚴”。在日益物質化的城市四處潛伏著欲望的陷阱。生活在都市邊緣和底層的小皮匠在欲望的囂動中守護傳統道德,努力保持內心的平靜。
康德說:“道德和能夠具有道德的人性是唯一具有尊嚴的。”{2}在他看來,財富、健康、機智等都不能體現人的尊嚴,因為這些外在的而具有價值的東西并不能把人置于不可替代的地位。小皮匠的尊嚴首先來自于他對道德的守護。他孝敬長輩,“為了表示贍養的決心”,他毅然把媳婦留在家中,“單身一人”在城市勞碌。他潔身自好,許多女顧客與他“很稔熟”,甚至“有些輕薄”,但是小皮匠則很持重,并不唆。他鄙視城市中的不潔欲望,為此寧可犧牲掉與河南房客那點“五湖四海的友情”。他寧可讓他的女人在鄉下“耳目閉塞”,也不讓她到“大染缸”似的城市來接受“污染”。小皮匠時常站在道德的高處鄙棄城市的陰暗面,甚至對這個“什么都攪在一處,分也分不開”的城市產生“同情”,覺得它是一個“可憐的世界”。顯然,小皮匠的精神優勢在很大程度上來自屹立在他身后的鄉村傳統。這在他對城市消費社會的批判中也可以得到確證。“即便是幾千塊錢的意大利皮鞋,小皮匠都能以平常心來對待”,雖然對名貴皮鞋有時“要格外小心一些”,但他“不是出于對昂貴價格的誠服”,而是出于職業上的“天生惜物”之心。“這種天價的名牌讓他覺得造孽”,“他心里有一個底,就是萬變不離其宗。怎么說?鞋總歸是鞋,總歸是要吃力,所以,堅固總歸是第一位的”。小皮匠對“名牌”的態度彰顯出傳統的實用主義心理和對消費社會的批判理性。
只有道德以及為理性所規定的意志才可體現的人類尊嚴,而意志只有在需要的沖突中才顯示出道德性,才具有尊嚴。小皮匠也有單身的孤寂,“免不了會想起女人綿軟的身體”,但他寧可在飲食的“盛宴”中揮霍欲望,也不愿到發廊和足浴房去發泄苦悶。然而,小皮匠還是在城市遭遇了世俗的愛情。他以自己的淳樸善良、知識見地和生命活力贏得了城市女性根娣的青睞。從衣食相幫,到情感相依,再到身體相擁,小皮匠與根娣的情愛在瑣屑的日常來往中水到渠成。然而,當“這人生的際遇給了他們莫大的歡喜”時,根海最終用妻子和女兒重新召喚起了自己作為丈夫和父親的責任,主動放棄了與根娣的情愛。小皮匠對城市情愛的回避再次彰顯了道德的力量。
“腹有詩書氣自華”,知識活動是人類最高尊嚴的存在。人們常常通過知識獲取身份和敬重。小皮匠的尊嚴不僅來自他對道德的守護,同時還來自于他的知識見地。小皮匠很愛看書,而且“比較廣泛”,包括《說岳全傳》、《武松》、《資治通鑒》,還有一些《檢察風云》、《讀者》、《今古傳奇》等雜志。雖然這些通俗書刊并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是它們同樣包含了豐富的生活經驗和樸素的人生道理。小皮匠對書有自己的看法和選擇。他把書分成古代和現代兩種,他認為,“古書里面有很多大的小的道理,大道理是關于世道,小道理則關系做人”,現代的書“說當下的事,可以開眼界,不至于太蒙塞”。小皮匠不但“用心”讀書,而且還善于從這些通俗書刊中汲取生活經驗和處世道理,“他可以用現代書里的那些人和事來檢驗古書里的道理,反過來,古書里的道理又可用來解釋現代的事情”。小皮匠的知識見地使得他在城里人面前“驕傲”起來。根娣對他的愛慕、小弟對他的佩服和叔爺對他的忌憚都源于此。小皮匠不但在手藝方面與時俱進,而且在精神氣質上超越了他的皮匠家族。每一代皮匠身上都脫不了臭味混雜的皮革氣味,然而小皮匠卻與他的前輩們不同,他身上不但沒有“這股皮匠行業的傳統氣味”,而且在儀表上非常講究。上班前,他“像一個正規企業里的工人,要換上工作服”;下班后,他又像一個高檔寫字樓里的白領,穿上西裝,戴上領帶,用香皂洗了手臉再回家。雖然王安憶時常在城市過往的懷舊中流露出一種文化守成主義色彩,但是顯而易見,在小皮匠的“驕傲”里既有來自他身后鄉村傳統支撐的道德品性,也有來自他面前城市文明陶冶的精神氣質。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說《驕傲的皮匠》代表了一種新的高度。
三、弄堂人生的世俗擁抱
王安憶在一次講演中說:“小說不是現實,它是個人的心靈世界,這個世界有著另一種規律、原則、起源和歸宿。但是筑造心靈世界的材料卻是我們賴以生存的現實世界。”{3}既然筑造小說世界的材料來自現實世界,那么《驕傲的皮匠》是由什么樣的材料筑造的呢?
毋庸諱言,《驕傲的皮匠》的材料全部來自弄堂人物的世俗生活。弄堂“是個產生是非的地方”,是都市中藏污納垢的“民間世界”。而只有這樣的“民間世界”才充盈著豐富的細節和淋漓的生氣。上世紀40年代它成就了張愛玲的“傳奇”,半個多世紀后,王安憶仍然在這里演繹現代上海的風情。進城皮匠的做活、穿衣、吃飯,下崗女工的逛街、跳舞、打牌,皮匠攤前的風月,麻將桌上的流言,男人間的爭斗,女人們的算計……王安憶不愧為編織細節和營構生氣的高手,以小皮匠為中心,鋪展出弄堂各色世態人情。
既然現實世界為心靈世界提供了豐富的材料,那么小說家又是如何有效地運用這些材料,并以此建筑起屬于她“個人的心靈世界”的呢?王安憶說:“從現實中汲取寫作的材料,這抓住了文學,尤其是小說的要領,那就是世俗心。”{4}現實世界是世俗的生活,小說的材料來自現實世界。因而,寫作者只有具有了世俗心才能融入世俗生活,才能從世俗生活中“汲取寫作的材料”,才能運用這些材料筑造起“個人的心靈世界”。有人說,小說只有“從俗世中來的,才能到靈魂里去”{5}。這多少道出了小說的秘密,越是俗世的越具有真實感人的力量。正是因為王安憶所具有的世俗心,《驕傲的皮匠》才有了俯拾皆是的富有世俗氣息的細節和場面,才有了真實生活的質感和觸動心靈的感動。
“世俗心”是接近小說的關鍵,要真正進入小說還需要有“邏輯的力量”。王安憶在談及福樓拜小說時說,“有時候小說真的很像鐘表,好的境界就像科學,它嵌得那么好,很美觀,你一眼看過去,它那么周密,如此平衡,而這種平衡會產生力度,會有效率”{6}。顯然,王安憶在這里強調的是小說要有符合生活的“邏輯”。因為現實世界提供給我們的材料通常是“一堆雜亂無章的東西”{7},是無序的,沒有邏輯的。這就需要作家根據生活的邏輯去組合和構筑一個“個人的心靈世界”。表面上看來,《驕傲的皮匠》充滿了生活的細枝末節,作者的敘述似乎漫不經心,但實際上這些生活的細節都在作者嚴密邏輯的組織下不蔓不枝。譬如,小皮匠與城市的和諧相處,是合乎歷史邏輯的必然;小皮匠贏得根娣的青睞,是小說順理成章的發展;爺叔在金蓉那里遭遇挫折,也是符合生活邏輯的安排。雖然小說是虛構和想像的世界,但是它的虛構與想像必須符合生活的邏輯,否則一切都將會遭到讀者的拒絕。
王安憶曾經這樣表述她的小說“理想”:“不要特殊環境、特殊人物;不要材料太多;不要語言的風格化;不要特殊性。”{8}這一“理想”實際上是小說創作“返璞歸真”的最高境界。當一名寫作者不再為“某種潮流、某種旗號、某種社會需要而寫作”,而把寫作當成一種“心靈的需要”,“從內心出發”,為“自我”寫作時,生活的“大地”將向他(她)無限敞開。《驕傲的皮匠》代表了王安憶小說創作的一個新的高度,它在某種程度上昭示著是王安憶小說理想的到來。瑣屑中蘊涵著豐富,質樸里透露出成熟,作者不再追求敘事的技巧和語言的豐富,而是在平淡樸拙的敘述中從容地完成了語淡意遠的風格轉向。
作者簡介:袁 萍,南昌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主要從事文藝學及中國當代文學研究。
{1} 鄭媛.借《啟蒙時代》遠離張愛玲,王安憶稱80后都不好惹[N].北京青年報,2007-05-14.
{2} 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4.443.
{3} 王安憶.心靈世界——王安憶小說講稿[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143.
{4} 王安憶.導修報告[J].小說界.2006(2).
{5} 謝有順.小說的物質外殼[J].當代作家評論.2007(3).
{6}{7} 王安憶.小說的當下處境[J].大家.2005(6).
{8} 陳潔.訪作家王安憶:寫作只服從心靈的需要[N].光明日報.2003-10-11.
(責任編輯:呂曉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