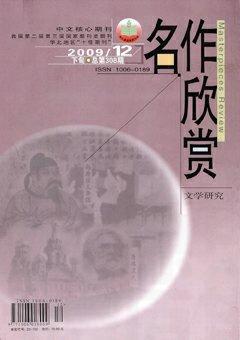《八月之光》中的母親角色
邵 娟
關鍵詞:威廉·福克納 《八月之光》 母親角色
摘 要: 本文通過對威廉·福克納《八月之光》的文本細讀,分析福克納對作品中母親角色構思和塑造上的藝術特色。通過人物身份的設計、人物對故事情節的作用、人物寫作手法的選擇等方面,福克納描繪出了20世紀初美國南方社會的種族的、階級的和兩性之間的矛盾。小說中的母親角色不是因情節設置需要而任意添加而成,她們的處境和性格關聯映照出了另一主人公克里斯默斯無法擺脫的悲劇命運,并影響著故事的發展和結局。
威廉·福克納發表于1932年10月的《八月之光》,通過杰弗生鎮十天的社會生活的描述,揭示了幾個主要人物的一生及其三代家史,體現了人類“心靈深處的亙古至今的真實情感、愛情、同情,自豪、憐憫之心和犧牲精神”(Faulkner:680),表明了作家反對種族偏見和宗教偏見的態度。
作為威廉·福克納的作品中最長的一部小說,《八月之光》以多重敘事角度的情節結構而聞名。故事主要分兩條線索,一條講的是克里斯默斯,他從小被送進孤兒院,因被懷疑是黑白混血兒從此失去了“身份”,受到社會種種虐待,最終促使他殺死了白種情人而被白人私刑處死;另一條講的是農村姑娘莉娜與情人相戀,懷孕后遭到遺棄,卻千里迢迢徒步來到杰弗生鎮尋找情人。
20世紀以來,隨著符號學和敘事學的發展,對這部作品文藝層面的探討已成為福克納研究的另一重要分支。讀者的閱讀也不再僅僅停留在對故事主要人物和情節的把握上,小說的二線人物和細節描寫逐漸成為閱讀的一個新焦點,而二線人物中的母親角色尤為引人注目。
《八月之光》中的女性幾乎或者說全部都是處于不利地位的配角,而這其中的母親角色除了莉娜外,其他人更是影影綽綽,有的(比如米莉和麥克依琴太太)甚至沒有機會替自己說上一句話;有的只能讓讀者透過她們的只言片語去揣測其內心世界(比如老海因斯太太和阿姆斯特德太太)。本文嘗試從《八月之光》中的幾位母親角色入手,探求母親角色對于小說故事情節的推動以及對錯綜矛盾的映照。
一
在那不具有感情色彩的開頭——恬靜從容得令人吃驚——莉娜·格魯夫的出現,就已經是一個類似于史詩的畫卷。一個懷孕的大腹便便的年輕女人,從千里之外徒步跋涉,帶著令人難以置信的信任感——生活中那種近乎弱智的單純和善良——來尋找孩子的父親。
莉娜·格魯夫自然是小說中母親隊列中的主角。《八月之光》寫于福克納的第一個女兒早產而夭折之后,正如福克納作品的法語譯者庫安德羅在他翻譯的《喧嘩與騷動》的前言里說,感情上的刺激是促使威廉·福克納寫作的重要因素。面對夭折的早產兒、孱弱的產婦,在悲痛的父親福克納眼里,健壯的孕婦和孩子就是最為珍貴的。1931年8月開始寫作的《八月之光》,最初題為《黑屋》,但內容和題目經過再三修改后,《黑屋》就變成了《八月之光》。平靜生活在自己天地的莉娜·格魯夫(Lena Grove)也成了小說中帶來光明的人物之一,雖然所耗筆墨有限。
父母早喪,莉娜從小和哥哥一家一起生活。沒受過什么教育的她似乎只是按照人的健康本能和沖動行事。她受了那個愛講俏皮話的盧卡斯·伯奇的誘騙而未婚先孕,對逃跑的未婚夫伯奇深信不疑,并下決心尋找他。一路上在鄉親們的幫助下,她風塵仆仆來到杰弗生鎮。孩子的父親,無賴盧卡斯·伯奇在出現在她面前幾分鐘以后,就撒謊溜走了。
生活在那年代里,作為一個沒結過婚的遭人遺棄的母親,她的生活只能在貧困、辛勞中渡過,她卻泰然自若,毫不感到羞恥。她只知道自己命中該有丈夫、該生兒育女。小說開始不久,福克納用莉娜風塵仆仆、不停行走的意象來喚起對濟慈《希臘古甕頌》中田園世界的聯想。莉娜與其說是福克納塑造的一個代表頑強的生命力、超然人格的女性形象,“不如說是他有意運用了一個非人格化的意味雋永的象征”(福克納:11)。
《袖珍本福克納選集》的編者馬爾科姆·考利說過,福克納筆下的人物都有一種對命運逆來順受的味道。但福克納自己卻并不以為然,有的人物如《八月之光》里的莉娜·格魯夫“就是和自己的命運極力搏斗的”(李文俊:238),她的男人是不是盧卡斯·伯奇并不重要,只是由于他是她肚子里孩子的生父,才不遠千里一路步行從亞拉巴馬州來到杰弗生鎮找他。盧卡斯·伯奇也不會從根本上改變她的命運,她的命運無非是嫁個丈夫,生兒育女。這一點她心里很明白,所以“她不要別人幫忙就走出家庭,去和自己的命運周旋”(李文俊:238)。
另一方面,莉娜的感性形象,讓我們脫離了那些深遠的意蘊和古老的象征,看到一個植物般茁壯單純的年輕姑娘。當莉娜長成大姑娘后,穿上郵購來的衣裙的莉娜每次去鎮上,總要在鎮口就從馬車上下來,光腳丫子走在人行道上。她當然不是享受平坦的街道,而是一廂情愿讓路人相信她也是個住在城鎮里的人。這種小女兒的虛榮和嬌憨令人忍俊不已。
當被盧卡斯·伯奇誘騙而未婚先孕后,哥哥咒罵她、斥責那個男人時,莉娜卻不肯認錯,一味替盧卡斯·伯奇開脫。像通俗小說中私奔的女主角一樣,夜晚拖著沉重的身子的她從窗子里爬了出去,除了零碎東西還隨身攜帶了自己全部的錢——三毛五分硬幣。
一路上遇到滿是善良的叫不上名字的鄉親,往往不等他們詢問,莉娜便會從頭到尾地講述她的故事,慢條斯理,一本正經,簡直“像一個說謊的孩子”(福克納:16)。當她回想起在阿姆斯特德家吃早飯的情景時,還自豪地感覺自己“吃東西像位貴婦人,像貴婦人那樣旅行”(福克納:17)。而拿著阿姆斯特德太太給她的一些零錢買沙丁魚時,她連沙丁魚的音都發不準,說成“花丁魚”。惹得售貨員也跟著她說“花丁魚”調侃她。
莉娜在杰弗生鎮做了母親——自己的頭生子出生了,其間另一主人公克里斯默斯殺人后外逃、被抓、再逃,最終被私刑處死。就在同一天,一方面是新生命的誕生,另一方面是血腥的死亡,為了平衡小說——也許也為了平衡自己的信仰——福克納才創造出了莉娜這樣完美得近乎于天使一樣的人物。
二
小說中隨著故事的展開,關于莉娜的筆墨漸次淡去,主角克里斯默斯開始登場。作為小說最重要的線索,身份不明的克里斯默斯,成為小說用筆最多的人物。因為被懷疑是“黑白混血兒”而失去了“身份”,“作為小說中唯一的悲劇人物,克里斯默斯因為不知道自己是誰,所以就故意拒絕任何人”(Vickery:2)。最終促使他殺死了白種情人而被鎮上的白人私刑處死。
圍繞克里斯默斯,小說中又出現了幾位母親,他的生母、外祖母、養母,以及他懷有身孕的情人。克里斯默斯的外祖父老海因斯是一個狂熱的種族主義者,他矮小、好斗,一天到晚叫囂著要把黑人統統殺死。當女兒米莉和一個疑是混血黑人的馬戲班墨西哥人私奔時,老海因斯騎馬追上后,在雨夜一槍打死這個馬戲班“黑人”,而米莉此時已懷有身孕。等米莉到了分娩的時候,老海斯拒絕為她請醫生,眼睜睜地看著她難產而死,留下了父母都死于非命的孤兒克里斯默斯。在小說中米莉自始至終沒有為自己說上一句話,就在十八九歲時閉上了眼睛。雖然她曾憧憬自由的生活,身穿節日盛裝,拿著手提袋同情人試圖逃走,逃離陰仄好斗的父親,但終歸失敗。
克里斯默斯殺人后在摩茲鎮被捕,他的外祖父母老海因斯夫婦恰巧住在此鎮。當得知他被捕的消息后,老海因斯夫婦30年來死水一般的生活又被攪起,老海因斯竭力煽動鄉親們的情緒,告訴人們,“他是那畜生的祖父,養了個魔鬼的后代,一直監管到今天”(福克納:301),一定要把克里斯默斯處以私刑。老海因斯太太則要形影不離地看住他,不讓他那樣做。穿著怪模怪樣、陳舊衣服的老海因斯太太,從摩茲鎮追著中了魔的老頭到了杰弗生鎮。但她哪里又能阻止魔鬼纏身的老海因斯!她無法阻止老海因斯用槍劫回私奔的女兒,也無法為難產時掙扎的女兒請醫生,眼睜睜看著她死去。
克里斯默斯被外祖母辛苦撫養了幾個月后,被老海因斯偷走丟到孤兒院里。老海因斯太太整整30年沒有見這個孩子,“從來沒有見過他獨立行走,沒叫過一聲他的名字”(福克納:249)。在看護莉娜生產時,她恍惚中產生了幻覺,時空交錯,以為是30年前女兒米莉在生小孩。在杰弗生鎮,她在監獄終于見到了被私刑處死前的外孫克里斯默斯。她竭力想讓外孫死得體面一些的卑微愿望最終也破滅了,克里斯默斯還是被珀西·格雷姆私刑處死。
克里斯默斯的情人伯頓小姐像莉娜一樣也是位孕婦。但她卻沒有莉娜那種大地母親般的坦然,從從容容地孕育出一代又一代的兒女。在杰弗生鎮,離群索居的伯頓小姐是個異類,住在黑人聚居區一座孤零零的樓房里。由于她的祖輩是來自北方的廢奴主義者,她自身還在慣性地堅持著父輩的工作。當情欲使她與克里斯默斯走近時,克里斯默斯一下就看穿“她正在努力成為一個女人,但不知道該咋辦”(福克納:160)的心思。而克里斯默斯自己“知道永遠不可能弄清楚自己究竟是誰,他對自己靈魂唯一的救贖就是拒絕任何人,生活在任何人之外”(Vickery:3)。這種身份混亂的危機使這對情人到了你死我活的境地。克里斯默斯不想被頭發剛剛花白的伯頓小姐套牢;伯頓小姐則欲生下胎兒并讓他接手自己幫助黑人的業務,克里斯默斯卻“不肯在白人社會中承認他是個黑人”(俄康納:170),“新英格蘭冰河凄厲的狂怒突然遇上新英格蘭神圣的地獄火焰”(福克納:172-173)。最終,懷揣手槍的伯頓小姐死在了克里斯默斯的剃刀之下。他一刀兩命。
克里斯默斯的養母麥克依琴太太像是丈夫身后的影子。麥克依琴冷酷無情、頑固偏執,而她是“一個善于忍耐、精疲力竭的可憐動物,渾身沒有性別的標志,除了整齊地夾在一起的灰白頭發和裙子”(福克納:110)。從克里斯默斯五歲進這個家起,她一直千方百計待他和善,非常迫切地表現對養子的好,反被他譏笑為“那種種細微笨拙而又徒勞無益的努力,都出于她受盡挫敗的遭遇和她拙劣愚蠢的本性”(福克納:112)。夾在心理扭曲的養子和頑固、暴戾的丈夫中,無論她如何好心待他,克里斯默斯都憎恨她的溫情善意甚至超過懲罰。對麥克依琴太太來說,最終塵埃落定,養子為了暗娼用凳子砸死她的丈夫,遠遁他鄉,拿走了她一角一分偷偷為他攢的錢。
莉娜和克里斯默斯在小說中自始至終沒有見面,她作為參照物而存在,為這樣一部充滿扭曲、暴力、殘忍的小說涂上一層亮色。圍繞著克里斯默斯的四位母親,她們在克里斯默斯的生命鏈上,努力過卻改變不了他的命運,只是惡化了自身的命運。生母米莉給了他生命,也開啟了他的悲劇命運;外祖母老海因斯太太要接替難產而死的女兒撫養這個孤兒,但阻止不了老海因斯對孩子的迫害,孩子幾個月大就被他從家里偷走扔進孤兒院;養母麥克依琴太太也竭力給孤兒溫暖,只換來憎恨和自身更悲慘的命運。情人伯頓小姐和克里斯默斯像兩頭角力的野獸,因情欲而吸引,因信仰和身份而相互殘殺,死亡拉上了斗爭的帷幕。
三
在小說的開始,也有一位引人注目的母親角色,那就是阿姆斯特德太太。農夫阿姆斯特德出于好心,讓大腹便便的莉娜搭乘他的馬車并借宿在他家。
拉扯大五個孩子的阿姆斯特德太太,從丈夫的三言兩語對莉娜的敘述中,就看穿了這個年輕女人的窘境,十分懷疑誘奸了莉娜的伯奇“會在那兒等著,把房屋家具一切都準備好了”(福克納:10)。在阿姆斯特德太太眼里,莉娜只是一個被男人欺騙而心甘情愿蒙在鼓里的糊涂女人。當莉娜講述自己和盧卡斯·伯奇的故事時,阿姆斯特德太太冷峻輕蔑地看著她,不留情面地戳穿了無賴盧卡斯·伯奇以及莉娜為他做的辯解。莉娜依然心平氣和、卻固執己見地對阿姆斯特德太太說:“我想小孩出世的時候一家人應當守在一起,尤其是生第一個,我相信上帝會想到這一點,會讓我們團聚的。”(福克納:14)阿姆斯特德太太則不耐煩地說,上帝也只好這么辦了。
晚上阿姆斯特德太太找出自己藏得嚴嚴實實的瓷公雞,敲碎后拿出錢,囑咐丈夫:“太陽一出來就套上騾子,領她離開這兒。”(福克納:14)第二天當莉娜離開前,她起來做好了早飯就故意躲了出去,卻出乎意料地把一分一角攢的賣雞蛋得的錢讓丈夫轉交給這個她看不起卻理解同情的外鄉女人。在四個星期目的地不明的徒步旅行中,只帶了三角五分錢的莉娜之所以沒有風餐露宿,衣衫襤褸,無不是因為有阿姆斯特德夫婦這樣的鄉親,出手相助,才一路順利地到達杰弗生鎮。像阿姆斯特德太太這樣的母親也許是母親層面上最普通最常遇到的類型,恪守婦道、吃苦耐勞、勤儉節約、含辛茹苦撫養兒女。
而在故事發生的杰弗生鎮,“鎮上的永久居民,他們以往的個人生活,不同的家庭背景在小說中很少被關注”(Millgate:45)。不管是“人們”,“鎮上的人”,“女人們”,都有著基本上無差別的對社會和種族的態度以及宗教信仰。母親角色,除了有孕在身的伯頓小姐外,沒有被特別描述或提及。這可能基于,杰弗生鎮的人們在小說的構建中,有著共同的“對社會現象的接受和抗拒,以及對小鎮以外陌生人的態度”(Millgate:45)。也就是說他們是作為一個整體出現的。
《八月之光》中的母親角色幾乎都是處于不利地位的配角,根植在美國南方這塊有著獨特文化、獨特傳統的土地上。她們經歷了生活的種種磨難,卻不失生活的勇氣和執著,代表了生活本身——不管發生了什么,日子還要繼續。《八月之光》中大多數男人,如克里斯默斯、老海因斯、格雷姆等,都帶著一種獰厲的面貌。不斷衍生的矛盾、不斷的彼此傷害,冷漠、殘忍、暴力、焦躁,這些情緒永遠縈繞在小說中。莉娜、米莉、麥克依琴太太、老海因斯太太和阿姆斯特德太太等母親角色,平衡了小說的氛圍和格局,也推動了情節的發展。
作者簡介:邵 娟,上海電力學院外語系講師,碩士,研究方向為美國文學、商務英語。
參考文獻:
[1] 福克納:《八月之光》,藍仁哲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年版。
[2] 李文俊編:《福克納的神話》,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年版。
[3] 俄康納編:《美國現代七大小說家》,張愛玲、林以亮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88年版。
(責任編輯:水 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