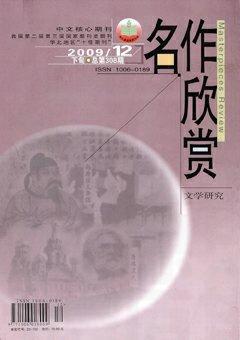沉默的自由空間
李紅波 彭 博
關鍵詞:沉默 語言 自由 空間 游牧
摘 要: 畫家出身的韓國導演金基德擅長使用畫面敘事,在電影《空房間》里,通過男女主人公的沉默,對人類使用語言和被語言支配的悖反困境進行了思索和抗爭,同時,還利用片中主人公的游牧生活方式,對僵硬的制度化空間進行了消解。
對于韓國導演金基德的電影《空房間》①,劉劍梅先生的看法還是相當精到的:“他的成功,一是把自己的繪畫特長引入電影,使電影語言與繪畫語言融合為一,畫面簡潔,內涵卻很豐富;二是他還很有思想,把詩意的思索也帶入電影,從而使影片不僅有繪畫性,而且有文學性。”②評論無疑從藝術性角度確認了這部特色鮮明、題材獨特作品的成功。筆者認為還有一種深藏于影片當中的哲學意蘊是有待發現的,可以從兩種極端現象感知這層內涵:一是男女主人公的長久沉默;二是自由空間的任意出入。
沉默的抗爭與多余的語言
影片的情節非常簡單,一個都市青年,后來才知道他是個大學生,開著摩托車,通過貼廣告的辦法探知房間的主人是否在家,如果確認主人不在家,他就小心地打開門鎖,到這個空房間住上一段,他日常所做就是做飯,洗衣服、澆花、鍛煉身體、整理相冊等生活瑣事,直到主人回來,他就再找另外一家,就這樣過著一種都市的游牧生活。故事的展開是他潛入一戶有錢人的家里,遭遇到女主人公——一位被其丈夫反鎖在家里的妻子,得知其遭到虐待的情況后,他用高爾夫球對其丈夫進行了懲罰,同時,帶著女主人公繼續其游牧生活。他們繼續闖進別人的空間,過著自己的生活,后來被女主人公的丈夫陷害,男主人公進了監獄,在里面練就真正的隱身術,出獄后潛入女主人公家里,和其丈夫三個人過著“匪夷所思的‘隱居的愛情生活”③。
這部影片與眾不同的地方不僅僅是離奇的情節,唯美的畫面,男女主人公長久的沉默才是最大的疑問。影片開始后,盡管周圍的世界眾聲喧嘩,男女主人公卻沒有一句臺詞,這讓人倍感驚奇,在一種等待男女主人公“說話”的焦慮心態中,觀眾的注意力完全與他們的命運同步而行,但是,影片只在臨近結尾處,女主人公才對那個虛實參半的男主人公說出一句“我愛你”。這是男女主人公在片中唯一的交談。思考男女主人公長久沉默的原因,應該說,與導演金基德的畫家出身有關,因為影片更傾向于畫面的敘事,而不愿對話壓制畫面的表現力,克拉考爾也曾指出:“凡是能使對話與畫面融為一體的影片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它們都為了恢復畫面的應有地位而抑制對話。”④不愿對話壓制畫面的表現力固然可以理解,但是,將沉默放大到極限而只流露一句簡單的“我愛你”,金基德似乎有意無意地提醒我們:生活中,真的需要語言嗎?
海德格爾的存在哲學認為,“人的所作所為儼然是語言的構成者和主宰,而實際上,語言才是人的主人。”⑤換言之,語言不僅是表情達意的工具,而且還成為束縛我們精神的重重厚繭。因為人類詩意的棲居不能離開賴以存在的語言,精神的游牧之地或棲居之歸根結底也只能在語言的園囿之中。在這個意義上,片中男女主人公固執而心靈相通的沉默,構成了對現代語言困境的最高抗爭。然而,他們的沉默并不是死亡式的,在長久的失聲中埋藏著至為強烈的愛情欲求,直到最終時刻才噴薄而出,使人震驚。讓我們回到那句簡短有力的獨白——“我愛你”。女主人公愛他什么?財產、地位還是名聲?這些,顯然他都沒有。而女主人公正身處豪宅,享有優裕的生活和良好的名譽,那么,她缺少的是什么呢?作為當代中國女性愛情宣言的詩歌,女詩人舒婷的《致橡樹》寫到,“這才是偉大的愛情,堅貞就在這里:不僅愛你偉岸的身軀,也愛你堅持的位置,腳下的土地”,對所愛之人身處之地的寬容接納比愛直接相關的身體具有更高的價值,愛情,在精神的意義上無關功利,也無關軀體,而關乎一種共通的生活方式。長久的精神孤寂與身體困鎖已經消除了這個女人發聲的機能,她成為一只等待拯救的籠中之鳥,她的喑啞預示著一種渴望,一種隨時叛離這個無愛巢穴的激情。對于男主人公游牧般生活方式的接受并不能說只是因為愛,而是因為這種方式代表著失而復得的自由以及平常人所能給予的人的尊重。愛情最初在這里只是一個標記,是在可有可無之間的,真正的考驗仍然來自現實的擠壓。女主人公丈夫策動的并不是一場對私通事件的圍剿,從道德的意義上看,他有著絕對充分的理由以正當的方式取回他對婚姻的權力。問題是這種取回是以空間剝奪的方式進行的。男主人公失去人身自由成為現實的囚徒,女主人公失去精神自由,成為行尸走肉。好不容易得到的自由生活頃刻之間就消失了,絕望激發了這個女人一直深埋心間的語言機能,這句三個字的愛情表白在完全失去空間的考驗面前雖然簡短卻感動人心,有什么比失去自由更渴望自由呢?有什么比陰陽兩隔更讓人感到愛情的凄美呢?也許我們被金基德的幻覺修辭所欺騙,那男主人公因越獄實際已經在獄卒的暴打之下喪生,可對于絕望等待的女主人公而言,他卻依靠特技成功脫生,重回身邊,相伴不離。那種不被任何人發現而只被女主人公看到的“隱身之術”不就是一個絕妙的雙關嗎?而這種超現實的想象不正說明在愛情的眼睛面前根本沒有空間的界限和物理的分隔嗎?這也許不是金基德個人的獨特體悟,但一定是藏于“隱身相見”童話之下的執著信念,是另一種無需語言的透明。
出逃后的女人和男主人公生活在一起,他們的生活習慣、情緒、道德、行動方式混同為一,既是對方的又是自己的,他們互相映射,互相穿透,一切交流都只依靠精神的默契,在詩性的動作中完成,語言從一開始就處在多余的位置。女人很快習慣了男主人公那種看似瑣碎的日常生活:做飯、洗衣服、整理相冊等,讓人不僅想到海子的詩:“從明天起,做一個幸福的人喂馬,劈柴,周游世界從明天起,關心糧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開。”這種平實感性的生活使人領悟到,原來像平常人一樣生活對于人們來說也是一種驚喜,甚至是一種奢望。中國道家講“大音稀聲、大象無形”,這種主張背后就是對語言的一種不信任;禪宗中的參話頭“問:‘何為佛,法師答:‘春來草自青”,就是通過阻斷日常思維,達到對語言的減少或消除。法國已故哲學家德里達把意義的產生推至一個前符號學階段,此階段的符號沒有能指和所指、實在和表征的區分,只有痕跡和聲音的物質化,其中的一切都沒有意義,亦無需意義,因為它是表達和意義一體、表征與存在不分的,以此映照意義的歷史,語言作為人為建構的形而上學特征就格外明顯了。所以,語言的出現并非人類文明的標志,而可能是人類墮落的開始,因為我們無法在一種自然而然的狀態下溝通,我們開始異化自己,于是隔膜、競爭、戰爭都出現了。因此,人類只要進入一種寬容的大愛之中,一定是不需要語言的。舒婷的《致橡樹》還說:“我必須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為樹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緊握在地下,葉相觸在云里。每一陣風過,我們都互相致意,但沒有人聽懂我們的言語。”“我愛你”,顯豁的是女主人公的心跡,而這種心跡關聯著的正是二人相處的無語生活。是啊!他們在說,只是沒有人聽懂。
自由空間與都市游牧
撇開法律或道德因素,男女主人公那種都市游牧生活確實有著令人著迷的地方:他們從容地出入于本不屬于自己的空間,不斷變換居住的環境卻固執地堅持自己的生活方式。這讓我們看到了空間的體制化傾向和對人的束縛。很多西方思想家認為,后天的制度在為我們制造賴以生存的物質空間的同時操控了我們對自由空間的感受,這些制度包括政治、經濟、文化、道德、法律甚至建筑物等。這些體制化的事物,不斷地強化我們的邊界感,提示我們,任何空間都是有邊界的,這些邊界客觀存在不容侵犯,我們只能遵守,無權反抗。難道真的是這樣嗎?很顯然,無論從何種原因上思考都不是,它們其實只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虛構,這種虛構造成自我的幻覺,就是說,即使我們被一種制度化的事物所塑造,我們也根本無法覺悟,相反感到“自然而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認為,這些空間概念是權利強加給我們的,是制度規訓的結果,劃出邊界就是為了便于統治,這些邊界就像一只只眼睛監視著你,使你不得不檢點自己的行為,收起那些自然真實的人性,慢慢變成一個可以“被度量的”理性個體。就這樣,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就區分出自己的房間、居所、故鄉等三維空間,但是對一種真正自然的在三維空間之上的自由空間,反倒失去認知能力。如果擺脫這些制度化的邊界約束,制度對我們的限制就立刻消失,我們就會生活在一種空無之中,一種在體制化的三維空間之外的“自由空間”。
片中的男主人公從我們習慣的機械生活中逃逸,一直悠然地生活在這種自由空間之中,反復地進行一項項傳統的感性生活操練。他對制度化空間的抵抗以一種無聲的方式進行,用異樣的眼光注視著體制內的一切,很多的荒謬和丑惡在這雙眼睛的凝視之下暴露無遺,他闖入每一家,就是對每一家故事的透視,都是現代人體制化生活悲喜與愛恨的集中呈現,順著這雙體制外的眼睛我們依次看到孩子拿槍射母親——家庭教育的失敗;男人虐待女人——上流社會的男權和虛偽;婚外情——夫妻間的不信任;孤獨老人凄涼死去——現代社會人情的冷漠;獄吏虐待囚犯——法律制度的腐敗……這種都市的游牧其實并不詩意,因為他在凝視的同時也在滋長恨意,內心漸趨失衡,無奈的觀望終于變成對故事的干預,他無法再保持對所侵入家庭不加改動的初衷,現身進入一個家庭的生活。我們可以把這種轉變看成是對這個女人的欲念與沖動,或者干脆說是愛情間的吸引,但從隱蔽的自由空間跨入現實的熱情之舉無疑最終葬送了他的游牧生活和整個生命。無論他和女人怎樣一次次潛入別人的生活,無論他看到多少別人的秘密,這個自由空間的存在始終需要一個合適的距離和無聲無息的姿態,保持克制、耐心和冷漠,一動不動地潛伏,這就是神奇隱身術的無上法則,不讓任何人發現,意味著要將自己隱匿于面前的世界,一旦發出聲響,不僅空間頃刻消失,而且自己也將無所遁形。我們借助男女主人公所見引發的所有反思,并不一定指向他們的實際思考。但是,長久沉默所顯示的個人立場,似乎很容易將我們的思考推及真實空間中諸多秘密的是非成因以及制度的偽善后果。僅從個體形象來看,他們并不懼怕現實的目光,但卻執著于躲藏和失聲的游戲,這里面是否暗含著一種宗教性的崇高意味?他雖不追償罪惡,但是極力發現罪惡。如果真有上帝存在,他也一定居于這個自由空間之中,雖洞悉一切,但卻默然無語,我們內心的善苗和惡根在他面前同等地蒙受寬恕。空房間并不是無物的房間而是一個讓人自思救贖之道的精神空間,人們從中發現自身早已隱居的感性和自然,只不過金基德大概實在找不出更好的方式來震醒我們早已昏昧的心靈,除了借助這樣一個超現實的凄艷寓言。
作者簡介:李紅波,文學博士,河南教育學院中文系講師、影視教育研究所成員,主要從事文學基礎理論和影視教育研究。彭 博,河南教育學院教師。
① 有的地方把片名翻譯為《空房誘奸》或《空間情人》,筆者認為過于直露,有挑人欲望之嫌,偏離了影片精神實質,“空房間”的譯名則極富韻味地傳達出影片深沉的一面。
② 劉再復新浪博客,《都市中的隱形人》,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d081e90100c6tl.html。
③ [德]齊格弗里德*克拉考爾:《電影的本性》,邵牧君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147頁。
④ [德]海德格爾:《演講與論文集》,孫周興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199頁。
(責任編輯:范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