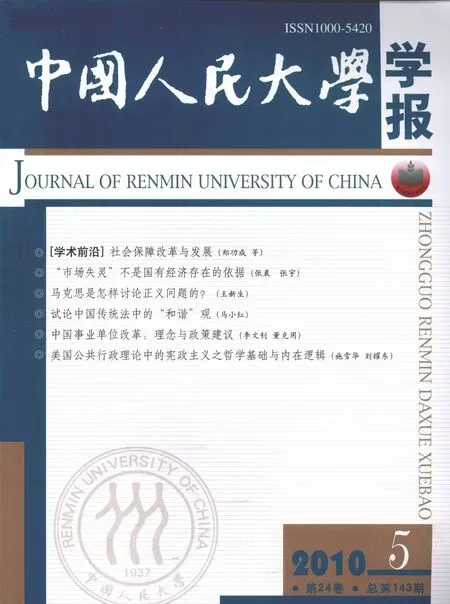民事審判中的村規民約與基本權利
劉志剛
民事審判中的村規民約與基本權利
劉志剛
村規民約既承載著實現村民自治的憲法使命,同時又具有解決鄉村民事糾紛的“私法”功能。在民事審判中,它往往是法院用來解決民事糾紛的事實上的依據。在基本權利適用于民事審判的背景下,村規民約與基本權利二者之間往往存在著邏輯上的關聯,該種關聯由以存在的共性場景是法律缺位。在該共性場景之下,二者在民事審判中的適用不存在絕對的先后次序,而是呈現出一種平行的、互動的外在面向。村規民約與基本權利在民事審判中不可能直接適用,它們適用的共同管道是公序良俗原則。
民事審判;村規民約;基本權利
首先,雖然我國現行《憲法》第8、9、10條確立了農村的集體所有制,但是除卻上述憲法規定和為數不多的少數法律規定之外,國家并沒有關涉農村集體所有制的相關法律規定。這事實上意味著國家一方面通過對土地、自然資源的集體所有的確認將村民們制度性地凝聚在一個小共同體之內,另一方面卻又沒有進而給這個小共同體提供相關的秩序型構規則。
其次,1998年通過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農村實行村民自治,村民委員會是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對村民委員會的工作給予指導、支持和幫助,但不得干預依法屬于村民自治范圍內的事項。這實際上意味著農村社區是脫離于國家行政管理體制之外的,國家立法機關沒有、也不應該提供相關的社區秩序管理規則,政府也沒有對社區內部秩序進行行政管理的依據和責任,農村的內部秩序主要通過村規民約、村民委員會來疏導。
再次,基于農村現行的集體所有制制度以及各地農村所存在的地域差異,國家目前沒有關于農村內部公益事業方面的具體規定,像兒童入學、老年人入養老院、環境衛生等方面的問題,更多地屬于村民自治的范疇,主要通過村規民約來凝聚民意并進而在村里付諸實施。
在上述諸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下,鄉村中形成了事實上的“法律不入”之地,鄉村社會秩序的調整結構性地由國家轉移到了村規民約的肩上,而后者在民主程序的框定之下,也顯現出了與鄉土民情、社會倫理的內在相宜性,成為化解鄉村社區民間糾紛、整合鄉村秩序的重要機制。然而,立基于鄉村民主多數同意基礎之上的村規民約并不能確保其獲得鄉村社區中每一個村民的同意或者恒久支持,當村民個體的利益在村規民約作用的場景下面臨著現實沖擊的時候,一些具有憲法觀念的村民便在自身功利主義的驅使下將村規民約整合下的民間沖突呈送至法院,謀求借助司法的力量將基本權利的精神滲透到鄉村社區。這樣一來,先前獲得村民多數同意、并在法律缺位的場景下維護和調理著鄉村秩序的村規民約便面臨著來自司法的消極檢視,基本權利也便在民事審判中和村規民約出現了邏輯上的關聯。
傳統憲法學理論認為,基本權利是指向于國家公權力機關的一種權利,對私人之間的民事糾紛沒有實際的意義。但是,自20世紀以來,由于國家職能的結構性轉移、承擔公共職能的私人團體的出現以及立法不作為引發的基本權利的虛置等諸多方面的原因,基本權利面臨著來自私法主體的現實侵害。基于對該種情勢的因應,基本權利的目標指向出現了拓展,由先前單一指向于國家公權力機關轉變為同時也可以指向于私法主體,民事審判中開始援引基本權利來處理和解決民事糾紛。但是,基本權利畢竟不同于民事權利,它在民事審判中的適用是有附加條件的。就適用前提來說,基本權利只有在法律缺位的情形下才能夠在民事審判中適用,否則就會有損于法律所承載的多數民主制度。從理論上來說,法律缺位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
其一,相關民事法律規定的缺位。也就是說,法院在處理和解決民事糾紛的時候,首先要考慮的是作為民法之淵源、法院裁判之準椐的法律是如何規定的,只有在沒有上述法律規定的情形下,才能夠考慮適用基本權利來處理和解決民事糾紛。
其二,具體形成基本權利之內容的其他相關法律的缺乏。也就是說,載明于憲法的基本權利僅僅是一個關涉權利的總括性名稱,其具體內容需要通過法律來加以充實和具體化。只有在此類法律缺位的前提下,法院才能考慮適用基本權利來處理和解決相關民事糾紛。
那么,作為基本權利在民事審判中適用之前提條件的法律缺位究竟指的是上述哪種意義上的法律缺位呢?筆者認為所指的應該是前者。在筆者看來,兩種類型的法律缺位所反映的不是同一個層面的問題。就前者來說,它所牽涉到的是基本權利與作為民法之淵源、法院裁判之準椐的法律之間的關系。兩者相比,法律無疑是應該優先適用的。畢竟,憲法中所確定之基本權利,僅僅是一個權利的名稱而已,并沒有關涉該基本權利內容方面的規定,需要通過法律加以具體化。對普通法院來說,它所需要做的是依據已經存在的具體法律來審理民事案件,而不是動輒上升到憲法層面,從憲法中去尋找權利乃至對其所找尋到的基本權利進行內容上的挖掘。否則,作為憲政之基石的民主多數機制將在普通法院基于“神圣使命”感的推動下而進行的挖掘中被侵蝕乃至根本摧毀。普通法院的職責僅僅是依法審理案件,而不是檢視法律本身存在的缺誤。因此,在民事法律存在的前提下,法院所需要做的就是依據民法審理案件;只有在相關民事法律缺位的前提下,法院才能夠適用基本權利來處理民事問題。與前種類型的法律缺位相比,后者所牽涉的實際上是基本權利與形成其內容的、且與民法無甚瓜葛的其他法律之間的關系。也就是說,在前種類型的法律缺位已經確證、且進而關涉到援引基本權利去處理該民事糾紛的前提下,權衡決定應該直接援引憲法中的基本權利條款還是通過援引形成基本權利內容的相關法律,從而間接達到援引基本權利條款之效果的問題。按照后者的基本思路,只有在形成基本權利內容的其他相關法律也缺位的情形下,才能進而援引基本權利條款處理相關民事糾紛。對此,筆者不以為是。
“齊玉苓案件”發生之后,圍繞基本權利條款與其他相關法律規定在民事審判中的關系問題,法學界進行了討論,大致有三種觀點,即“法律優先適用說”[6](P327-333)、“憲法、法律平行適用說”[7]、“折中說”。[8](P168)上述觀點折射出一個焦點問題,即基本權利條款與為具體法律所具體化了的基本權利之間的關系問題。該問題在邏輯上和上述第二種類型的法律缺位實際上是關聯在一起的。筆者認為,從邏輯上來說,法院固然可以通過援引形成基本權利內容的其他法律來達到適用基本權利的效果,但是,必須警醒的是,為其他法律所具體化了的權利在性質上并不是基本權利,而是法律權利;而且,該種權利因為刊載于公法之中,在目標指向方面往往具有不同于私法權利的秉性。在依法裁判的行為準則之下,法院怎么可能一方面援引該種權利,另一方面卻又背離法律的字面規定、改變該種權利的目標指向呢?誠然,民法并不僅僅表現為純粹意義上的民法典或基礎性的民事法律,其他法律規范也是承載民法內容的重要載體。但是,在公、私法界分的語境下,不同類型的法律在性質、關系結構、功能面向等方面是存在差異的,前者與后者的關系在民法的語境下更多的是一種一般民法與特別民法之間的關系。前者肩負著實現“私法自治”的使命,后者卻承擔著限縮“私法自治”空間的職責。與前者相比,后者的民法功能在直觀層面上主要顯現為確立前者不得違反的框架基礎,而不是賦予民事主體以相關的權利和活動的自由;而且,其他相關法律并不必然成為承載民法內容的特殊民法,該種面向的具備必須依托于該類法律中包含有關涉民事內容的相關條款,否則,它就與民法無甚直接的瓜葛。以其是基本權利內容的具體化為由而將其當作基本權利予以適用,是對法律權利地位的拔高,更是對依法裁判原則的違反;以其作為審理民事案件的直接依據,更是混淆了公法與私法之間的界限,是對民法精神的踐踏和公法之本來面向的扭曲。
因此,筆者認為,基本權利在民事審判中得以適用的前提——法律缺位,在內涵上所指向的只能是第一種類型的法律缺位,至于后者,只能作為法官裁斷私法行為是否侵害到基本權利的判斷標準。
二、村規民約與基本權利在民事審判中適用的位階關系
(一)村規民約是否可以作為民事審判的依據?
村規民約是與習慣關聯在一起的,該范疇本身并不具有獨立的法源意義,它在民事審判中的意義主要取決于它在語詞上所依附的“習慣”在民法中所處的地位。此處,筆者試圖從實證和應然兩個角度展開對本問題的剖析:
第一,在法律語言邏輯上對村規民約產生“蔭庇”功效的“習慣”在民法中所處的現實地位是什么?從實證的角度來看,在當代中國的法治話語中,習慣所處的地位并不高。“只有法律承認其有效的習慣,才能作為制定法的淵源。”[9](P315)“中國當代的制定法,除了在涉及國內少數民族和對外關系的問題上,一般是輕視習慣的。”[10]2008年,有民法學者指出:“在中國,到目前為止明確提到風俗習慣的法律法規在數量上共有大約170余件,但其大多數都是出現在行政法規中。真正與民事法律相關的,除《物權法》第85條等少量法律條文之外,大多數是涉及婚姻問題的司法解釋。”[11]在上述制定法的語境之下,習慣原則上是不具備由以在民事審判中適用的正當性的,蔭庇于它的村規民約自然也就不能成為法院進行民事審判的依據。然而,從司法實踐的角度來看,法官卻秉持了一種與制定法精神不甚吻合的行為邏輯。在審判實踐中,法官實際上“穿梭在制定法與習慣之間”,選擇性地允許習慣性規則進入司法,“修改或置換制定法”。[12]這種狀況使得前述權威法理學者關涉習慣所處法律地位的表述在一定程度上被修正,給人留下的外在觀感似乎是:習慣是否可以作為制定法的淵源,并不一定在于它是否獲得了法律的承認,而在于它是否被法官選中。在法律沒有確認習慣效力的場景下,法官基于解決糾紛的“現實需要”,也可以援引習慣作出裁判,這在民事裁判中表現得尤其明顯,由此使包括村規民約在內的習慣在民事審判實踐中處于一種非常曖昧的狀態。
第二,習慣,或者更為直接地說,蔭庇于習慣的村規民約是否應該在民事審判中適用呢?對此,筆者秉持肯定的立場。從文本分析的角度來看,習慣在中國傳統社會所處的法律地位也不高,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該時期法律秩序的格局也是如現今時代這般處于法律一枝獨秀的狀態之中。恰恰相反,以“鄉例”、“民俗”等小傳統表現出來的習慣在維護傳統中國社會的法律秩序中一直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13]只不過,由于中國古代的律法多為刑法規范、且官府處理民間詞訟往往以調處為主,既不援引律例,也不依據民間習慣,因此,民間習慣與民事審判規范之間并不存在直接的關聯,它自然也就在制定法層面呈現出與現今時期相同的外在面向,從而引起其他法域學者的誤解。[14]事實上,如果回溯一下傳統中國社會國家在私法層面對民間社會組織自治所秉持的一以貫之的授權和放任立場,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傳統社會的法律秩序實際上是通過國家制定法和民間習慣的分工合作、相互協調而實現的,習慣事實上起到了外在于制定法的、為國家所認可的“法”的功效,它所承載的國家秩序型構理念與事實上所起到的社會作用與現今時期我們所理解的、更為通用的法律定義是一致的。立基于此,基于習慣在制定法層面所呈現出的與現今時期相同的外在面向而推導出文化決定論的立場,并進而作為否定在民事審判中適用包括村規民約在內的習慣的理由是無法成立的。與傳統中國社會相比,現今時期制定法所呈現出的、關涉習慣所處地位的外在面向就不具有類同于先前時期那般的制度及社會依托,法官辦案中所顯現出的“在制定法和習慣之間往來穿梭”更多的是出于一種對社會現實問題的消極因應,而不是像先前時期那般、具有植根于所處社會大背景下的正統性。在依法裁判的語境下,法官援引習慣作出裁判的行為往往具有與生俱來的不正當性,要受到來自實務和學理層面的雙重檢視。究其原因,可以歸結于中國的法律現代化。[15]在法律現代化的時代背景下,國家關注的重心是通過國家強制力的推動,盡快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現代法制,其目標指向是移植借鑒西方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法律制度,即所謂的同國際社會接軌。在這個問題上,學界所達成的共識與國家的立法走向是一致的。在這種背景下,學界和國家立法部門在對習慣的立場上出現了一種“社會學意義上的合謀”,這不僅使得習慣在制定法中所處的地位非常尷尬,處于近乎被邊緣化的狀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汲取了法官援引習慣進行民事審判的理論依托,使其裁判行為在理論基礎上顯得非常單薄。這樣一來,法官就不得不“在制定法和習慣之間往來穿梭”,既要顧及法律缺位狀態下鄉村秩序型構的現實需要,又要考慮到施加于自身的“依法裁判”的剛性準則,以求在這一理想和現實的夾縫中盡力塑造自己所做裁決的正當性。筆者認為,與其像目前這樣使村規民約在制定法和司法實踐中呈現出不同的邏輯面向,還不如通過某種妥當的方式從制度上賦予村規民約以民法淵源的法律地位,允許法官在民事裁判中援用。這事實上也是符合法治的基本理念的。依法裁判固然是法官行為的基本準則,但是,村規民約也并不是純粹鄉土性的民間習俗,它同時還承載著憲法賦予它的自治使命以及由此而蘊涵的憲法對其民間糾紛解決機能的認可和對“法律不入”狀況的默認。在憲法價值和法治準則同時并存的前提下,法官優先考慮的無疑應該是前者。
(二)村規民約與基本權利在民事審判中的位階關系
近年來,農村中圍繞村規民約問題引發的民事糾紛逐漸增多,爭訟雙方分別援引村規民約和基本權利來論證自身行為或者訴求的正當性,從而使村規民約與基本權利在民事審判中被關聯起來。從各地法院的具體處理來看,做法不一,由此使村規民約與基本權利在民事審判中的位階關系問題顯得有些曖昧。例如,在1997年發生于河南省鄭州市的“李麗紅訴鄭州市中原區中原鄉朱屯村村民委員會”案中,原告李麗紅向鄭州市中原區人民法院起訴,訴稱被告鄭州市中原區中原鄉朱屯村村民委員會制定的《關于外來人員入戶享受待遇的若干規定》違背《憲法》第48條第1款及《婦女權益保障法》第20條的規定,不應具有法律效力,請求中原區法院確認被告上述規定無效,并給原告以“村民待遇”。法院在判決中指出:“本院認為,村民委員會屬于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可以依法進行自治活動,被告鄭州市中原區中原鄉朱屯村村民委員會制定規范性文件屬于自治活動的范疇,未違反法定程序,且其制定的規范性文件在內容上設定享受村民待遇的條件并未違反《憲法》及《婦女權益保障法》男女平等的原則性規定,故原告稱這些規范性文件不具有法律效力,理由不足,法院不予采信。”[16]最后,法院依據上述村里所謂的“文件規定”處理了該案。與之相比,湖南省桃江縣人民法院在對一件類同案件的處理中,卻秉持了不同的立場。1999年,湖南省桃江縣人民法院公開審理了“肖建純等訴桃江縣桃花江鎮肖家山村梭關門村民小組”案。[17]在該案中,原告肖建純等六位出嫁女訴稱,被告此前于1994年4月制定的《梭關門村民小組承包責任制的各項規定》剝奪了她們作為組民應該享受的待遇。法院審理后認為:梭關門組制定的鄉規民約,剝奪了已婚婦女應享有分配的權益,違背了我國法律中男女平等的原則,該規定不具有法律效力。桃江縣法院鑒于該案的特殊性,多次組織雙方協調,并走訪和邀請有關部門做原、被告雙方的調解工作,但由于雙方分歧太大,無法達成一致意見。在多次調解無效后,法院于2001年4月作出一審判決:由被告村民組償付原告及其子女土地征收費各近5000元。
對上述案件進行分析后可以發現,兩個案件在如下方面存在類同之處:其一,原告訴求的直接理由都是被告方通過的村規民約侵犯了他們的平等權;其二,法院在審理該案件的過程中對相關村規民約都進行了審查;其三,法院最終對案件的處理是建立在對村規民約和基本權利的價值判斷基礎上的。上述問題在直觀的顯性層面盡管往往直接或者附帶地貫之以法律權利的名號,但究其實質,實際上是關乎基本權利與村規民約的價值平衡問題。說到底,就是法院究竟應該依據村規民約來處理案件還是應該援引基本權利來處理案件的問題。對此,筆者擬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
第一,作為上述案件中矛頭指向的村規民約由以產生并承載相關內容的背景是相關法律的缺位。上述案件中矛盾產生的根本在于,因外嫁、離婚、喪偶、再婚等婚姻狀況變化而流動的婦女,是否具有相關農村集體成員的身份?該種身份的具備是他們從相關農村集體獲得土地承包經營權以及其他相關權益的基礎。但是,該種身份的具備與否是根據什么標準來確定的呢?就目前來說,戶口是確定該種身份的重要依據。正常情況下,依據戶口是可以確定村民相較于相關農村集體的身份的。但是,由于該種身份的具備是和土地承包經營權以及其他相關權益關聯在一起的,而我國目前實行的又是以農村為單位的集體所有制,因此,該種身份的具備就有必要獲得該集體的同意和確認,否則,就有可能侵損到為憲法和法律所保護的集體所有制。那么,集體通過什么樣的方式來確定該種身份的獲取規則呢?從理論上來講,該種獲取規則應該由作為產權主體的集體來確定,但是,由于“在物權法上,所有制意義上的‘農村集體’永遠不能成為物權法的主體”,所以“農村集體的物權法主體地位問題,(實際上)是一個沒有答案的死問題”[18],因而,似乎只能套用《物權法》第59條的規定——“依照法定程序經本集體成員決定”。如是觀之,由承載集體意愿的村規民約來確定集體成員的身份是具有正當性的,這在某種程度上似乎應該理解為是國家有意為作為物權主體的“集體”留下的一個“法律缺口”。
第二,村規民約與基本權利在民事審判中的關系性質及位階問題。在上述兩個案例中,法院都對村規民約進行了價值判斷,并在價值判斷的基礎上作出了相應的處理。不同之處在于:在第一個案例中,法院援引村規民約處理了該案;在第二個案例中,法院在宣布村規民約因違反“法律中的男女平等原則”而無效之后,徑行在沒有法律規定的前提下處理了該案。對此,筆者有幾點質疑:首先,法院有對村規民約進行違憲審查、違法審查的權力嗎?從法律文本的角度來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等相關法律并沒有賦予法院對村規民約進行違憲和違法審查的權力;從理論上來說,村規民約既承載著實行村民自治的憲法使命,同時還肩負著物權法賦予它的行使“集體”物權的重托,由法院對其進行審查既是對自治的干涉,也是對物權的法外限制。其次,原告訴稱遭受侵犯的權利究竟是基本權利還是法律權利?顯然,原告訴稱或者法院確認村規民約侵犯法律權利的意圖是:在推翻村規民約的基礎上依據其他的規則來處理該案。然而問題的癥結在于:前述糾紛產生的背景是法律的缺位,而且,民事權利之外的、作為確證村規民約無效之依據的法律權利是不具有類同于基本權利那般的適用于民事審判的理論基礎的。更何況,在《物權法》第59條和《婦女權益保障法》第32條同時并存、且《物權法》第59條并沒有為特殊民法承載之價值理念的滲透預留入口的前提下,怎么能夠想當然地依據后者來確認符合《物權法》第59條規定的村規民約無效呢?因此,筆者認為,原告訴稱遭受侵犯的權利在性質上只能是基本權利,相關法律的規定只是其所對應的基本權利在內容上的具體化而已。
統合前述兩點質疑,筆者意圖申明的立場是:村規民約與基本權利在民事審判中的關系是一種平行的關系,它們都屬于法官進行民事審判的一種潛在依據。法官進行民事審判的前提不在于必須對村規民約違憲、有效與否作出一個先期的裁斷,而是應該在正視村規民約正當性的前提下,通過檢視其在程序上的缺漏并根據由此而獲得的內在確信,選擇性地援引上述兩種規則,以達致解決民事糾紛、實現社會和諧、滲透基本權利三種目的的統一。法官必須深刻地認識到:鄉土社會所秉持的是一種不完全等同于基本權利運作邏輯的、以互惠原則為前提的習俗秩序,“糾紛解決背后所持守的基本原則就是使原初的互惠關系得到恢復”,基本權利在鄉村社會的武斷滲透固然可以帶來微觀個體之間的平等,但由此而“放大到整個的村落社區所帶來的卻是一種社會的不平等”。[19](P133)二者之間不存在一種絕對的優先問題,而是應該因時因地具體權衡。
三、村規民約與基本權利在民事審判中適用的管道
如前所述,在法律缺位的場景下,村規民約與基本權利可以適用于民事審判中,作為法官裁斷案件的援引準則。但是,在依法裁判原則的拘束之下,法官通過什么樣的途徑才能夠把村規民約、基本權利合乎邏輯地引入民事審判中來呢?對此,筆者擬從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一)村規民約與基本權利不可能在民事審判中直接適用
從理論上來說,村規民約可以通過“習慣”這一具有法源性的制度性平臺進入民事審判之中,進而將其承載的物權主體之意愿彌散在據此而作出的民事裁決之中。然而,問題的癥結在于:在中國目前為止明確提到風俗習慣的170余件法律法規中,習慣多數出現在行政法規中,“真正與民事法律相關的,除《物權法》第85條等少量法律條文之外,大多數是涉及婚姻問題的司法解釋”。[20]這與村規民約存在并發生作用的場景不太一樣,村規民約事實上無法借助上述平臺進入民事審判。除此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可以借用的管道呢?考慮到中國長期以來政治話語主導的社會背景,有學者對制定法中有可能承載“習慣”之意蘊的其他語詞,如“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中國特色”、“地方特點(色)”等進行了檢索,經過分析之后認為:“后兩個關鍵詞在現有的中國制定法的語境中都不具有將習慣帶進制定法之中的可能,而‘具體情況’有可能。”但是,“同遵循‘習慣’相比,強調‘具體情況’有更多的弊端”。[21]立基于此,筆者認為,從法律適用技術的角度來看,制定法中唯一可以充當承載村規民約的直接運送管道就是“習慣”,但就目前制定法的現狀來說,這一路徑相較于村規民約在民事審判中的適用而言,事實上沒有什么實際的意義。
那么,如果將視角從實然的角度切換到應然分析的理論層面,制定法是否有必要進行適當的修正,將允許援用“習慣”的條款嵌入其相關環節之中呢?筆者認為沒有必要,具體理由有以下兩點:
第一,習慣與國家法之間的關系是互動的,而不是僵化的。習慣與國家法的價值取向不同,前者注重的是道德與人倫的立法秩序,后者注重的卻是法理秩序。中國法治發展的特有路徑決定了在較大程度上移植和借鑒西方法治理念的國家法與植根于鄉土社會的習慣之間存在沖突的必然性。正如國家法有可能存在缺陷一樣,習慣也有可能存在諸種問題,與前者相比,后者存在問題的幾率可能更大一些。因此,國家法與習慣之間的關系就不應該是一種絕對的以前者取代后者、或者根據地域劃界而治的問題,而應該呈現一種互動、整合的外在面向。基于不言自明的原因,這種互動、整合效果的達成不應該寄希望于制定法的永久框定,而應該依賴于包括司法在內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的建造以及法院在國家法與習慣規則之間進行選擇的適度自由。
第二,習慣與國家法之間的關系調適必須考慮到基本權利。習慣與國家法之間的關系固然可以置于法律既存的場景之下,外現為習慣與法律之間的關系,但法律缺位狀態下習慣與基本權利之間的關系也應該被納入二者關系的范圍之列。正如前文所談及的,法律缺位場景下法官進行民事裁判并不必然需要以對村規民約的違憲性作出裁判為前提,而是應該在正視二者存在正當性的前提下,選擇性地援引上述兩種規則,以謀求“以互惠原則為基礎的鄉土秩序”能夠盡可能地汲取蘊涵普世價值的基本權利滲透過來的陽光。顯然,上述目標的達成依靠對二者適用順序的僵化定位是無法實現的,通過在制定法中嵌入“可以援引習慣”的授權條款從而使基本權利在事實上處于被排斥狀態的做法更是無助于該目標的實現。統合前述,筆者認為,村規民約不可能在民事審判中直接適用。
目前,關于基本權利在民事審判中的適用問題,多數學者持肯定的態度。但是,對于基本權利條款在民事審判中如何適用,學界存在較大的分歧。筆者認為,基本權利在民事審判中不可能直接適用,具體理由有以下兩點:
第一,基本權利具有完全不同于私權利的稟性。與私權利相比,基本權利的基本立足點在于限制國家權力,而不是對私人間關系的調整,憲法權利的大范圍私法適用將導致憲法權利體系的紊亂,傳統憲政理念將憲法權利固著于公權之一端,有其內在的正當性基礎。基本權利在性質定位和功能等方面都具有不同于私權利的特性,這些差異決定了基本權利不適于被當作私權利適用。在現代社會條件下,盡管由于諸多因素的推動,基本權利開始進入私法層面,在民事審判中發揮一定的作用。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傳統憲法學理論所指出的基本權利私法適用所產生的風險已經不復存在,恰恰相反,現今的憲法學理論和司法實踐只不過是在正視前述風險存在的前提下,盡力謀求該風險與推動基本權利“私法”適用的諸種因素的協同而已,基本權利在民事審判中的間接適用就是這種努力的成果。
第二,基本權利直接適用于民事審判將導致其對村規民約的結構性取代。基本權利和村規民約都具有憲法上的正當性。前者承載的是憲法上的人權保障理念,后者承載的是實現村民自治的憲法使命。從根本上說,實現村民自治也是為了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村民自治的運行固然應該盡可能地尊重基本權利,但是,該種尊重必須以維系村民自治的存在為前提,而不是以村民自治制度的坍塌為代價。從實踐來看,承載村民自治精神的村規民約往往和鄉村社區的風俗民情、倫理道德具有內在的相宜性,普世性的基本權利在鄉村社區的武斷輸入往往會在事實上造成整個鄉村秩序的瓦解,進而使村民自治喪失其實質意義。立基于此,基本權利精神在鄉村的滲透就應該是適度的,而不應該浪漫主義地幻想在目前的社會背景下能夠將基本權利的陽光普照到整個農村社區。相應的,它和村規民約的關系就應該是互動的,而不是對村規民約的徹底取代。但是,基本權利在民事審判中的直接適用恰恰意味著對村規民約的結構性取代。
(二)村規民約與基本權利進入民事審判的管道——公序良俗原則
對此,筆者從以下兩個角度進行說明:
首先,公序良俗等民法基本原則在民事審判中適用的必要性。從理論層面來看,法律原則在司法實踐中的適用有其存在的正當性。目前,國外學者對此已經基本形成了共識,司法實踐中依據法律原則進行裁判的做法也屢見不鮮,梅迪庫德和德沃金在各自的論著中為我們提供了一些這方面的鮮活實例。①相關案例可參見迪特爾·梅迪庫德:《德國民法總論》,515頁,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德沃金:《法律帝國》,14頁以下,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在國外學者的視野里,法律原則往往被當做對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進行必要的限制、借此打造其所做裁決正當性的工具。[22](P371)與之相比,由于我國民法對能否直接適用民法基本原則作為法官審判的依據沒有作出明確規定,因此,國內對于該問題在比較長的時段里,理論上一直存在爭議,實踐中法院的做法也不盡一致。早在1994年,國內就有民法學者指出,鑒于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生活的復雜性以及民法規范本身所固有的局限性,我國民法應當在立法中明確規定民法原則可以直接適用于具體案件。[23]此后,民事審判實踐中也陸續出現了一些依據民法基本原則進行裁判的案例。2001年,圍繞四川省瀘州市納溪區法院審理的“張學英訴蔣倫芳遺贈糾紛案”,學界進行了廣泛討論,總體上呈現為兩種立場:其一,法律規則較之于模糊而不確定的法律原則,具有具體性和確定性,應該優先適用[24](P74);其二,法律原則是法律規則的基礎,應該秉持原則高于規則的立場。二審法院所秉持的就是該立場,它在二審判決中指出:“公序良俗原則在法律適用上具有高于法律具體規則適用之效力。”[25]從法院秉持的立場以及學界對該案件討論的具體情況來看,盡管對原則與規則在司法適用中的先后順序尚有不同意見,但是,對于法律原則在司法中的適用問題卻是已經基本達成了共識。
現今時代,對法律原則在民事審判中適用問題的檢視,似乎應該一如法理學者在時隔數年之后評析該案時所指出的那樣,必須深切地認識到:“當下法規范的總體概貌可用‘立法極簡主義’一言而得以蔽之,其中,大量的法律漏洞以及類似于哈特所言的‘空缺結構’尤為顯見,而在一定程度上可有效彌補種種規范缺失的判例制度則尚未建立,龐大駁雜的實施細則、司法解釋乃至‘審判紀要’幾乎在實務中處于法規范的主導地位,并可能與既有的法規范構成沖突。凡此種種法秩序的存在狀況,均過當地徒增了在司法實踐中適用法律原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26]如是描述和斷言,或許應該是我們對該問題秉持的基本立場!
其次,村規民約和基本權利對公序良俗原則的客觀化塑造。公序良俗是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的簡稱,是傳承于法國、意大利、日本以及我國臺灣地區民法典中的一個概念,德國民法典中將其稱為善良風俗。我國現行民事立法中沒有直接采取公序良俗這一稱謂,《民法通則》第7條、《合同法》第7條中使用了“公共利益”、“社會公德”兩個術語,國內一些民法學者將其視為公序良俗原則在我國現行法上的體現。[27](P47)一般認為,“公序良俗原則具有克服規則模式僵化、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權、追求實質正義、拓展私法法源、溝通私法與外部法律秩序及倫理秩序等重要功能”[28],這使得它“在今日已為私法上之最高原則”。[29](P335)在法律原則適用于民事審判的聲浪中,公序良俗原則越來越被作為控制私法自治的過濾器和塑造法官裁決正當性的工具。但是,由于公序良俗原則在內涵及外延上的高度不確定性,使得它在較大程度上顯現為一種價值判斷,而不是一種內容明確的可操作性規則。在法律原則應該適用于民事審判的共性體認下,法官完全有可能通過公序良俗這一制度載體,將自身的價值判斷注入其中,進而催生出具有形式正當性的裁決。這樣一來,不僅該原則之過濾私法自治的原初目的難以實現,而且先前寄托于其上的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意圖很有可能反而蛻變為法官對自身價值理念進行邏輯走私的正當性工具。要消除該種風險,就必須對公序良俗原則進行“客觀化”塑造,使它獲得由以適用所必需的正當性。如何對其進行“客觀化”的再塑造呢?筆者認為,村規民約和基本權利就是對其進行“客觀化”塑造的重要手段。通過它們的塑造,不僅公序良俗原則適用所必需的正當性將由此而獲得,而且村規民約和基本權利也將因之而獲得進入民事審判的管道。對此,筆者從以下兩個角度加以說明:
第一,村規民約與法官的自由裁量相比更具有規范性。公序良俗原則本身并不存在一個客觀的標準,“它只是為法官提出一個方向,要他朝著這個方向進行裁判,至于在這個方向上法官到底可以走多遠,則讓法官自己去裁判”。[30](P147)這事實上等同于將“公序良俗”原則的話語主導權完全交付到了法官手中,而法官對其內涵的宣示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個人的內在修為,這就使當事人難以獲得對法院裁決的穩定預期。相比之下,村規民約卻具有更為規范的意義。在正常情況下,它往往是對相關地域之風俗民情、生活習慣的文字化確認,它的內容中凝聚了鄉村社會的環境特征、人的自然稟賦以及人與人之間的沖突及其解決的信息,是村民們在反復博弈后形成的日常生活中必須遵循的行為定式。以之作為充實公序良俗原則的內核,不僅可以實現對該原則的“客觀化”,而且,由于它和鄉村社區的內在相宜性,也可以由此獲得法院裁決的社會信服力。
第二,憲法中的基本權利條款是確保法官所注解之“公序良俗”原則內置于“法秩序”之內的重要依據。對于法律原則的“客觀化”問題,西方學者進行過較為深入的討論。針對法律原則適用過程中有可能存在的風險,德沃金曾經指出,原則的適用對于消除上述缺憾顯然是必要的,但是,所適用的原則本身必須既能夠符合或證明既存的實定法,又能夠在道德上是最佳的。[31]但是,如何才能確保這一目標的實現呢?拉倫茲指出:“這種法的續造當然不能抵觸法秩序的一般原則及憲法的‘價值秩序’。事實上,惟其與之一致,其始能被正當化。因此,此種法的續造雖然在‘法律之外’,但仍在‘法秩序之內’。”[32](P321)顯然,兩位學者所指稱的“憲法之價值秩序”或者“憲法規則”主要是指憲法中的基本權利條款。
統合前述,筆者意圖申明的立場是:村規民約與基本權利在民事審判中只能間接適用,它們的適用管道就是民法中的公序良俗原則。借助該原則,它們不僅可以將自己承載的風俗民情和人權保障理念輸入民事裁判之中,而且可以通過法官對該原則的制度性適用,使二者在民事審判的過程中達致動態平衡。更為關鍵的是,村規民約所承載的實現村民自治的憲法使命和基本權利所蘊涵的人權保障的憲法精神將在這一動態的平衡過程中達到最佳的兼容狀態。
[1] 蘇力:《送法下鄉——中國基層司法制度研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
[2] 蘇力:《法治及其本土資源》,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
[3][4] 田成有:《鄉土社會中的國家法與民間法》,載陳金釗:《民間法》,第1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
[5] 王銘銘:《鄉土社會的秩序、公正與權威》,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
[6] 參見胡錦光:《憲法的司法適用性》,載徐秀義、韓大元:《現代憲法學基本原理》,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0。
[7][8] 陳雄:《論訴訟中的中國憲法適用》,載《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01(2)。
[9] 沈宗靈:《法理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10][15][21] 蘇力:《當代中國制定法中的習慣——一個制定法的透視》,載《法學評論》,2001(3)。
[11][20] 姚輝:《論民事法律淵源的擴張》,載《北方法學》,2008(1)。
[12] 蘇力:《中國當代法律中的習慣——從司法個案透視》,載《中國社會科學》,2000(3)。
[13] 梁治平:《清代習慣法》,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
[14] 勒內·達維德:《當代主要法律體系》,487頁,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滋賀秀三:《清代訴訟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載梁治平:《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41頁,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16] 《鄭州市中原區人民法院(2003)中民初字第121號民事判決書》,參見www.hnf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181。
[17] 蔡海鷹等:《六位出嫁女挑戰鄉規民約》,載《檢察日報》,2001-04-24。
[18] 尹田:《物權主體論綱》,載《現代法學》,2006(2)。
[19] 趙旭東:《互惠、公正與法制現代性——一個華北農村的糾紛解決》,載《北大法律評論》,第2卷第1輯,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22] 參見林立:《法學方法論與德沃金》,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
[23] 梁慧星:《誠實信用原則與漏洞補充》,載梁慧星:《民商法論叢》,第2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4。
[24] 許明月、曹明睿:《瀘州遺贈案的另一種解讀》,載王利明:《判解研究》,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
[25] 《張學英訴蔣倫芳遺贈糾紛案二審判決書》,載《判例與研究》,2002(2)。
[26][31] 林萊梵、張卓明:《法律原則的司法適用》,載《中國法學》,2006(2)。
[27] 參見梁慧星:《民法總論》,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28] 易軍:《民法上公序良俗原則的政治哲學思考——以私人自治為中心》,載《法商研究》,2005(6)。
[29] 鄭玉波:《民法總則》,臺北,三民書局,1979。
[30] 沈敏榮:《法律的不確定性——反壟斷法規則分析》,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32] 拉倫茲:《法學方法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6。
(責任編輯 李 理)
The Village Regulations and the Fundamental Rights in Civil Trial
LIU Zhi-gang
(Law School,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
The village regulations bear the constitutional mission of implementing the villager self-government,furthermore,they can be used to solve the country civil disputes.Because the village regulations and the fundamental rights are all used in civil trial,naturally,the logical connection is built between them.The common background supporting the connection is law vacancy.Under the common background,their application in civil trial has no priority,on the contrary,they present a parallel,interactive external fronts.They can not be directly applied in civil trial,their common applying duct is the principle of public order and good customs.
civil trial;village regulation;fundamental right
劉志剛:法學博士,復旦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上海200433)
十多年前,當蘇力提出“法院的基本職能究竟是落實和形成規則,還是解決糾紛”[1](P176)這樣一個頗具中國語境范式問題的時候,已經注意到了“中國當代正式法律的運作邏輯在某些方面與中國的社會背景”之間的脫節。[2](P29)植根于鄉村社會背景之下的村規民約與法律之間的沖突實際上就是該種“脫節”的一個具體側面。近年來,國內一些關注民間法的學者對此已經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在本文中,筆者無意進一步探究二者之間的這種顯性沖突,而是意圖將思維的觸須伸展至法律缺位的場景之下,對民間社會規范的重要形式——村規民約進行拓展研究,通過對其與基本權利在民事審判中的適用進行關聯性分析,將對該問題的研究引向深入。
一、村規民約與基本權利在民事審判中適用的共性場景分析——法律缺位
20世紀90年代以來,民間法引起了國內法學界的廣泛關注。該種現象出現的原因無疑是多元的,如傳統的回歸、國家法神話的破滅、法律多元認識的推動等等。[3](P5-8)在挖掘法治本土資源的聲浪中,作為民間社會規范之重要形式的村規民約也引起了學界的重視。在筆者看來,傳承已久的村規民約之所以重新引起人們的重視,固然有著上述幾個方面的原因,但其根本的原因并不在于此,與上述幾個方面的因素相比,關涉鄉村內部秩序的法律缺位或許更為根本。從歷史上來看,從鴉片戰爭以后開始,國家就開始加強了對鄉村的監控,但是,“直至解放前夕,鄉村社會的狀況總體上仍處于費孝通先生所說的‘處于蛻變過程中’的層面上,屬于國家‘法治秩序’與‘禮治秩序’、‘德治秩序’、‘人治秩序’、‘宗法秩序’等交錯并存的‘多元混合秩序’這樣一種格局,或者說國家法仍然是疏理和松弱的,而民間法還很管用”。[4](P1)如是這種現象,究其實質,緣生于國家對鄉村的監控主要體現在公法層面,而在私法層面依然是放任的,鄉村社會秩序的調整主要是依靠民間社會規范。新中國成立后,在土地改革、合作化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沖擊下,農村先前的組織和控制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其中,“公社化造就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經濟控制與行政控制網絡,使得國家權力對鄉村社會的滲入和控制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和深度”。[5](P418)先前松散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外在于國家法而存在的鄉村社會成為國家權力蔭庇下的一分子,與城市一樣,接受國家權力一體化的管轄。然而,國家權力在鄉村社會的全面滲透并沒有帶來國家法在農村的興旺和繁榮。相反,該時期國家法律的整體萎縮以及鄉村社會的地域性所引致的法律在鄉村的缺位導致了民間社會規范被逐出鄉村以后的規范缺失問題,并由此引發了頗具時代特色的鄉村秩序的政治性塑造。這種政治性的塑造不僅背離了傳統民間社會規范所凝結的社會倫理,而且在更深層次上損害了法律由以在鄉村滲透的社會基礎。因此,當這種政治性的塑造基于時代的變幻而喪失其正統性的時候,歷史傳承下來的鄉村民間社會規范又恢復了其往昔的價值,繼續流動在鄉村人們的思維脈搏之中,調整著他們的行為,維系著鄉村社會的秩序。1978年以后,在農村改革的沖刷下,費孝通先生所描述的“鄉土中國”逐步發生了變化,調控鄉村社會秩序的民間社會規范逐步萎縮,國家法的精神越來越多地滲透進了鄉村。但是,基于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源自國家的法律在鄉村的一些內部場域事實上是缺位的: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一般項目(07JA820019);復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資助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