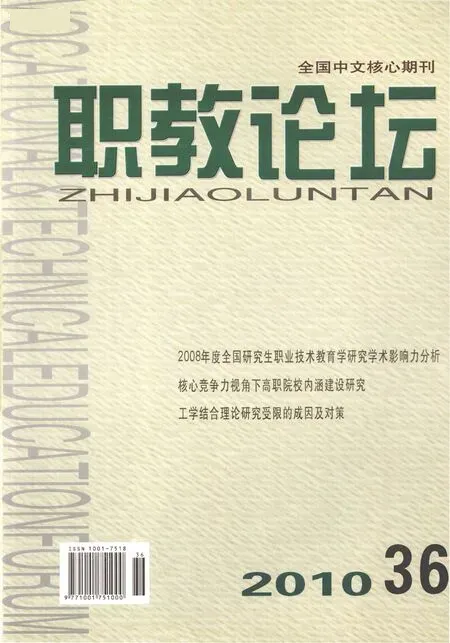再談職業教育的研究方法
□趙志群
再談職業教育的研究方法
□趙志群
我國目前職業教育研究還很薄弱,致使一些重大實踐問題始終找不到有效的解決途徑,職教研究的學術影響也很有限。如由于多學科和跨學科特點,很多人認為職業教育學應屬于一級學科,然而在新設一級學科的論證中,相關建議幾乎未經討論就被否定了。這說明學術界對職業教育非常陌生,同時也反映了職教研究學術地位不高的現實。提高職教研究水平,需要對職教研究進行深層次的方法論層面的反思。
職教研究涉及幾乎所有的社會科學領域,因此也會用到多種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我國目前的職教研究多是思辨和(不嚴謹的)質性研究,研究者一般針對時弊闡述個人觀點和感受,并提出建議。為數不多的量化研究多是簡單問卷調查,所用數據處理方法以計算各選項比例為主,采用嚴格測量技術進行的量化研究還很少,也沒有形成有影響力的量表,甚至多數人對此類概念都非常生疏。
很多從事職教研究的是工作在管理和教學一線的兼職研究者。由于他們本身處于研究對象之中,扮演著研究工作的主體和客體雙重角色,因此這些“草根研究”經常會按照研究者的“預設”去解釋現實,其結果往往只是對自己工作經驗的總結。而科研機構和高校的專職(外部)研究者,由于對研究對象缺乏深入了解,常常只能在概念層面進行討論,無法獲得很有價值的成果。目前關于“就業導向”、“中高職的區別與銜接”和“職業能力”等問題研究,就處于這樣一種境地。
這里提出了一個研究方法論的重要問題:研究者需要對研究領域(domain)熟悉到何種程度才能進行有價值的研究?研究方法與研究對象的相關度有多大?
“研究方法的內容相關性”問題在學校管理、教師發展和課程開發等中、微觀層面的研究領域顯得更為重要。作為觀察者、訪談者或設計者的研究人員,必須對所研究的領域有所了解,才能使研究對象具體化,而不再停留在一般意義上。例如,研究數控技術專業的人可能不需要掌握某型號的數控機床操作,但必須是數控技術人員。這體現了人類學研究方法的核心觀點:隱藏在背景中的認識和研究方法越多,對研究對象的了解就越清晰。事實上,不僅研究過程要求研究者必須熟悉研究領域,而且要想選擇合適的研究方法,也必須滿足這一要求。
研究人員到底需要多少領域知識才可以開展研究工作,這與研究對象的特點有關。以課程研究為例,職業知識有兩種極端情況:①職業行為模式固定,知識完全存在于可觀察的行為中。這時外部觀察者不必了解這種行為模式,也不需解析行為所隱含的信息。他觀察到了職業外部活動,就看到了與所研究職業的全部。②職業知識高度復雜,需要通過大量與情境相關的行動表現出來。從業者能將這些知識以整體化方式自覺應用到實踐中而不需要相關背景知識,能用一系列有條件的行動規范(即“如果——就”的關系)和特定程序解釋職業知識。在上述兩種極端情況下,課程研究者無需熟悉相關研究領域。
然而事實上只有少數職業屬于上述情況。在多數情況下,研究者所研究的職業知識并不是單向的“刺激與反射”的關系,掌握這些知識要“以超越自己現有績效”的方式進行。在具體工作中,實踐專家通過“能做什么”和“如何做”來表現他們特有和無法言傳的信息。由于這些知識在很大程度上是隱性知識,在幫助實現“超越自身績效”方面的貢獻很有限(Ryle1949),因此研究者掌握一定的領域知識是必要的。
不涉及具體領域知識的單純觀察和訪談等無法實現科學研究的目標(即所謂的領域特殊性原則)。職教研究者的處境就像人類學者研究外國文化時一樣,關鍵是他何時能夠了解外國文化:他只有在親身經歷該文化的社會化過程后,才能掌握它。其結果是,他對該文化不再陌生,也不再只是一個研究者。
這里就出現了一個兩難困境:即如何處理研究過程中的“接近”(proximity)與“疏遠”(distance)的關系:研究者越接近研究對象,就能越深入認識研究對象;然而隨著與研究對象距離的接近,研究者可能無法再有效促使專業人員進行解釋,也不會再像初學者一樣思考問題,而這對課程設計恰恰是一個基本要求。另一方面,距離研究對象越遠,研究者就越能像一個感興趣的外行那樣提出問題,這會促使專業人員詳細解釋他們的默會知識(G.H.Neuweg/P.Putz2008)。
研究方法的內容相關性問題可引發很多討論,它給職教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多啟發,例如其他條件相同時,中、微觀層次的研究要求研究者更加深入了解研究對象。職教研究因領域不同而研究方法不同,可能需要采用某一領域所特有的、與內容相關的研究方法,即研究有一定的情境性。如果很好地解決了方法論的問題,職教研究就可能取得高水平的成果。如萊夫(J.Lave)和溫格(E.Wenger)不足六萬字的《情境學習:合法的邊緣性參與》,按照嚴謹的人類學研究方法對助產士、裁縫等6個職業的學徒制進行案例研究,開創了學習理論研究的新紀元。讓我們共勉。
責任編輯 殷新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