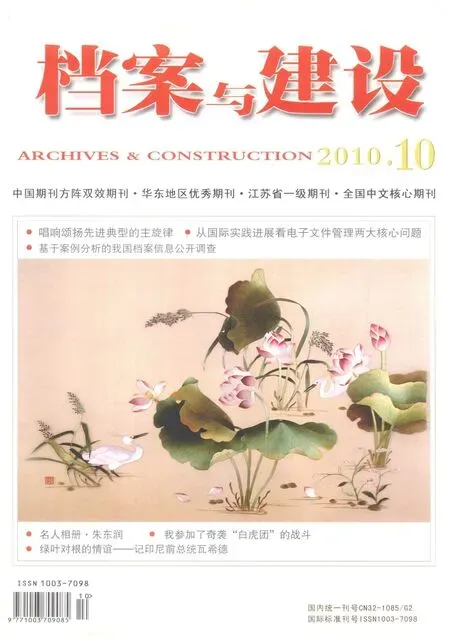采供血機構檔案規范化管理在醫療訴訟中的重要作用
□蘇錫云
為保護獻(受)血雙方的合法權益,采供血機構業務檔案所提供的原始資料已成為“舉證責任倒置”醫療訴訟的客觀基礎。這就要求采供血機構強化職責,完善采供血機構在醫療訴訟中的舉證依據,增強采供血機構的訴訟風險意識。在提高采供血液質量、確保臨床安全用血、開展輸血研究的同時,迫使醫療機構對采供血業務檔案進行規范化管理與使用,不斷提高業務檔案管理水平。
一、采供血機構業務檔案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及其對醫療訴訟的影響
1.采 供血機構業務檔案管理信息不完整,導致醫療訴訟可信度遭質疑
由于采供血機構業務工作的特殊性,每一份血液都需要有一份完整的檔案,從獻血者填寫的第一份獻血咨詢表開始,到這份血液使用到患者身上,需要經過血液采集、檢驗、成分分離、儲存、發放、運輸等多個環節。在這些工作中,每個獻血者的身份識別、檢查、每個項目的檢測、每個環節的操作,所形成的原始記錄及按照規定需要進行的相關檢測記錄,都要真實、準確、完整地納入檔案管理。這些年來,由于獻(受)血人數的不斷增多,一些采供血機構采供血過程中所形成的原始記錄的不規范和不連續,導致了業務檔案信息資料的不完整,造成業務檔案可信度遭質疑等問題不斷顯現,采供血業務檔案所出示記錄的可信度很難成為司法判決的基本證據。因此,如何規范采供血業務流程和檔案信息資料的完整性和真實性,是每個采供血機構亟待認真研究的重要問題。
2.采 供血機構業務檔案資料丟失現象嚴重,導致醫療訴訟舉證無據可依
采供血醫療侵權案件涉及的侵權行為、被告方過錯、采供血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及損害后果,均需要業務檔案提供法律依據。在采供血醫療侵權訴訟舉證中,實行的是因果關系過錯責任推定原則,采供血醫療機構需要證明的是醫療行為與患者的損害后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一些采供血業務機構由于不重視檔案資料的規范化管理和利用或片面追求降低檔案管理成本,加上采供血業務檔案形成環節多、業務檔案管理內容與一般工作信息存在一定的交叉等原因,造成檔案遺漏、破損甚至丟失現象嚴重。導致在醫療訴訟倒置舉證中不能證明或者不足以證明自己在采供血醫療活動中沒有過失醫療行為。
3.采 供血機構業務檔案保管條件得不到保證
隨著無償獻血制度的不斷完善和發展,無償獻血人數不斷增長,采供血機構業務檔案增長成為我們目前建設最快、數量最大的檔案。每天的業務檔案量多達二三十卷,有時一天同一類的檔案就多達十多卷。檔案室空間的有限與紙質檔案不斷增加的矛盾十分突出。根據訴訟法關于“醫療糾紛法律訴訟舉證倒置和訴訟官司十年有效”等有關規定,目前的采供血短期業務檔案管理除少數檔案如親子鑒定、遺傳信息檢測、采供血統計年報表等紙質檔案要求永久存檔外,其他紙質檔案通常在十年后,通過鑒定銷毀部分過期或無保存價值的無償獻(受)血檔案來提高檔案管理效率,增加庫房容量。而醫療官司實行舉證倒置后,采供血機構如何預防獻(受)血慢性病例而產生的訴訟官司,把檔案數量大與檔案保存空間有限的矛盾處置穩妥,已成為采供血機構業務檔案管理中不容忽視的問題。
二、采供血機構業務檔案規范化管理在醫療訴訟中作用重大
1.規 范化管理的采供血流程與檔案,成為獻(受)血醫療責任的原始訴訟基礎
檔案管理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基礎性工作,采供血業務檔案是統計獻血情況、制定獻血計劃的可靠依據,也是核對受血者受血日期、受血量及使用血液單位的直接資料,記載了采供血業務工作各個環節的大量信息,是實施醫療訴訟舉證最基本的依據。通過對業務檔案資料的統計分析,及時了解獻(受)血者分布等客觀情況,不僅為臨床輸血、篩查、醫學統計等血液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而且成為獻(受)血醫療責任的原始訴訟基礎。因此,必須不斷健全采供血工作的質量標準、評價和監控體系,不斷完善采供血業務檔案管理規范。
2.規 范化管理的采供血業務檔案,成為確定獻(受)血醫療責任的法定依據
隨著獻(受)血醫療糾紛越來越頻繁地發生,相關的醫療原始檔案就成為分辨獻(受)血各方責任的重要法律依據。采供血業務檔案的記錄是在采供血操作過程中產生的業務工作的真實原始記載,既反映獻血者的個人情況及其所獻血液的全部信息資料,如血液的來源和去向,又反映每袋血液經檢測證實為安全及保存、制備過程符合相關質量要求的證明情況。所以在涉及采供血活動的醫療糾紛中,采供血過程中所形成的原始檔案記錄就是證實自己嚴格依法執業,在采供血業務工作中無過錯的重要證據。如患者在獻(受)血過程中發生血液反應或在獻(受)血后發現感染了某種經血液傳播疾病,醫院要就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及不存在醫療過錯方面提出證據,也就是說,采供血醫療機構和患者要向法院提供兩個要件的證據,而確定責任的主要依據就是業務檔案資料。
3.增 強采供血業務檔案可信度,成為解決獻(受)血醫療責任的根本保證
要解決采供血機構業務檔案的可信度問題,一是要進一步落實檔案管理信息的完整性、全面性和連續性問題,防止檔案資料信息的破損、遺漏甚至丟失;二是要落實紙質與電腦檔案雙套管理機制,提高采供血業務檔案管理質量;三是要加強業務檔案保密安全管理制度和嚴格使用制度,避免人為篡改、竊取、泄密。為此,各級采供血機構要進一步增強檔案意識,加大對檔案工作的重視與投入,充分發揮采供血業務檔案信息在推進采供血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四是要加強檔案管理人員崗位職責教育,維護檔案的完整性與實體安全性,確保不因工作疏忽而致使檔案遺失、被竊、損壞等嚴重問題的發生,做到檔案管理工作有條不紊。
三、在醫療訴訟中采供血機構業務檔案應用案例分析
2009年,某患者因患溶血性貧血、干燥綜合癥入院治療過程中,分2次輸入了800毫升洗滌紅細胞,出院2個月后經檢查又患上了丙肝,患者認為是因輸血導致的,將醫院告上法庭,要求醫院給予醫療費及后續治療費的賠償。而醫院則認為血液是由甲、乙兩家采供血機構提供的,因此將甲乙兩家采供血機構列為共同被告。而患者所輸入的血液系甲血站向獻血者A某、乙血站向獻血者B某所采集。甲血站向法院提交了A某血液初、復檢化驗及檢驗報告等完整的原始檔案記錄,證明自己所提交的檔案材料是真實的,且在采集血液過程中已履行了法定義務,其提供的血液是符合標準的;乙血站所提供的B某初、復檢報告和酶標機的記錄均為復印件,且酶標機中記錄的日期與復檢報告的日期不一致,而患者最后一次輸入的血液系酶標機記錄日期的10天之后,這意味著乙血站提供的血液并沒有進行復檢,沒有履行法定義務。最終法庭判令,甲血站無需承擔法律責任,而乙血站無充分證據證明患者的丙肝是從其它途徑傳染的,且所提供的原始檔案材料的真實性、完整性和可信度受到質疑,法院認定丙肝與輸血有因果關系,賠償患者醫療費及后續治療費用。同是供血機構卻有兩種不同的判決結果,采供血流程與業務檔案管理規范化與否,不僅直接關系到經濟利益的得失,而且很大程度上也影響著采供血職能部門在社會公眾中的形象和無償獻血事業的可持續發展。
隨著人們法制觀念、自我保護意識的增強,以及醫療糾紛訴訟中舉證倒置等規定的實施,規范化管理和有效利用檔案已經成為采供血醫療機構的重要工作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