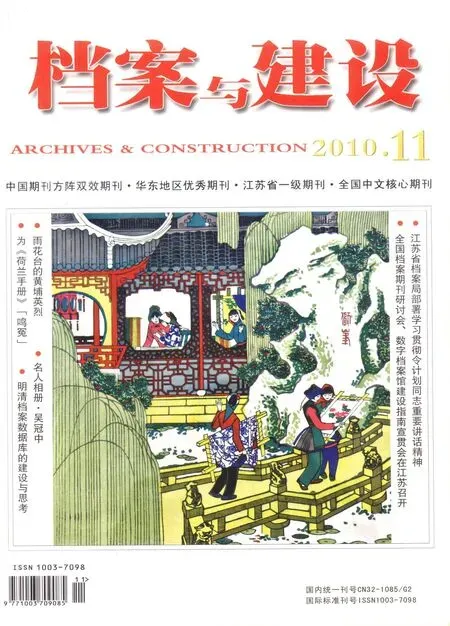檔案中介機構設立的利益分析
□李華瑩
一、檔案中介機構研究現狀
對于何為“檔案中介機構”一說,學界眾說紛紜。有學者認為“檔案中介服務機構是介于政府與企事業單位之間、專門從事檔案技術和事務服務的一種社會中介服務機構。”①有學者認為:“根據社會中介組織的定義,采取形式邏輯的方法可對檔案中介機構作如下定義:檔案中介機構是介于檔案行政管理部門與社會之間提供檔案業務服務的社會中介組織。”②也有學者認為:“檔案中介組織是社會中介組織的一種,指在政府、企事業單位和個人之間架起溝通的橋梁,是為社會提供檔案業務技術服務及檔案信息咨詢的各種組織、機構的總稱。其以提供檔案保管、利用、處置和咨詢等服務為主要目的和工作內容。”③總的來說,檔案中介機構的特征主要為:社會性、服務性和獨立性。
首先,社會性是指其介于政府與社會之間,為政府和企事業單位、個人提供檔案服務。其次,服務性即檔案中介機構為政府、企事業單位或個人提供的是一種檔案咨詢、代管等服務。最后,獨立性是指檔案中介機構作為獨立的法人組織,盈虧自負,責任自擔。其中,具有爭議的是,檔案中介機構是否具有非營利性。
有學者認為,按照不同的分類標準,檔案中介機構有不同分類:①按照產生方式可以分為體制內檔案中介機構,如檔案培訓中心、檔案咨詢服務中心等;體制外檔案中介機構,如檔案行業協會、民營檔案中介機構等。②按照職能可以劃分為組織協調型:檔案行業協會;咨詢服務型:檔案咨詢服務中心、檔案事務所;專門技術服務型:檔案整理中心、檔案寄存中心、檔案鑒定中心等;綜合服務型:檔案服務有限公司。③按照投資方可以劃分為事業單位型;民營型;外資型,如上海信安達檔案文件管理有限公司。④有學者認為,我國的檔案中介機構應分為企業性質的檔案中介機構和事業性質的檔案中介機構。⑤也有學者認為,應將其分為商業化中介機構和行政化中介機構。⑥總的來說,對我國檔案中介機構的分類是基于其設立現狀,或由檔案行政管理機構直接設立,或掛靠于檔案行政管理機構,或由社會力量所設立(此種被稱之為民營檔案中介機構)。
二、現階段我國檔案中介機構的產生基礎
有學者認為,作為社會中介服務機構的一種,檔案中介機構的產生基礎為“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或“小政府、大社會”理論,體現的是還權于社會。對此,有學者還援引我國《行政許可法》第13條的規定為據,即“通過下列方式能夠予以規范的,可以不設行政許可:①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能夠自主決定的;②市場競爭機制能夠有效調節的;③行業組織或者中介機構能夠自律管理的;④行政機關采用事后監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夠解決的。”此外,還有學者從效益最大化角度或業務外包角度論證其產生基礎。所謂“效益最大化”,是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單位保管檔案的成本逐漸上升,包括人員、庫房、箱柜及溫濕度調控設備等,故成立檔案中介機構可以降低企業或單位的成本,實現效益最大化。而“業務外包”(outsourcing)是指在市場運作中,為了節省資金,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潤,企業會選擇將自己內部一些非核心的、次要的或者輔助性的功能或者業務承包給企業外部的一些更加專業、更加優秀的服務機構。⑦
除此之外,學界關于檔案中介機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圍繞檔案中介機構的體系建設,如檔案管理機構的地位、責任、權利、服務對象、服務內容、收費標準、賠償制度及其與檔案行政管理部門之間的關系。而針對我國檔案中介機構存在問題進行分析,則認為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問題:①與檔案行政管理機構職責劃分不清;②檔案中介機構方面的法律法規建設極不完善,全國目前只有浙江省檔案局2004年頒發的《浙江省檔案中介服務管理辦法》唯一一部專門的法規性文件;③服務層次較低,檔案中介機構提供的服務主要集中在檔案代管、咨詢、教育培訓和檔案用具銷售;④人員隊伍建設落后,檔案中介機構吸納的技術人員多為臨時性,或業已退休的檔案人員,故而工作難以創新。
筆者認為,對檔案中介機構進行制度設計固然重要,但我國檔案中介機構的存在現狀所體現出的深層次現象,如我國檔案中介機構與檔案行政管理機構的關系為何如此糾纏不清,以至于成為檔案中介機構進一步發展的桎梏等,都須以研究。而這一切都源于檔案及其管理之于社會的不可或缺性。正是此種“不可或缺性”成就了不同的利益訴求,也同樣成就了檔案中介機構的雙重屬性,即商業屬性和社會服務屬性。
三、關于設立檔案中介機構的利益分析
利益是各個人所提出來的要求、愿望或需要,可以被分為三類:個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會利益。個人利益是直接包含在個人生活中并以這種生活的名義而提出的各種要求、需要或愿望;其他一些是包含在一個政治組織社會生活中并基于這一組織的地位而提出的各種要求、需要或愿望;還有一些其他的利益或某些其他方面的同類利益,它們是包含在文明社會的社會生活中并基于這種生活的地位而提出各種要求、需要或愿望。⑧
對于個人或國家而言,檔案的不可或缺性所體現的就是這樣一種利益訴求。自1949年以來,我國所建立的檔案管理體系主要是遵循國家意志,實現公共利益。在這一過程中,檔案的不可或缺性一律被上升為公共利益,主要由檔案行政管理機構進行收集、管理和利用等。然而檔案畢竟是作為一種“公共物品”而存在,隨著國家和社會關系的再定位,在這一公共物品的分配和利用過程中,個人或社會對其的利益訴求及相互之間的重疊或沖突也隨之出現。因而,在檔案中介機構的建立過程中就先后出現過這樣一些聲音,如不應建立檔案中介機構,仍應由檔案行政管理機構對檔案進行管理;檔案中介機構的收費應當是象征性的,其定位應更偏向于社會服務性;應將檔案中介機構區分為行政性中介機構和商業性中介機構等等。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及國家機構職能的轉變,檔案中介機構的出現必然成為趨勢。然而如何建立檔案中介機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仍將是學界爭論的焦點,而檔案中介機構與檔案行政管理機構二者“涇渭分明”則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畢竟在我國檔案的公共服務性和秘密性更多地被強調,而現階段的立法及檔案中介機構的信用體系建設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實現的。
對利益的任意調整,是不能長久維持的。⑨故而,在檔案中介機構建立和發展的過程中,簡單地用檔案行政管理機構取代中介機構是不科學的,而完全由檔案中介機構取代管理機構對檔案的微觀管理職能,在現階段看來,短期內是不可實現的。但檔案中介機構可以圍繞著非國有的這部分檔案進行研究,并努力開拓代管檔案、檔案咨詢、教育培訓及檔案用具銷售之外的服務領域,提高自己的業務能力,才是其存在之本。
在我國現階段,檔案中介機構無論是由檔案行政管理機構直接設立,或掛靠于檔案行政管理機構,或由社會力量所設立(此種被稱為民營檔案中介機構),其所體現的不過是不同利益之間的博弈。而商業性中介機構與行政性中介機構共存體現的更是利益之間的一種均勢。因而,檔案行政管理機構應在尊重各方利益的基礎上,科學地做出抉擇,而不應簡單地應用行政手段消滅商業性中介結構,或形成一種檔案領域的“行政壟斷”。畢竟,當人們的主張和需求被拒絕承認而且還是在非理智的基礎上被否認時,他們會感到雙重不滿。⑩
檔案中介機構的出現,是中國市民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民主意味著公眾參與,公眾參與的領域越廣泛,公眾參與度越高,一國之民主才可能稱得上較高程度的民主。公眾參與并不意味著“官退民進”,相反,其更多的時候體現為公眾對公共事務的知曉和參與,它代表的是政府與公眾的良好互動,在二者互動的過程中,提高公眾對政府及其行為的認可度,既可以很好地確立政府機關的威信,也可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筆者認為,檔案中介機構的出現,正是這樣一種理念在檔案領域的踐行,而檔案中介機構的健康發展和運行也有賴于檔案行政管理機構對此理念的尊重。
誠如前述所言,檔案中介機構的出現,是個人利益或社會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重疊或沖突,排解此種重疊和沖突并不一定要消滅其中的某一項利益。在此種情形下,要達到“利益最大化”,即在最少阻礙和浪費的條件下使檔案這一公共物品滿足人們的需要和要求,顯然,盲目消滅其中的某一項利益并非明智之舉,而且在非理智的基礎上否認其中一項利益,不僅會面臨阻礙,也是對市場規律的一種違背。某種要求或愿望以規模形式被提出后,首先要做的是確認某項利益是否必須被承認。在承認該項利益之后,就要努力保障在確定限度被承認的利益。既然檔案中介機構作為一種檔案利用形式為市場所需要,那么檔案行政管理機構所要做的就是對這種需要進行權衡,然后確認在什么限度內對該種利益進行保障。對此,上海檔案咨詢服務中心的設立就是一個很好的典范。
既然現階段檔案行政管理機構與檔案中介機構二者共存,那么檔案行政管理機構的工作重心理應放在理順二者的關系及規范檔案中介市場秩序上。檔案行政管理機構仍履行管理職責,但該管理不應狹隘地定位于對檔案的管理。固然對檔案的管理是其基本的業務能力和要求,但對檔案管理領域新生事物的應對和管理理應是“管理”的內在涵義。對于目前檔案行政管理機構設立的聯合檔案室以及檔案寄存中心等,不妨將其看作檔案管理和利用的另一種形式。但此種利用方式,畢竟只能極為有限地緩解市場需要。檔案行政管理機構不妨立足于對整個市場秩序的建設和規制,把好檔案市場的脈象,未雨綢繆,應對來自國外的競爭。
從未來看,社會性的檔案中介機構是檔案管理的中堅力量。但現階段,二者只能并存,檔案行政管理機構應當有意識地去保護社會性的檔案中介機構,不需要行政力量去消滅,造成行業壟斷。
總體來說,目前檔案市場出現的檔案中介機構及檔案行政管理機構采取的新舉措,都是由市場需求所推動的,檔案中介機構的出現更是帶有很強的“脅從性”或被動性。這也就導致了檔案利用率不高,社會檔案意識不強的局面。正如有的學者所提出的,“檔案是一種寶貴的社會資源,檔案信息以其直接性、原始性而優于其他信息。然而由于社會檔案意識不強,利用的方式又繁瑣、單調,很難激起利用的欲望,致使檔案館反不及圖書館、博物館等社會文化事業機構的利用率高”。?被動地由市場推動,充其量是“由下而上”的形式之一,但一門學科的真正發展應是“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相互作用。我國的檔案管理機構屬于“局館合一”的體制,由上而下的效力能更好地發揮,故而,檔案行政管理機構更應發揮“由上而下”的推動作用,做好統籌規劃,提高檔案的社會認知度和利用度。檔案絕不應是可有可無的“擺設”,它亦可以創造社會效益。
當一種制度的變革為市場所要求時,我們所要做的不是排斥或打壓。對于檔案中介機構,它絕不是“洪水猛獸”,相反,檔案中介機構的發展,可以為檔案學科提供更多的活力。不論是商業性的檔案中介機構,還是行政性檔案中介機構,都是市場的發展而推動形成的,都應順應市場需要及時調整自己的市場走向。作為檔案中介機構的管理者,檔案行政管理部門理應創造一個利益平衡點,使兩種檔案中介機構和諧共存。作為檔案工作者,我們理應用科學的方法論來看待檔案中介機構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種種問題,不盲目地批判或者繼承。檔案中介機構這個檔案服務主體定會越走越好。
注釋:
①鄭金月:《檔案中介服務機構存在的問題及其對策》,《中國檔案》2000年第3期。
②宗培嶺:《檔案中介機構的社會定位》,《浙江檔案》2005年第7期。
③韓玲玲、沈麗、謝靜:《我國檔案中介服務業及其組織優化模式》,《商業經濟》2005年第9期。
④苗華清:《淺析檔案中介機構的發展策略》,《浙江檔案》2006年第12期。
⑤徐云鵬、潘純瑤:《淺談我國檔案中介機構的改革》,《蘭臺世界》2008年第12期。
⑥齊虹:《關于檔案信息咨詢產業化的思考——兼議檔案中介機構產必然性與發展方向》,《北京檔案》2000年第11期。
⑦苗華清:《檔案中介機構的理論發展基礎探析》,《蘭臺世界》2007年第1期。
⑧⑨⑩[美]羅斯科·龐德著,沈宗靈譯:《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41、47、47頁。
?王歡喜:《試論檔案中介機構介入待銷毀檔案的處理》,《湖北檔案》200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