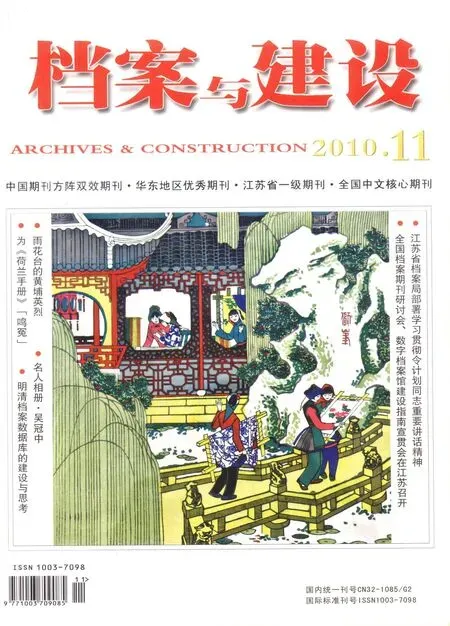略述遼宋夏金元時期中國少數民族文字石刻檔案
□唐雯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各少數民族都為中國歷史的發展作出過不少貢獻。在中國古代少數民族有勒石記事的歷史傳統,在保留的石刻檔案中,刻有少數民族文字的石刻檔案不可忽視。遼宋夏金元時期,契丹、黨項、女真、蒙古這些少數民族先后建立起很大的區域性政權甚至于全國性政權,并用本民族的文字鐫刻于石上,石刻檔案大量形成。本文試對現存的遼宋夏金元時期中國少數民族文字石刻檔案的歷史與內容略作介紹。
早在五代十國初期的公元916年,契丹族首領耶律阿保機稱帝,建立契丹國,年號神冊。神冊五年(公元920年),突呂不等參照漢字筆畫結構創制契丹大字。不久,耶律迭刺又創制契丹小字。前者表意,后者表音,兩種文字與漢字同時使用。然而金在滅遼的60多年后,明令廢止契丹文,導致契丹文失傳,至今未被破譯。后來陸續有考古發現的契丹文石刻檔案等文獻資料,為研究契丹文提供了研究條件和重要依據。
目前已知的契丹文石刻檔案主要是用契丹大字或契丹小字鐫刻的紀功碑、哀冊文、建廟記、墓志、題記等。其中契丹大字石刻八種,重要的有:《遼太祖紀功碑》殘石,發現于內蒙古巴林左旗遼太祖陵前;《耶律延寧墓志》,遼統和六年(988年)刻,1964年出土于遼寧朝陽縣,志文上半部刻契丹大字,下半部刻漢字,但二者并不對譯;《北大王墓志》,重熙十年(1041年)刻,1975年出土于內蒙古阿魯科爾沁旗,志文為契丹大字,志蓋為漢字;《蘭陵郡夫人建靜安寺碑》,咸雍八年(1072年)刻,現立于內蒙古寧城縣,正面刻漢字,背面刻契丹大字,字跡已漫漶不可識;《蕭孝忠墓志銘》,大安六年(1090年)刻,1950年出土于遼寧錦西縣,志文刻契丹大字,志蓋刻漢字;《故太師銘石記》,清寧二年(1056年)刻,志蓋刻篆書漢字,志文刻契丹大字40行、1800余字,是迄今所知契丹大字石刻檔案中字數最多的石刻檔案。
契丹小字石刻檔案目前已知有15種。重要的有:《興宗皇帝哀冊文》和《仁懿皇后哀冊文》,分別刻于清寧元年(1055年)和大康二年(1076年),1922年出土于內蒙古巴林右旗遼慶陵;《道宗皇帝哀冊文》和《宣懿皇后哀冊文》,均刻于乾統元年(1101年),1930年出土于慶陵之道宗陵;《許王墓志》,乾統五年(1105年)刻,1975年出土于遼寧阜新縣,志蓋上刻漢字及對譯的契丹小字一行;《耶律仁先墓志》,咸雍八年(1072年)刻,1983年出土文物于遼寧北票縣,契丹小字志文刻于漢字志蓋背面,有70行、5100余字,另有漢字志文,但不對譯;《大金皇帝都統經略郎君行記》,金天會二年(1124年)刻于陜西乾陵《無字碑》上,有對譯漢字,且保存完好,是解讀契丹小字的重要依據。
公元1038年,黨項族首領李元昊稱帝,建立西夏,命野利仁榮創制西夏文。西夏文結構多仿漢字,形體方正,也有楷、草、隸、篆諸體,與漢字并用。西夏滅亡后,西夏文仍為黨項族所使用,直至明末,以后便失傳。與契丹文不同的是,保存至今的西夏文文獻相當多,西夏文石刻檔案只是其中一部分。
西夏文石刻檔案中最著名的是《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刻于西夏天佑民安五年(1094年),現存于甘肅武威市博物館。碑陽刻西夏文,額題為篆書,碑文為楷書28行約1800字,碑陰刻漢字。兩種文字雖然不互譯,但所述內容大體相同,不僅反映了西夏的經濟、政治史實,也是研究早期西夏文的重要依據。近年來,在清理銀川市賀蘭山東麓西夏王陵時,發現不少西夏文、漢字殘碑,其中有二號陵出土的《西夏仁宗壽陵碑》殘石,從殘存的西夏文碑文看,記載的是西夏仁宗及其祖先之事。
公元1115年,女真族首領完顏阿骨打稱帝,建立金國,不久便命完顏希尹、葉魯參照契丹文和漢字,創制女真大字。金天眷元年(1138年),金熙宗又創制女真小字。與契丹文一樣,大字表意,小字表音。女真文在金國跟漢字一起通行,直至金亡,而在東北地區女真族故地則一直使用至明代。女真文文獻傳世很少,現存的十余種女真文石刻檔案是研究女真文最基本的資料。
《女真進士題名碑》是最早被發現和研究的女真文石刻檔案,刻于正大元年(1224年),現存于河南開封市文廟。它一面刻漢字,一面刻女真文,明代時漢字被磨去。《大金得勝陀頌碑》刻于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現存于吉林扶余縣,是紀念金太祖寧江州破遼勝利的紀功碑。此碑一面刻漢字,一面刻女真文,并可對譯,是現存的女真文石刻檔案中存字最多、研究價值最重要的石刻檔案。其它現存石刻還有吉林舒蘭縣的《昭通大將軍同知雄州節度使墓碑》、山東蓬萊的《奧屯良弼詩碑》、《海龍女真國書摩崖》等。在今朝鮮境內還有《慶源郡女真國書碑》、《北青女真國書摩崖》等石碑。
公元1206年,蒙古族首領鐵木真統一蒙古各部,號“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國家。塔塔統阿借用畏兀爾文(回鶻文)的字母拼寫蒙古語,創制蒙古畏兀爾字。忽必烈正式建國號大元之前,八思巴根據藏文字母創制八思巴蒙古字,定為蒙古國字。因而,蒙古文包括這兩種文字。
現存最早的蒙古文石刻檔案是《移相哥碑》,亦稱《成吉思汗石》,刻于1225年成吉思汗西征勝利后不久,今收藏于俄羅斯圣彼得堡博物館。《云南王藏經碑》刻于元至元六年(1269年),現存于云南昆明筇竹寺,與《移相哥碑》類似,都是單用蒙古畏兀爾字刻成。此外還有內蒙古翁牛特旗的《張氏先塋碑》(刻于 1335年)、《竹溫臺碑》(刻于1338年)、甘肅武威市的《西寧王忻都公神道碑》(刻于1362年),以及今蒙古境內的《釋迦院碑》(刻于 1257年)、《興元閣碑》(刻于1342年),都是用蒙古畏兀爾字與漢字刻成,石碑上的蒙文據漢字譯出或縮寫。
現存八思巴蒙古字石刻檔案數量不少,多是寺觀所刻皇帝圣旨、皇后懿旨、諸王令旨之類。石刻內容是保護佛寺道觀產業不受侵犯或減免僧道賦稅,一般都有漢字譯文。這些是研究元代宗教和寺觀經濟不可多得的史料。可貴的是,這些漢字譯文都是用當時的漢語白話直譯出來的,所以又稱“元代白話碑”,對今人研究元代專名譯語有著特殊的價值。
在北京居庸關云臺門洞的東西兩壁上,有元代至正五年(1345年)用梵文、藏文、蒙古文、回鶻文、西夏文、漢文六種文字所刻的佛經和題記。此處石刻檔案中的八思巴蒙古字部分,有音譯梵文陀羅尼經的譯文,有關于元代佛教傳播情形的記述,這些都是珍貴的蒙古文佛教史料。還有據漢字音譯的加封孔子、孟子的制書等,為研究古代漢語語音提供了可靠史料依據。古代雖有漢語音韻之學,但很難確定漢語語匯的實際音值,而八思巴字是拼音文字,用它音譯漢語文獻,使今天的學者可以借此重新構擬元代漢語的語音。云臺門洞東西兩壁石刻檔案中的西夏文部分,有音譯佛經譯文,則對研究西夏語語音非常有價值。
①路遠、裴建平:《石版文章——歷代碑刻瑣談》,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