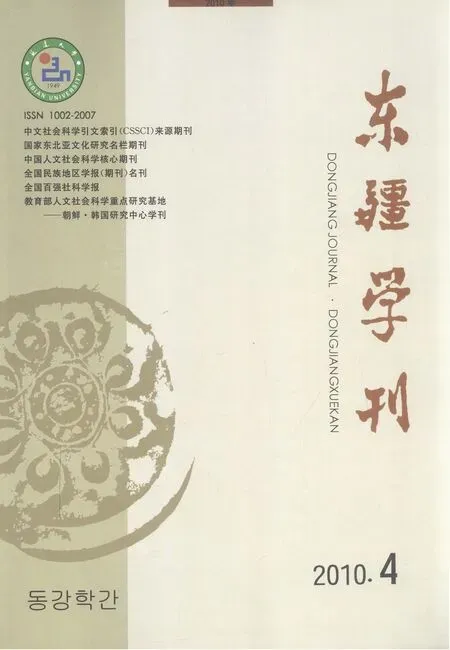中國古典詞味論的承傳
胡建次
(南昌大學中文系,江西南昌330031)
中國古典詞味論的承傳
胡建次
(南昌大學中文系,江西南昌330031)
我國古典詞味論的承傳,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味”作為詞作審美之本標樹之論的承傳,二是詞味表現要求之論的承傳,三是詞味創造與生成之論的承傳。其中,在第三個方面,其內容主要體現在三條線索中:一是字語運用與詞味關系之論的承傳,二是詞作用筆與詞味關系之論的承傳,三是藝術表現與詞味關系之論的承傳。上述幾條線索,從主體上展開了古典詞味之論,分專題勾畫出了古典詞味論的論說軌跡。
古典詞學;詞味論;維面展開;線索承傳
“味”是我國古典詞學審美論的重要范疇,它與“韻”、“趣”、“格”、“境”等范疇一起,被用來概括詞的審美本質特征,標示詞的不同審美質性。在我國古代文論史上,“味”是一個出現和成熟得相對較早的審美范疇。它確立于魏晉南北朝時期,發展于唐宋,承傳于元代,完善于明清,已成為古代文學理論批評最重要的范疇之一。
一、“味”作為詞作審美之本標樹之論的承傳
我國古典詞學將“味”作為詞作審美之本的標樹,主要出現于清代。其主要體現在劉體仁、孫麟趾、蔣敦復、劉熙載、沈祥龍、王國維等人的批評言論中。他們主要從詞作藝術魅力融含的角度,對“味”在詞作審美中的本體地位予以標舉與闡明。
清代前中期,劉體仁的《七頌堂詞繹》云:“晏叔原熨帖悅人,如‘為少年濕了,鮫綃帕上,都是相思淚’,便一直說去,了無風味,此詞家最忌。”[1](915)劉體仁通過評說晏殊詞作將“相思”之題和盤倒出,過于直白淺露,對詞作較早提出了含蓄有味的要求。他把缺乏滋味論斷為詞家創作的大忌,體現出對詞作含蓄之美的推崇。孫麟趾的《詞徑》云:“學問到至高之境,無可言說。詞之高妙在氣味,不在字句也。能審其氣味者,其唯儲麗江乎。”[2](2554)孫麟趾明確將“味”標樹為詞作審美的本質所在。他界定,“氣味”是使詞作顯示出“高妙”的東西,它具有非實體性的特征,要通過字句加以體現,但又并不完全體現在字句之上。蔣敦復的《芬陀利室詞話》云:“詩至詠古,酒杯塊壘,慷慨激昂,詞亦有之。第如迦陵之叫囂,反覺無味。”[1](1568)蔣敦復具體論說到懷古詞的創作,他對陳維崧懷古之詞過于呈現出議論化的色彩不以為然。其論對“味”作為詞作審美的本質所在實際上也予以標樹。其又云:“若入李氏、晏氏父子手中,則不期厚而自厚。此種當于神味別之。”[1](1590)蔣敦復對李、李煜和晏殊、晏幾道的詞作都甚為推崇,論斷他們的詞作含蘊豐厚的思想內涵與不盡的藝術意味,人們應該注重從詞作的“神味”上對它們加以辨析。蔣敦復進一步將“味”視為詞作審美的質性范疇。
在晚清,劉熙載在其《藝概·詞概》中云:“詞之為物,色香味宜無所不具。”[2](3706)劉熙載將“味”與詞作藝術表現中的“色”、“香”一起,論斷為詞作最重要的審美質素,見出了詞作審美展開的多維性。其又云:“桓大司馬之聲雌,以故不如劉越石。豈惟聲有雌雄哉,意趣氣味皆有之。品詞者辨此,亦可因詞以得其人矣。”[2](3710)劉熙載通過評說桓溫與劉琨詩作的高下之別,又觸及詞味的論題。他主張品詞應從“意趣”、“氣味”入手,品其詞,知其人,體現出他切實地將是否有味視為詞作審美的首要準則,見出了“味”在詞作審美中的本體地位。沈祥龍的《論詞隨筆》云:“詞之蘊藉,宜學少游、美成,然不可入于淫靡;綿婉宜學耆卿、易安,然不可失于纖巧;雄爽宜學東坡、稼軒,然不可近于粗厲;流暢宜學白石、玉田,然不可流于淺易。此當就氣韻趣味上辨之。”[1](1849)沈祥龍在辨析不同詞人的詞作風格特征時,將“味”與“氣”、“韻”、“趣”一起,標樹為詞作審美最重要的東西。他強調說,要從審美質性的深層次上界分詞人、詞作,趨正而離變。沈祥龍之論,在清人將“味”作為詞作審美之本的標樹中論說得最為明確,顯示出了重要意義。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則云:“北宋名家以方回為最次。其詞如歷下、新城之詩,非不華瞻,惜少真味。”[3](224)王國維通過評說賀鑄之詞,對“味”在詞作審美中的本體地位也予以標舉。他批評賀鑄之詞與朱彝尊、王士的詩一樣,在藝術表現形式上盡管華美富贍,但在藝術魅力的呈現上仍然有所不足。
對“味”作為詞作審美之本的標樹之論,在現代詞學中也有承傳。如:趙尊岳的《珍重閣詞話》云:“作詞首貴神味,次始言理脈字句。神味佳則胡帝胡天,亦成名作,而神來之筆,又往往在有意無意之間,其中消息,最難詮釋。”[4](769)趙尊岳承傳前人之論,繼續將“味”標樹為詞作審美的最重要所在。他說,“神味”是詞作藝術表現中最核心的東西,與詞的理脈、字句不處于同一層面,它在最本質的意義上決定著詞作的優劣高下。
二、詞味表現要求之論的承傳
我國古典詞學對詞味表現要求之論,也主要出現于清代。其主要體現在孫麟趾、周濟、劉熙載、程文海、陳廷焯、沈祥龍等人的論說中。這一方面的論說視域較為零散,并未形成什么像樣的專題承傳線索。我們將它們放在一起略作勾勒與闡說。
在清代前中期,孫麟趾的《詞徑》云:“陳言滿紙,人云亦云,有何趣味。若目中未曾見者,忽焉睹之,則不覺拍案起舞矣,故貴新。”[2](2555)孫麟趾對詞味表現提出了應追求有新鮮之味的要求,他強調說,要在藝術陌生化的過程中使詞作審美具有觸人心神的特征,這與袁枚在《隨園詩話》中對詩歌新鮮趣味的提倡是一致的。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云:“雅俗有辨,生死有辨,真偽有辨,真偽尤難辨。稼軒豪邁是真,竹山便偽;碧山恬退是真,姜、張皆偽。味在酸咸之外,未易為淺嘗人道也。”[1](1493)周濟在評說宋代幾位代表性的詞人、詞作藝術表現真偽的同時,還承傳了司空圖論詩之意,提出了“味在酸咸之外”的論斷,其論寓含著詞味,具有含蓄朦朧與不斷發散的特征。在晚清,劉熙載的《藝概·詞概》云:“詞淡語要有味,壯語要有韻,秀語要有骨。”[2](3707)劉熙載指出詞作的語言運用可以趨淡,但必須淡而有味。他將“味”與“韻”、“骨”一起,視為詞作藝術創造與審美的最質性的東西。程文海的《題晴川樂府》云:“蘇詞如詩,秦詩如詞,此益意習所遣,自不覺耳。要之情吾情,味吾味,雖不必同人,亦不必強人之同,然一往無留如戴晉人之訣,則亦安在其為寫中腸也哉。”[5](248)程文海在詞作的藝術表現上提倡要有個性。他認為,蘇軾之詞如詩,秦觀之詩如詞,這都是緣于創作者所稟的氣質與個性。他說,詞作應抒寫創作主體自身獨特的情致,表現自身獨特的意味。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云:“純寫閨,不獨詞格之卑,抑亦靡薄無味,可厭之甚也。然其中卻有毫厘之辨。作情語勿作綺語,綺語設為淫思,壞人心術。情語則熱血所鐘,纏綿惻悱,而即近知遠,即微知著,其人一生大節,可于此得其端倪。”[1](1613)謝章鋌從詞作藝術表現的內容上立論詞味。他反對一味抒寫閨中生活之細碎,認為這容易導致詞格卑陋,綺靡無味。他將詞作藝術表現的“情語”與“綺語”加以區分,提倡以情感化的語言加以抒寫,表現人生的真情實感。謝章鋌將詞味的生成落足到了鮮活的現實生活之中,其論體現出對承承相因以詞敘寫個人之私情題材的厭惡以及對不斷開拓詞作新題材的呼喚與倡導。陳廷焯的《白雨齋詞話序》云:“詩有韻,文無韻,詞可按節尋聲,詩不能盡被弦管。飛卿、端己,首發其端,周、秦、姜、史、張、王,曲竟其緒;而要皆發源于風雅,推本于騷辯。故其情長,其味永,其為言也哀以思,其感人也深以婉。”[6](1)陳廷焯從文體質性與藝術表現上分辨詩、文、詞三種文學形式。他認為,詞與詩不同,詞要依照音樂節拍來選詞用語,它追求的審美效果是情感悠長、韻味深永,這與詩作藝術表現形成了細微的區別。沈祥龍的《論詞隨筆》云:“詞不能堆垛書卷以夸典博,然須有書卷之氣味。胸無書卷,襟懷必不高妙,意趣必不古雅,其詞非俗即腐,非粗即纖。故山谷稱東坡《卜算子》詞,非胸中有萬卷書,孰能至此。”[1](1850)沈祥龍對詞的創作提出了有書卷氣味的要求。他反對作詞時一味堆砌書本知識,一味寓事用典,逞才使氣,而提倡適度地運用所學知識與所識事理,化入于詞中,使詞作顯示出濃郁的書卷氣味,如此,才能使詞作更好地入乎雅致之中。
對詞味的表現要求之論,在現代詞學中也有承傳。如:趙尊岳的《珍重閣詞話》云:“作詞之神味云者,蓋謂通體所融注,所以率此理脈字句,而又超于理脈字句之外。若以王阮亭所謂神韻釋之,但主風韻,則或失之俳淺,非吾所謂神味矣。”[4](769)趙尊岳之論,道出了“味”是渾融地體現于整個詞作之中的,它具有非實體性、被含寓性的特征。它存在于具體字句之中,然而又超拔于字句之上,是詞作藝術表現中深層次魅力之所在。
三、詞味創造與生成之論的承傳
我國古典詞味創造與生成之論,在以下幾方面形成了相互承傳的線索:一是字語運用與詞味關系之論,二是詞作用筆與詞味關系之論,三是藝術表現與詞味關系之論。對此,我們將分別勾勒與論說。
(一)字語運用與詞味關系之論的承傳
這一線索主要體現在沈義父、包世臣、陳椒峰、蔣敦復、陳廷焯的論說中。南宋末年的沈義父在其《樂府指迷》中云:“蓋音律欲其協,不協則成長短之詩。下字欲其雅,不雅則近乎纏令之體。用字不可太露,露則直突而無深長之味。發意不可太高,高則狂怪而失柔婉之意。思此,則知所以為難。”[1](199)沈義父較早地從字語運用的角度論說到了詞作之味的創造。他反對詞作用字造語過于直白淺露,認為這與詞味創造的要求背道而馳。在清代,包世臣的《月底修簫譜序》云:“意內而言外,詞之為教也;然意內不可強致,言外非學不成。是詞說者言外而已,言成則有聲,聲成則有色,色成而味出焉。三者具,則足以盡言外之才矣。”[5](671)包世臣從詞作藝術表現的角度論說到詞味的創造。他以“意內言外”為詞作藝術表現的本質模式,以此為基點,主張詞的創作在根本上要對字語運用加以認真琢磨,反復酌斟,如此,由字語運用而決定其音律表現,由音律表現而決定其藝術技巧,最終創造出富于審美魅力的詞作。陳椒峰《蒼梧詞序》云:“楊誠齋論詞六要:一曰按譜,一曰出新意是也。茍不按譜,歌韻不協,歌韻不協,則凌犯他宮,非復非調,不出新意,則必蹈襲前人。即或煉字換句,而趣旨雷同,其神味亦索然易盡。”[5](794)陳椒峰在楊萬里論詞提出的“六要”的基礎上,把“神味”作為詞作審美最本質的東西。他提出,詞作應在音律協和的基礎上出新意,如此,才可避免所表旨趣相同卻導致神味全無之弊。蔣敦復的《芬陀利室詞話》云:“余亦謂詞之一道,易流于纖麗空滑,欲反其弊,往往變為質木,或過作謹嚴,味同嚼蠟矣。故煉意煉辭,斷不可少。煉意,所謂添幾層意思也;煉辭,所謂多幾分渲染也。”[1](1562)蔣敦復看出了詞作的藝術表現往往有流于偏執化的特征。他明確地提出要錘煉詞意與字語的要求,認為:惟有通過錘煉詞意,才能使詞作呈現出“復調”結構與深度表現模式;也惟有通過錘煉字語,才能使詞作面貌搖曳多姿,更富于藝術意味。蔣敦復之論,體現出對無味之詞作的堅決摒棄。陳廷焯的《白雨齋詞話》云:“元以后詞,則清者失真味,濃者似火酒矣。言近旨遠,其味乃厚;節短韻長,其情乃深;遣詞雅而用意渾,其品乃高,其氣乃靜。”[6](217)陳廷焯通過評說元朝以后的詞作的審美特征,也闡說到了字語運用與詞味表現的關系的論題。他認為,詞人用字造語要淺近直切,而意旨表現則要深遠有致,如此,才能使詞味醇厚無垠。陳廷焯對詞味創造的要求與傳統詞論是一致的。
對字語運用與詞味關系之論,在現代詞學中也有承傳。如:顧憲融的《論詞之作法》云:“詞中要有艷語,語不艷則色不鮮;又要有雋語,語不雋則味不永;又要有豪語,語不豪則境地不高;又要有苦語,語不苦則情不摯;又要有癡語,語不癡則趣不深。”[4](689)顧憲融從語言運用的角度論說詞味的創造。他主張詞作用語要豐富多樣,“艷語”、“雋語”、“豪語”、“苦語”、“癡語”各有其藝術魅力,其中,要想使詞作呈現出悠長的滋味,最好多用清新雋永的語詞。顧憲融從深層次對詞作用語的要求與詞味的生成加以了貫通。
(二)詞作用筆與詞味關系之論的承傳
(三)藝術表現與詞味關系之論的承傳
這一線索主要出現于晚清時期,并主要體現在陳廷焯、沈祥龍、況周頤、王國維等人的論說中。陳廷焯的《白雨齋詞話》云:“詞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蘇、秦之終,后開姜、史之始,自有詞人以來,不得不推為巨擘,后之為詞者,亦難出其范圍。然其妙處,亦不外沉郁頓挫。頓挫則有姿態,沉郁則極深厚。既有姿態,又極深厚,詞中三昧亦盡于此矣。”[6](16)陳廷焯對周邦彥詞作評價甚高,認為其承前啟后,富于獨創,其詞作獲得成功的“妙處”,在于詞作在思想內涵與情感表現上極為深厚,在藝術形式與技巧表現上聲情揚抑,如此,才充分地表現出詞家對社會人生體悟的千般滋味。陳廷焯從“沉郁頓挫”立論詞作之味,注重詞人詞作情感表現的真摯深婉與藝術形式的相符相切,這為王國維拈出“意境”論詞奠定了基礎。沈祥龍的《論詞隨筆》云:“含蓄無窮,詞之要訣。含蓄者,意不淺露,語不窮盡,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其妙不外寄言而已。”[1](1848)沈祥龍在將含蓄美論斷為詞作藝術表現之本的同時,對“含蓄”的美學內涵及其藝術呈現模式予以闡說。他認為,含蓄之美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詞作表意要避卻淺白直露,二是詞作用語要留有回旋余地,其旨歸是創塑出令人回味不盡的藝術空間,而這都要通過“寄意于言”的藝術表現模式加以傳達。沈祥龍明確將“寄言”論斷為詞作有“余味”的必然途徑。他還說:“詞雖濃麗而乏趣味者,以其但知作情景兩分語,不知景中有情,情中有景語耳。‘雨打梨花深閉門’、‘落紅萬點愁如海’,皆情景雙繪,故稱好句,而趣味無窮。”[1](1848)沈祥龍將“趣味”作為詞作審美的首要準則。他反對詞作一味追求濃麗,反對將“情”與“景”這兩個重要審美生發質素加以機械分割,認為兩者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具體說就是,“景”是情感貫注的“景”,“情”是通過外物加以體現的“情”,詞作只有做到情景交融,才能產生出趣味無窮的審美效果。況周頤的《香海棠館詞話》云:“初學作詞,只能道第一義,后漸深入。意不晦,語不琢,始稱合作。至不求深而自深,信手拈來,令人神味俱厚。”[4](117)況周頤從學習作詞上論說到詞作用語造意與詞味融含的關系。他指出詞的創作是有層次之分的,當主體到達一定的創作層次后,其詞意表現并不追求繁富,其字語運用也不追求修飾,但詞作卻在“不求深”中“而自深”,融含醇厚無垠之神味。況周頤將詞味的深淺厚薄與主體創作層次的正比關系揭示了出來。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則云:“古今詞人格調之高,無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覺無言外之味,弦外之響,終不能與于第一流之作者也。”[3](212)王國維之論,明確從意境的創造上來立論詞味,把意境的有無視為是否有言外之味的唯一生發源。他在前人以意境立論詩味的基礎上,進一步論斷意境乃詩詞等表現性藝術之本,它與“格調”等審美范疇相比,更具有原發性,故強調“于意境上用力”而得“言外之味”。此論在我國古代對詞味創造與生成的論說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其《人間詞話附錄》又云:“至乾嘉以降,審乎體格韻律之間者愈微,而意味之溢于字句之表者愈淺。豈非拘泥文字,而不求諸意境之失歟?”[3](257)王國維批評乾嘉以來不少人作詞局限于在體制、格調與音律運用等方面做文章,舍本而逐末,斤斤計較于細枝末節,在不經意中忽視了對詞作意境的努力創造,這使他們的詞作意味淺薄,缺乏動人的藝術魅力。王國維之論,標志著我國古代對詞味生成論說的最高成就。對藝術表現與詞味關系之論,在現代詞學中仍有承傳。如:夏敬觀的《蕙風詞話詮評》云:“矜者,驚露也。依黯與靜穆,則為驚露之反。而依黯在情,靜穆在神,在情者稍易,在神者尤難。情有跡也,神無跡也。驚露則述情不深而味亦淺薄矣,故必依黯以出之。能依黯,已無矜之跡矣。神不靜穆,猶為未至也。”[2](4588)夏敬觀認為“驚露”與“依黯”及“靜穆”是截然相反的,前者在藝術表現上體現為缺乏涵詠吟味,下字用語過于直切淺白,其直接導致的結果是使創作主體情感表現不深致,詞作韻味不見醇厚。其又云:“對偶句要渾成,要色澤相稱,要不合掌。以情景相融,有意有味為佳。”[2](4595)夏敬觀對詞作造句用語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還強調說“以情景相融,有意有味為佳”,亦即在情感表現與寫景狀物高度融合的基礎上,創作出富于藝術魅力的詞作。夏敬觀將富于審美意味作為詞作藝術技巧運用與語言表現的首要原則。
[1]張璋,等.歷代詞話[C].鄭州:大象出版社,2002.
[2]唐圭璋.詞話叢編[C].北京:中華書局,1986.
[3]王國維著,徐調孚注,王幼安校訂.人間詞話[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4]張璋,等.歷代詞話續編[C].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
[5]孫克強.唐宋人詞話[C].鄭州:河南文藝出版社,1999.
[6]陳廷焯著,杜未末校點.白雨齋詞話[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
I207.1
A
1002-2007(2010)04-0026-05
2010-06-25
胡建次,男,教授,山東大學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文論。
2007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古代文論承傳研究”(項目編號:07cwz001);江西省社會科學“十一五”規劃項目“中國古典詞學理論批評承傳研究”(項目編號:08wx37)。
[責任編輯 叢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