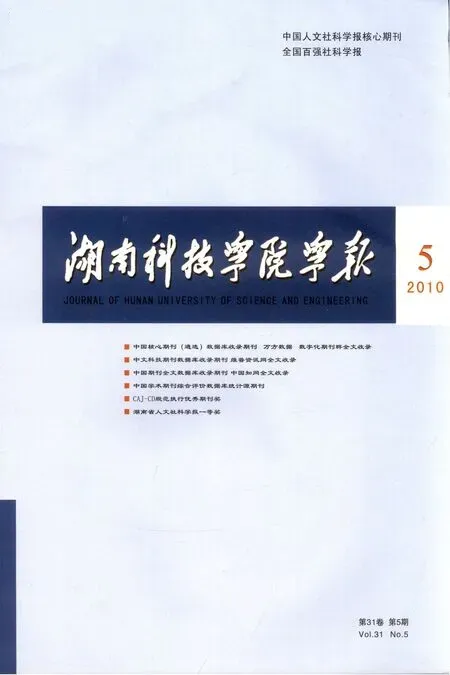兗州興隆寺塔興建及地宮供養佛舍利之寺院關系考
萬 里
(湖南省社會科學院 哲學研究所,湖南 長沙 410003)
兗州興隆寺塔興建及地宮供養佛舍利之寺院關系考
萬 里
(湖南省社會科學院 哲學研究所,湖南 長沙 410003)
兗州市興隆寺塔地宮出土的宋嘉祐八年“安葬舍利”碑文中提及了龍興寺、精妙寺和重光寺三個寺名以及三十余個院名。這些寺、院之間是什么關系,學術界有著不同的看法。然而,這涉及到該寺塔的修建究竟是一種基本上局限于宋代龍興寺一所寺院及其分院的單獨行為,還是一種較為廣泛地動員和求得了當時兗州佛教界支持的教界集體行為以及部分施主支持的社會行為。經辨析考證,除了少數“院”為宋代兗州龍興寺的下屬“分院”外,絕大部分“院”應該是獨立的佛教寺院,它們與龍興寺之間并無隸屬關系。規模宏大雄偉之宋代兗州龍興寺塔,正是在宋代兗州各佛教寺院僧眾以及諸多社會信眾的助緣之下修建成功。
興隆寺;龍興寺;佛塔;地宮;安葬舍利碑
關于兗州興隆塔地宮“安葬舍利”碑文的內容,2008年底,兗州市博物館樊英民先生在自己的新浪博客中發表了《興隆塔地宮安葬舍利碑解讀》一文;隨后山東大學譚世寶教授也撰寫了《兗州興隆塔地宮宋嘉祐八年十月六日“安葬舍利”碑考釋》[1]一文。兩篇文章對該碑文進行了比較詳盡而又精審的考證釋讀,將碑文中的主要內容大致厘清,為后續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篳路藍縷,功莫大矣。本文擬就兩文中尚未涉及或者尚且存疑的一些問題試做補充考證,以供討論參考。
一
據統計,碑文中提及了龍興寺、精妙寺和重光寺三個寺名,以及三十余個院名。樊英民先生認為:“……各種院的名稱有30多個,其中還有首都東京的等覺禪院等。僅‘當寺’(龍興寺)以下的‘院’就有21個,還沒包括法語所在的大悲院。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寺’和‘院’是一種什么關系?這20多個院都是屬于龍興寺的嗎?如是,這寺的規模真夠大的了,為什么只有各院院主而未見有寺主的名字呢?還有,難道兗州就只有一個寺嗎?為什么上文曾引過的兗州延壽寺也未出現?既然能有東京的寺院,為什么兗州所屬各縣的寺院一個也沒有?筆者不具備這方面的知識,不敢妄下結論。”譚世寶教授則認為:“‘龍興寺泗州院’為本寺一個分院之名,可以由碑文以下的提法得到充分證明。本‘行狀’最后說法藏的遺留佛寶輾轉‘付與當寺大悲院主講經僧法語起塔供養’。這里的‘當寺’意思就是本寺,代指上文的‘龍興寺’。故‘付與當寺大悲院主講經僧法語起塔供養’,就是把法藏的遺留佛寶交給本寺大悲院主講經僧法語起塔供養。因此,其后文才參與‘起塔供養’的僧人大多數只記其所屬之院而不及其寺,都是屬于本寺其他各分院的僧人,只有少數是屬于重光寺泗州院等以及精妙寺地藏院的比丘尼。”兩者比較,可以看出,對于碑文中寺、院之間錯綜復雜而又表述得并不清晰的關系,樊英民先生予以存疑,譚世寶教授則肯定所有的“院”都系于相應之“寺”的歸屬之下,因此,在該文附2之《參與建塔供養佛寶功德的僧俗人員及寺院表》(按:該表對“院”名的統計為30個,實際為34個,其中包括未明確系錄“寺”之歸屬的“經藏院”兩出,以及在“龍興寺泗洲院”之外出現的“泗州院”一出)中,除了將緊接著“重光寺泗洲院”出現的“無量壽院”系于重光寺之下,以及明確標明為“重光寺觀音院”和“精妙寺地藏院”的兩“院”外,該表將其他的全部僧尼“院”均系于龍興寺之下,包括所指明確的“東京等覺禪院”在內。這樣,龍興寺轄下的“院”便有幾近三十個之多。
這些“寺”“院”之間到底是一種什么關系?絕非一個簡單的數目統計問題,而是涉及到,作為兗州歷史上最為重要的建筑之一、也是被視之為佛教界莫大功德之一的興隆塔的修建,以及佛祖舍利的安放,是一種基本上局限于龍興寺一所寺院及其別院(“下院”或“分院”)的單獨行為,還是一種較為廣泛地動員和求得了當時兗州佛教界支持的教界集體行為以及部分施主支持的社會行為。因為我們知道,即使在生產力相當發展的當代,要修建或者修復一座如此規模、耗資巨大的佛塔,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況是在古代。而且,在唐、宋時期,官方對各地佛教寺院和道教宮觀的的規模始終是予以控制的,因此,作為一所地方的佛教寺院,政府能夠容許其發展到多大的規模,以及在政府對度牒(出家人數量的)的嚴格控制下其能夠發展到多大的規模,從而具有多大的經濟能力,還是一個問題。
二
首先,讓我們從行文的習慣上探討該碑文所載“寺”“院”之間的關系。
按照傳統的行文習慣,在類似的文字表述中,一般將主持者以及作為該功德主體寺院的名字排列在所有參與者的最后,以示對作為“客體”的參與人員及單位(寺、院)的尊重。該碑文正是如此。
從該碑文的第1行至12行“至嘉祐八年癸卯歲,將上件功德舍利,付與當寺大悲院主講經僧法語,起塔供養”,表述的是該項功德工程的緣起、付諸實施的經過以及主持者為誰。從第13行開始,是給予助緣(資助)的供養者和功德主(者)的名單。該名單至第27行之“大悲院主修塔功德主講經沙門法語,小師洪才、洪江、洪潤、洪泰、洪道”結束,表明作為大悲院主的沙門法語不但是該項功德工程的主持者,還是率領該院諸位“小師”一道積極參與的出資者。列名于助緣供養者和功德主名單中的大悲院諸僧之所以排列在最后,正是遵照了傳統的行文禮儀習慣。如此看來,“大悲院”與列名于之前的其他寺、院,有著明顯的“主”“賓”關系。當然,這既可以是不同“寺”屬之間的“寺”“院”的關系,也可以是同一“寺”屬之間的“院”的關系。
該碑文對于寺院僧人的排列還遵循著另一傳統習慣規律,即以僧人的地位尊卑為序(是否還有以年齡長幼的順序排序,以及以出資多少的順序排序,因無法得知諸僧尼的年齡,以及不知各自出資數目的多寡,故不得而知)。首先列名的是“華嚴院管內僧正講經論賜紫沙門行深;延圣院主僧判賜紫沙門可昱;當寺上生院主傳大乘戒講經論沙門惠旻”;作為出家人列名最后的是“重光寺泗洲院主尼志真、志全;無量壽院尼法堅;精妙寺地藏院主尼志演,小師惠清、惠喜、義達;重光寺觀音院主尼守遇、守榮、守興”等。在古代中國男尊女卑的語境中,女性出家人比男性出家人的地位為低,甚至要堅守更多的戒律,此為眾所周之的事實,毋庸贅言。在這一名單中,大悲院諸僧排列在社會各界所有“助緣修塔維那眾”、甚至包括各位尼師的后面,正是出于一種自謙和對他人參與“助緣修塔”的尊重。
“僧正”又稱僧主,為中國古代管理佛教事務的僧官之一,南北朝時期為中央僧官的最高職官,唐、宋以降多為地方各州地位最高的僧官,其副手為副僧正,僧判則是地位次于副僧正的僧官。北宋元照律師所撰之《芝園集》上卷《溫州都僧正持正大師行業記》云:“郡倅唐公(谷)舉師為僧判,次遷副僧正。郡守張公(濟)性嚴,少交游,待師獨厚,又遷都僧正。”[2]宋贊寧《大宋僧史略》卷中云:“所言僧正者何?正,政也,自正正人,克敷政令,故云也。蓋以比丘無法,如馬無轡勒,牛無貫繩,漸染俗風,將乖雅則。故設有德望者,以法而繩之,令歸于正,故曰僧正也。”[3]“管內僧正”沙門行深和“僧判”沙門可昱,無疑是兗州地位最高和次高的僧官,故排列在最前面;而“傳大乘戒”者作為一個地區數量并不會很多而且權重位顯的“戒師”,雖然“沙門惠旻”是“當寺”也就是龍興寺的“上生院主”,也必須凸顯出來,名列前茅,而不能與大悲院的沙門法語等人列名于最后,況且,“上生院”與“大悲院”雖然寺屬相同,但畢竟還是“一家(寺)”之中的“兄弟(不同“院”)”關系,尊之在前也順理成章。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三所“院”中,有著“當寺”指稱的是排在第三位的“上生院”,而不是列名第一的“華嚴院”和第二的“延圣院”,可見這兩個“院”都不會是龍興寺的“下院”、“別院”或者“分院”,否則“當寺”一語應該寫在“華嚴院”之前。
遵照這一思路,再看下面的名單。碑文的第20行和21行,在“凈土院主講經沙門惠燈;西彌勒院主僧智海”之后、“經藏院主僧普勤;泗州院主講經沙門惠信;三學院主僧守遠;經藏院僧慶遇”之前,有“東京等覺禪院賜紫僧守祥”的名號。譚世寶教授認為包括“東京等覺禪院”及其之后列名的“經藏院”、“泗州院”和“三學院”,都是兗州龍興寺的“分院”(見唐文及附錄2)。如果說按照行文習慣的排列和理解,“東京等覺禪院”名目之前的那些“院”名都是延續于“當寺上生院”之后,還可以被認定是龍興寺的“分院”或者“別院”,那么之后的“院”則可以肯定與龍興寺沒有隸屬關系了,因為這些“院”名系于“東京等覺禪院”的后面。不管在古代還是在現代,都絕對沒有這樣的行文表述方式。
三
就筆者有限的閱讀面,在古代,以“等覺”命名的佛教寺院極為罕見,筆者僅僅只檢索到四所,分別是東京的等覺禪院、徽州府的等覺院、福建浦城縣的等覺寺(院)和云南蒙化府的等覺寺,此外,福建閩縣還有一所名稱稍有差異的東禪等覺院。
徽州府的等覺院為徽州太平興國寺的十所別院之一。徽州府的太平興國寺建于唐肅宗至德二年(757),初名興唐寺,宋太平興國中改寺額為“太平興國寺”,寺中“有戒壇”,并非禪院[4]。
福建浦城縣的等覺寺(院)比較有名,是因為幾位宋代著名文人所留下的記載。北宋蘇頌所撰之《翰林侍講學士正奉大夫尚書兵部侍郎兼秘書監上柱國江陵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贈太子太師謚文莊楊公神道碑銘并序》稱:“……浦城者,則其邑有舊構佛祠,勅號等覺禪院,以為殖福之地。又有施田以飯其凈眾。今族孫進士倜主其世祀云……”[5]南宋真徳秀所撰之《楊文莊公書堂記》稱:“浦城夢筆山等覺院,邑人禮部侍郎楊公澄為本縣令日所建也。侍郎之子文莊公少讀書于此山。既去,以文學節義擅聲中朝,為薦紳標式后人,即其處為書堂,繪公父子祠之。嘉定中郡守李公大異,作五大字表其額。”[6]在《福建通志》中,浦城縣的這一先為“佛祠”后為“書堂”的等覺院名為“等覺寺”[7]。
云南蒙化府的等覺寺為南詔時期蒙氏所建,在《明一統志》[8]、《清一統志》[9]和《云南通志》[10]中均有記載,位于蒙化府治的東部。
以上這些名為“等覺”的寺院均與兗州沒有任何關系,不必細論。值得注意的是,在宋代以前,兗州確實曾經有過一所名為“等覺”的佛教寺宇。這所寺宇建于五代時后晉髙祖天福五年(940)。宋王欽若等撰《冊府元龜》載:“五年二月甲子,天和節,道釋賜紫衣、師號者凡九十人;寺宇賜名額者凡二十五所:東京寶繩、寶像、寶花、法林,西京惠雪,京兆普靜,兗州等覺、玄機,蔡州吉祥,懷州妙理,襄州護國,許州定水,貝州寶剎,博州金繩,耀州密行,代州仁壽,鄴州感化,潞州妙士,定州毘城,岐州善覺、遺相,澤州解空,慈州集圣,鄆州真覺……”[11]但是,這所后晉朝廷賜名額的寺宇應該不是“安葬舍利”碑文中的“等覺禪院”,因為碑文中已經指明是“東京等覺禪院”。而且后晉兗州所建的名為“等覺”的是“寺”而非“院”,并且也不是兗州龍興寺的“下院”、“分院”或“別院”。
東京等覺禪院是一所屢見于史籍記載的著名佛教寺院。據明李濂撰《汴京遺跡志》巻十一“祠廟庵院”記載:“等覺院在安遠門外之西北,宋太祖乾德六年(開寶元年,968)創建,金季兵毀。”[12]又《汴京遺跡志》卷十“寺觀”載:“上方寺在城之東北隅安遠門里夷山之上,即開寶寺之東院也,一名‘上方院’。……上方寺塔前有行書碑一,題曰《大宋東京右街重修等覺禪院記》,乃咸平戊戌(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尚書職方郎中賜紫金魚袋王嗣宗撰,隴西彭太素書,字體流暢,頗類西安《圣教序》。汴城石刻惟此為最耳。”[13]彭太素所書的《大宋東京右街重修等覺禪院記》為法書精品,屢見于后世書畫譜和金石碑刻著作著錄。與東京(新)龍興寺(宋太宗即位后,改敕額為“太平興國寺”)一樣,東京等覺禪院為宋代開國之初官方所建之皇家寺院。該寺宇修建完畢后,宋太祖與其弟趙光義(后來的宋太宗)曾經于開寶九年(宋太宗太平興國元年,976)八月去東京新龍興寺和該寺宇巡幸[14]。
東京(新)龍興寺前身的是唐代的龍興寺,與包括兗州龍興寺在內的天下各州郡之龍興寺一道為唐代所勅立(包括新建和對原有寺院的改勅名額)。宋陳思稱:“……中宗初復位,天下州郡皆置龍興寺一所。此碑以景龍四年五月立。”[15]宋沙門志盤則稱:“玄宗,……勅天下諸郡建開元寺、龍興寺。”[16]兩者所載天下諸州郡創建龍興寺的時間不一致,因其較為復雜,又偏離于本文的題旨,留待另文討論。唐代除了敕立佛教的開元寺和龍興寺外,先后所敕立的還有以“開元”和“龍興”命名的道教宮觀,并作為“……八十一州郭下僧尼、道士女冠等國忌日各就龍興寺、觀行道散齋”[17]之處所。基于唐代天下諸州郡之龍興寺均為奉敕所建或敕額,性質功能相似,之間有著一定的互動關系應該是在情理之中。而東京等覺禪院與東京(新)龍興寺同為趙宋王朝的皇家寺院,二者互動關系密切,故兗州龍興寺與東京等覺禪院的交往關系是否由此建立并延續下來,尚可深入考察。我們知道,在宋代,兗州當地及附近還有一些比較著名的寺院,如曾經作為宋真宗東巡泰山行宮的延壽寺(回鑾寺)等,均未見于該碑文的寺院名單中,應該是沒有參與這項意義重大的活動。而遠在汴京(開封)的東京等覺禪院卻能夠參與,表明該禪院或者其僧侶與兗州龍興寺有著一種較為特殊的密切關系,則是無疑的。
如前所述,“安葬舍利”碑文中列名于“東京等覺禪院”之后那些“院”名,可以肯定與兗州龍興寺沒有隸屬關系,那么是否可能為東京等覺禪院的“分院”或“別院”呢?如前所述,創建于北宋初年的東京等覺禪院是一所全新的寺院,在北宋末年便毀于金兵之手,此后未見再復建,存在的并不長,考諸史籍,亦未見其有“分院”或“別院”的記載,故不能如此認定。而且,千里迢迢,一所“母院”及其若干“子院”都各自作為對外的“主體”參與贊助兗州龍興寺佛塔的修建工作,似乎也是不大可能的。實際上,這些“院”都應該是兗州當地的寺院。
四
要搞清碑文中“寺”與“院”的關系,可以先了解佛教“寺”與“院”的差別。一般而言,“寺”與“院”性質的區別不是很大,都是佛教僧眾生活并進行宗教活動的場所,故往往“寺院”并稱。但具體而言,又有一些細微的差別。這種區別主要是在規模上。就佛教僧人的居住修行處所而言,院最初本是寺內的一部分,即寺內的別舍。但唐宋以降,逐漸獨立出來成為居住修行處所的名稱,只不過院的規模一般比寺略小。而庵,則是多指佛教出家的女眾(比丘尼)居住修行的處所(但也不盡然),其規制一般也比“寺”或“院”要小。在很多情況下,由于“院”的規制比“寺”要小,故有時“院不立佛殿,惟樹法堂,表佛祖所囑受當代為尊也”[18]。
正是因為“院”與“庵”的規制比“寺”小,故經常見到佛教寺宇由“院”升格為“寺”的記載,亦有由“庵”升格為“院”的記載。反過來,也有因“寺”荒廢、規制縮小而改名為“院”者。作為“寺”的“分院”、“別院”、“下院”或“支院”,不一定稱之為“院”,也可以稱“寺”、“庵”或“堂”;“院”之下也有稱之為“院”或“庵”的下院;“庵”之下也有稱之為“庵”的下院。絕不能一概而論。而且,由于“院”的規制相對要小,對其中的建筑設施要求也不如“寺”高,故在古代,作為佛教僧眾居住修行處所的“院”遠遠比“寺”多得多。“安葬舍利”碑文中所體現的正是這種狀況。我們可以從其他文獻資料中予以證實。
以上所述之“分院”、“別院”、“下院”或“支院”的種類多見于史籍,如:“明慶寺在木子巷北,唐大中二年建,為靈隱(寺)下院,大中祥符五年改今額。……長生庵在溜水橋西城下,為昭慶(寺)下院。……云居圣水寺,舊名‘云居禪庵’,在七寶山。元元貞間中峰禪師建。……上方庵為圣水(寺)下院。”[19]“演福庵在髙峯無門洞之陰,俗稱南天竺。山下有演福寺,舊址有夕佳樓、白蓮院,隋開皇建,今廢。庵即寺之下院。”[20]“普化庵近香積寺,系香積(寺)下院,僧無為重建。”[21]“凈土庵即凈土寺下院,去縣十八里。……萬歷二十八年,朱文元舍地,僧德祺建。”[22]“純一院,宋嘉定年間勅建。元至正兵毀。洪武二十四年立為叢林,有下院曰‘慧林庵’。”[23]“佛慧寺……下院名‘圓通庵’,在六寶村;別院名‘白業堂’。”[24]
因“寺”荒廢、規制縮小而改名為“院”者,如:“智果院在武林門外東關六里,舊為宋東山萬壽寺。寺敞可容數百僧,四面環水,蓮花盛時香聞里許。有亭臨其上,曰白蓮亭。外有涵虛、鏡水二閣。中有白蓮橋。米芾題‘且吃茶匾’。元末兵毀,其地盡入民居。洪武三年,智果僧文□于舊基得觀音像一座,三焚而不毀者,未辨為幾百年所遺,因建殿為供匾,曰‘智果下院’,俗為‘觀音庵’。萬歷七年,僧明繡拓基以廣其制,創大法堂。萬歷戊申,僧海成、照心復捐資,辟地浚池,種蓮作亭,以追舊跡。”[25]
但最多的還是因寺宇的規制擴大從而由“院”升格為“寺”,亦見由“庵”升格為“院”。如:“侯官南報恩院,南澗寺南。大中十一年,觀察使楊發以‘隙游亭’地,命僧鑒空創寺及塔七層。咸通九年,敕號‘神光之塔’,院曰‘報恩塔院’。……太平興國二年,升為寺。明道中,始為禪剎。”[26]“護國天王院,欽平上里。本會昌中竹林廢寺。大中初復之。咸通中,改今額。皇朝慶歷中,升為禪寺。”“精嚴寺,三秀里。長興二年置。初號‘潯湖塔院’。……皇朝大中祥符六年,升為‘精嚴(寺)’。”[27]“鷲峰院,永西里。漢乾佑三年,……僧凈慧卜庵居焉……皇朝寶元二年,升為院。崇寧間,改為神霄宮,尋復為院。”[28]“鳳池寺,懷賢里。漢乾佑元年置,本僧慧覺塔亭也。……二年正月,始為禪院,賜號‘鳳池報慈’。皇朝紹興八年,以為顏門下岐焚修之場,改‘顯忠嗣慶’為額。”“賢沙寺,懷賢里。升山之下。梁開平元年置。本安國宗一禪師塔院也。……晉開運三年,淮兵寇閩,焚掠幾盡。皇朝天禧二年,僧戒珠始葺而新之。紹興三十一年,朱丞相倬奏請為功德院,敕賜‘教忠崇報’為額。”[29]“粵靈巖寺乃莆山之靈秀焉。……昔梁陳間,邑儒滎陽鄭生……獻其居為金仙院,即陳永定二年庚申也。……。隋開皇九年升為寺焉。”[30]文獻中類似記載甚多,不再贅引。由此可見,在一般情況下,“寺”與“院”的性質雖然并無多大區別,但其規制確實還是有所差異,故常常有所謂“院”升格“寺”的情況出現。
那么究竟多大的規模稱之為“寺”,多大的規模稱之為“院”,多大的規模稱之為“庵”,以及多大的規模又可以由“庵”升格為“院”、由“院”升格為“寺”呢?筆者尚未見到直接的資料,無法斷定。實際上,也不可能由官方或民間(教界)制定一個統一的、恒定的標準。但是,從一些相關的文獻中還是可以看出蛛絲馬跡來。
歷史上,除了少數佞佛的皇帝執政時對佛教的發展采取支持鼓勵的政策外,一般而言,出于經濟利益的沖突,以及恐怕寺院宮觀藏匿歹徒、各種宗教教團坐大從而威脅到政權的穩固,總是對各種宗教、包括佛教采取限制發展的政策。歷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滅佛”便包括趙宋建國之前的后周世宗柴榮。宋太祖即位后,雖然終止了周世宗的廢佛政策,但仍然采取各種措施和手段控制佛教的自由發展,例如采取“系帳制”和“敕額制”等[31]。以致有“宋法,非敕額不敢造寺”之說[32]。而從政策上允許系帳和敕額而得以存留的寺院,除了其他必須具備的條件外,寺院的規模也是一個重要的指標。具體而言,即寺院須有多少間屋宇。在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情況下,對寺院屋宇數量的要求有所變動,一般不能少于一百間;在特殊的情況下如新皇帝即位受徽號時,亦有特殊的恩敕,但也不能少于三十間。少于三十間屋宇的寺院,則必須具備另外的特殊條件,此即《續資治通鑒長編》所載:“先是上封者言,諸處不系名額寺院多聚奸盜,騷擾鄉閭,詔悉毀之,有私造及一間已上,募告者論如法。于是詔寺院雖不系名額而屋宇已及三十間,見有佛像,僧人主持,或名山勝境高尚庵巖不及三十間者,并許存留。自今無得創建。”[33]
然而,人們對宗教信仰的自發訴求,并不是官方的嚴密限制就可以控制得了的,因而事實上民間私造的寺宇大量存在,只要不是“多聚奸盜,騷擾鄉閭”,地方官員對此也是開一只眼閉一只眼。這些民間私造的寺宇大多規模較小,出家僧(尼)眾較少,無法稱“寺”,也不能稱“寺”,便多以“院”、“庵”、“堂”等命名。以致出現了 “僧(尼)院”遠比 “僧(尼)寺”多的現象。
由南宋陳傅良等撰寫、梁克家署名的《淳熙三山志》卷三十三至卷三十八為“寺觀類”,其中詳細記載了截至南宋淳熙年間之福建三山(福州)地區的佛教寺院、道教宮觀的歷代建置沿革、存留狀況及稅負數額等,是一份不可多得的佛寺建置史和經濟史的寶貴資料。
在該志所載錄的數以千計的佛教寺院庵堂中,“院”的數量居絕大多數。例如,該志卷三十八記載羅源縣的佛教寺院六十一所,其中五所為“尼院”,一所為“庵”,其余全部稱之為“院”,竟沒有一所稱為“寺”的;而且只有四所具有寺(院)額(即朝廷的“賜額”)從而具備官方承認之存在的合法性。其中還有許多是兗州龍興寺“安葬舍利”碑文中所出現的院名,如“觀音院”、“三學院”、“泗洲院”、“水陸院”、“慈氏院”等,而且有院名完全相同但所指非一的“院”,如“觀音院”就有三所,分別是唐咸通元年所置位于安金里的“觀音院”、后晉天福六年所置位于臨濟里的“觀音院”和宋乾德三年所置位于霍口里的“觀音院”。這三所“院”所置年代不同、所處地理位置不同,他們之間并無任何隸屬關系。
該志卷三十七記載了永福縣的佛教寺院七十一所,其中三所為“尼院”,一所為“塔院”,一所為“庵”,一所為“堂”,只有二所為“寺”,即“中峰寺”和與兗州龍興寺“安葬舍利”碑文中同名的“重光寺”,其余都是“院”,而且只有五所具有寺(院)額。也出現了與兗州龍興寺“安葬舍利”碑文中同名的“上生院”、“觀音院”、“羅漢院”等。有四所“觀音院”,分別是唐咸通二年所置位于永安里的“天柱觀音院”、后唐天成三年所置位于平蓋里的“謝洋觀音院”、宋建隆二年所置位于感德里的“上觀音院”和所置年代不詳位于待旦里的“中觀音院”,之所以分別以“天柱”、“謝洋”、“上”、“中”限定語加之于這些“觀音院”的前面,應該是當地人為了有所區分,避免混淆所致。有二所“資福院”,分別是唐景福元年所置位于義仁里的“上資福院”和唐光化二年所置位于保安里的“下資福院”。有二所“崇壽院”,分別是后唐長興二年所置位于義仁里的“上崇壽院”和太平興國二年所置位于唐元里的“下崇壽院”。這些所置年代不同、所處地理位置不同但卻完全同名的“院”,之間并無任何隸屬關系,冠以“上”、“下”,亦與前述區分“觀音院”的目的相同。
《淳熙三山志》對其他各縣佛教寺院的記載情況大致相同,不再贅引。
上述《淳熙三山志》對重名寺院的區分處理,與兗州龍興寺“安葬舍利”碑文中之“南觀音院”和“重光寺觀音院”以“南”、“重光寺”所指限定來與另一所“觀音院”相區別,以及“東羅漢院”、“西羅漢院”和“東彌勒院”、“西彌勒院”以“東”、“西”來區別同名的“羅漢院”和“彌勒院”,其目的性質完全相同。所謂的“東”“西”,其實分別指其在兗州當地的地理位置。與《淳熙三山志》中之“天柱”、“謝洋”、“上”、“中”、“下”等出現的情況完全一樣。這種區分,既可能是龍興寺興隆塔地宮“安葬舍利”碑文的撰寫者或《淳熙三山志》的作者所為,更可能是當時民間人士對同一城市或區域內出現之重名寺院所處地理位置的不同而約定俗成的區分稱謂,或者是寺院的修建者和居住者(出家僧眾)為了與其他重名寺院的區分而自我命名。如果這些以“東”“西”來區分的“羅漢院”和“彌勒院”都是龍興寺轄下的“分院”或“別院”,在同一個寺院的統一規劃之下,能夠起的名字應有盡有,何必重名?
值得指出的是,在唐宋時期,一些歷史悠久、規模較大、實力雄厚的寺院,其名下出現的某些“院”,并非是與其有著隸屬關系但獨立于該寺院整體建筑群之外的“分院”、“別院”或“下院”,而是某一所寺院建筑群中為供奉某種特定對象或具有某種特定功能的“院落”。正如李森先生在《青州龍興寺院落考證》一文中所說的:“眾所周知,中國古代名剎大多由若干院落組成。迄今為止,我們在文獻和石刻資料中已發現了龍興寺的八個院落——佛堂、新羅院、九曜院、天宮院、志公院、百法院、藥師院和臥佛院。龍興寺究竟建有多少院落? 囿于資料,難以詳知。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這是一座典型的多院式組合寺院。張弓先生指出:‘多院式規格雖有不同,卻都是大寺。’”隨后,該文對這八個“院落”逐一進行了考證。例如:志公院“顯然是因供奉志公和尚而得名”;藥師院“顯然是因供奉藥師佛而得名”;“臥佛院的得名,顯然是因院內供奉著釋迦牟尼涅像”;“天宮院應是專門供奉彌勒的院落”;“九曜院的建造,反映了五代時期寺內存有九曜和熾盛光佛信仰情況”;“百法院的建造,反映出寺內存在唯識宗信仰”;至于新羅院,該文引陳尚勝先生的論述說:“新羅院是新羅僑民在佛寺內設立專門用以接待客僧的院館。”由此,李森先生得出結論說:“(青州)龍興寺這時應是一座多院式組合結構寺院了。”[34]正是由于系于某所寺院名下的某些“院落”是該寺院建筑群中為供奉某種特定對象或具有某種特定功能的“院落”,因此這些“院落”不會重名,亦即不會重復出現。以青州龍興寺為例,便不會出現兩個以上的新羅院、九曜院、天宮院、志公院、百法院、藥師院和臥佛院等院落,而只是如他兗州龍興寺一樣,以該院落在整個寺院建筑群中所處的位置而以“上”、“下”、“東”、“西”、“南”、“北”等方位名稱加以區分。如此看來,兗州龍興寺興隆塔地宮“安葬舍利”碑文中所出現的“南觀音院”、“觀音院”、“東羅漢院”、“西羅漢院”和“東彌勒院”、“西彌勒院”應該不是該寺院建筑群落中的“院落”。基于此,“安葬舍利”碑文中所出現的“東律院”,因其有方位前置詞“東”字,也不可能是該寺院建筑群落中的“院落”,甚至不是與其有著隸屬關系但獨立于該寺院整體建筑群之外的“分院”、“別院”或“下院”。因為既然有“東律院”,必然有“西律院”,如同“東”、“西”羅漢院和“東”、“西”彌勒院一樣,如果他們同屬于兗州龍興寺之“別院”或“院落”,那么在龍興寺興修佛舍利塔如此巨大的功德事務中,“西律院”及其的僧人名目未見著錄,又到哪里去了呢?
五
討論至此,已經非常明顯,“寺”與“院”之間并無必然的隸屬關系。能夠明確判定為兗州龍興寺之“別院”或“下院”的只有在碑文第2行中出現的“泗洲院”、第14行中出現的“上生院”,以及在第12行和第27行中重復出現的“大悲院”,第21行出現的“泗州(洲)院”因為列名于“東京等覺禪院”的后面,亦似乎不大可能是碑文第2行中出現的那所“龍興寺泗洲院”。除此之外的其他寺院,大部分應該是兗州府城(滋陽)當地或附近州縣的寺院。
在《淳熙三山志》中,記載了各所寺院每年所承擔的賦稅率,數額分別為十數文、數十文、數百文、數貫、十數貫不等,數目均不大,還有僅僅只承擔“一文”賦稅的,如:“侯官開化院,縣西。景祐四年置。舊產錢一文。”“侯官西法林尼院,州西南。崇寧二年置。舊產錢一文。”[35]“連江縣……寶積院,崇德里。嘉祐二年置。舊產錢一文。”[36]“長溪縣……福生院,望海里。開寶八年置。舊產錢一文。”[37]“寧德縣……白蓮院,水漈里。太平興國七年置。曾記:建炎二年,建寇焚毀,后重立。舊產錢一文。”[38]甚至有因無產業,連一文錢賦稅都不承擔、也無法承擔的,僅僅在州城及其附廓,這樣的寺院就有九所,即:“閩縣九仙天王院,州東南。元年置。崇寧三年為崇寧觀廚宮。建炎元年仍舊。無產錢。”“報恩尼院,加崇里。天圣二年置。舊無產錢。”“吉祥院,加崇里。景祐元年置。舊無產錢。”“多寶院,易俗里。(景祐)四年置。舊無產錢。”“廣福院,仁惠里。康定元年置。舊無產錢。”“鷲峰院,永盛北里。(熙寧)三年置。舊無產錢。”“天王院,歸善里。(元豐)二年置。舊無產錢。”“德慧塔院,易俗里。(元符)三年置。舊無產錢。”“云門庵,縣南洋嶼。紹興初,大慧禪師宗杲居此。……舊無產錢 有產屬地主家一所。”[39]顯而易見,從這些寺院所承擔的賦稅率看,其規模都不是很大,甚至有些只能維持最基本的生存。
以《淳熙三山志》所載情況度之,參與修建兗州龍興寺佛塔和安葬佛舍利的寺院,大多數應該是民間私造、規模不大、經濟能力有限、且并未獲得朝廷敕額的寺院。這些民間私造的寺院,由于受到官方度牒指標的控制,出家的僧眾不一定很多。基于此,故這些寺院在歷代傳世的史籍中沒有、也不可能留下記載。就此,“安葬舍利”碑文便有著不可替代之寶貴的文獻價值。這一推測還可以從許多其他的文獻中得到印證,限于篇幅,這里不再展開討論,有些問題,擬另撰文涉及。
附帶提及,從“安葬舍利”碑文中所出現的寺院名稱看,包括有歷史上佛教的諸多宗派和信仰特色。由此可見,在北宋時期,佛家的諸多宗派都有著一個繁榮復興的態勢,真可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他們在修建佛塔以供奉佛舍利這一功德因緣下,和諧與共,展現了佛教教義精神的慈悲為懷。
據王禹偁《大宋兗州龍興寺新修三門記》碑文可知,即使是作為“東兗招提之甲”的兗州龍興寺,想將“建于(唐宣宗李忱)大中年”間之“位歷數朝,時踰百祀,風雨所寇,簷楹不完,寺眾羞之”的寺院“三門”“思所整葺”也“力未支也”[40],那么,在社會經濟生產力并不十分發達的宋代,兗州寺院出家眾以及社會信眾等功德主以民間助緣的方式籌集資金修建如此規模(這里假定當時所建造的即是現在所見到之高十三層的)佛塔,究竟有多大的工程量、需要耗費多少資金、花費多長的時間?現在無法考索。但是,參考當時官方所建之類似佛塔,便可得知其工程巨大、所費不貲、修建時間不短!據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宋)太宗端拱二年……八月……丁巳,……先是,上遣使取杭州釋迦佛舍利塔置闕下,度開寶寺西北隅地造浮圖十一級以藏之,上下三百六十尺,所費億萬計,前后踰八年,癸亥工畢,巨麗精巧,近代所無。”[41]北宋東京開寶寺釋迦佛舍利塔之修建,集國家之財力,還“所費億萬計,前后踰八年”,民間修建類似佛塔之艱巨,可見一斑。正是如此,我們才能深深地理解到“小師懷秀”為了完成光正大師法藏之造塔安葬“世尊金頂骨真身舍利”的心愿,數十年時間,想方設法,甚至以“欲乞岱岳□回鑾驛,乞賜名額”的方式求得朝廷的重視和支持,最終“年老,無力起塔”的艱辛與無奈。薪火相傳,精神不滅,龍興寺大悲院主講經僧法語從小師懷秀手中接過這一沉重的接力棒,終于在宋代兗州各佛教寺院僧眾以及諸多社會信眾的助緣之下,將佛塔修建成功,其艱辛困苦,非當事者是難以體味的。
規模宏大雄偉之宋代兗州龍興寺興隆塔的興造,不止如“安葬舍利”碑文所述之完成了“安葬于闐光正大師從西天取得世尊金頂骨真身舍利”的莫大功德,了卻了西域于闐國遠赴中原的光正大師法藏以及龍興寺小師懷秀等幾代僧人的心愿,譜寫了一曲中外(西天,即印度)文化交流和西域與華夏民族文化交流的華麗樂章,在當時產生了“教化十方”的巨大作用,更綿延千年,為后世留下了一份寶貴的宗教文化遺產。保護好這份寶貴的文化遺產,讓其在新時代煥發新生,產生更大更佳的社會效益,是肩負在當代國人尤其是兗州各界人士身上的重任。
[1]載兗州市民族宗教局編:《山東省兗州市佛教歷史文化研究參考資料》,第7~30頁,2009年4月。
[2]宋元照撰:《芝園集》,《卍新纂續藏經》第59冊,第658頁。
[3]宋贊寧撰:《大宋僧史略》,《大正藏》第54冊,第242頁。
[4]見清趙宏恩等監修、尹繼善等重修:《(雍正)江南通志》卷四十七“輿地志”,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08冊,第462~463頁。
[5]見宋蘇頌撰:《蘇魏公文集》卷五十一,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92冊,第546頁。
[6]宋真徳秀撰:《西山文集》卷二十六“碑銘”,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74冊,第398~399頁。
[7]見清郝玉麟等監修:《(雍正)福建通志》巻六十三“古跡二”,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30冊,第268頁。
[8]見明李賢等撰:《明一統志》卷八十六“云南布政司·蒙化廳”,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73冊,第800~801頁。
[9]見《(乾隆)大清一統志》巻三百八十八,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83冊,第197頁。
[10]見清鄂爾泰等監修:《(雍正)云南通志》卷十五“祠祀附寺觀”,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69冊,第468頁。
[11]宋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卷五十二“帝王部·崇釋氏第二”,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03冊,第54頁。
[12]明李濂撰:《汴京遺跡志》卷十一“祠廟庵院”,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87冊,第636頁。
[13]明李濂撰:《汴京遺跡志》卷十“寺觀”,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87冊,第616頁。
[14]見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十七“太祖”,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14冊,第252頁;元托克托等修:《宋史》巻三“本紀第三·太祖三”,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80冊,第114頁;《宋史》卷一百十三“禮志·禮十六”,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82冊,第190頁。
[15]宋陳思撰:《寶刻叢編》卷五“陳州·唐龍興寺碑”,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82冊,第265~266頁。
[16]宋沙門志盤撰:《佛祖統紀》卷第五十三“歷代會要志第十九之三”,《大正藏》第49冊,464頁。
[17]宋王溥撰:《唐會要》卷五十,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06冊,第645頁。
[18]北宋釋道誠集:《釋氏要覽》卷下“禪住持”,《大正藏》第54冊,第301頁。
[19]明吳之鯨撰:《武林梵志》卷一,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88冊,第15~22頁。
[20]明吳之鯨撰《武林梵志》卷三,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88冊,第55頁。
[21]明吳之鯨撰《武林梵志》卷四,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88冊,第74頁。
[22]明吳之鯨撰《武林梵志》巻六,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88冊,第128頁。
[23]明吳之鯨撰《武林梵志》卷四,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88冊,第80頁。
[24]明吳之鯨撰《武林梵志》卷四,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88冊,第75頁。
[25]明吳之鯨撰《武林梵志》巻四,文淵閣《四庫全書》,588冊,第70頁。
[26]宋梁克家撰:《淳熙三山志》卷第三十三“寺觀類一”,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84冊,第485頁。
[27]宋梁克家撰:《淳熙三山志》卷第三十四“寺觀類二”,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84冊,第502~511頁。
[28]宋梁克家撰:《淳熙三山志》卷第三十六“寺觀類四”,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84冊,第534頁。
[29]宋梁克家撰:《淳熙三山志》卷第三十八“寺觀類六”,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84冊,第567~574頁。
[30]唐黃滔撰:《黃御史集》巻五《莆山靈巖寺碑銘》,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84冊,第143~145頁。
[31]劉長東教授對此有專門的研究,參見其博士后出站報告《宋代佛教政策論稿》,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2005年。
[32]見元鄭元佑撰:《僑吳集》卷九《無錫泗州寺記》,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16冊,第540頁。
[33]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九十一“真宗天禧二年夏四月戊子”,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15冊,第437頁。
[34]李森:《青州龍興寺院落考證》,載《中國文化研究》2008年冬之卷,第128~132頁。
[35]宋梁克家撰:《淳熙三山志》卷三十三“寺觀類一”,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84冊,第490頁。
[36]宋梁克家撰:《淳熙三山志》卷三十四“寺觀類二”,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84冊,第502~506頁。
[37]宋梁克家撰:《淳熙三山志》卷三十五“寺觀類三”,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84冊,第517~521頁。
[38]宋梁克家撰:《淳熙三山志》卷三十七“寺觀類五”,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84冊,第556~559頁。
[39]宋梁克家撰:《淳熙三山志》卷三十三“寺觀類一”,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84冊,第490~501頁。
[40]載清畢沅、阮元同撰《山左金石志》卷十五,清嘉慶二年(1797)儀征阮氏小瑯嬛仙館刊本,第5~6頁,。
[41]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十,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14冊,第422~436頁。
(責任編校:張京華)
K878.6
A
1673-2219(2010)05-0017-07
2009-10-30
萬里(1951-),男,遼寧復縣(今瓦房店市)人,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主要從事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民俗宗教文化、湖湘文化等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