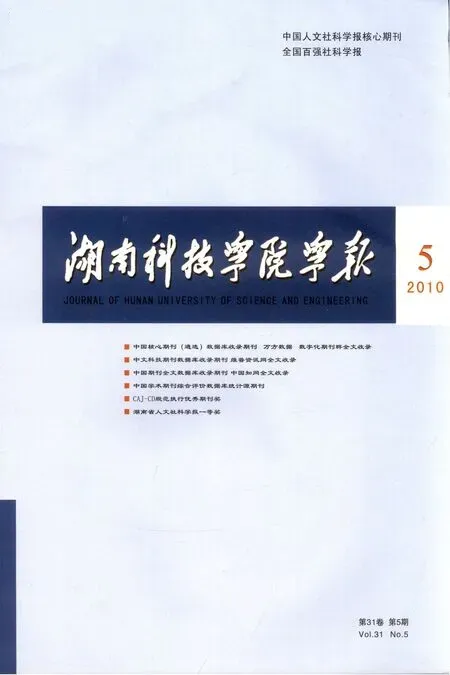新時期文學的“去政治化”趨向與新世紀文學的“再政治化”
鄭國友
(湖南第一師范學院 文史系,湖南 長沙 430205)
新時期文學的“去政治化”趨向與新世紀文學的“再政治化”
鄭國友
(湖南第一師范學院 文史系,湖南 長沙 430205)
20世紀特殊的時代情勢迫使中國文學介入政治場域。文學的政治運作與政治的文學實踐使該時段的中國文學承受了過多的非文學使命。新時期文學“去政治化”的文學想象是對過去文學“政治化”的一種反叛。然而,二十余年來的試圖使文學在遠離或逃避政治這一帶有強大社會能量的話語、制度、作用力的文學努力,同樣是使文學步入歧途和困境。新世紀的文學面臨著一個“再政治化”的問題。
新時期;新世紀;文學;“去政治化”;“再政治化”
一 政治化與文學異化
20世紀特殊的時代情勢迫使中國文學介入政治場域,從而使該時段的文學在整體上被烙上了鮮明的政治色彩。文學群體和作家個體均從各自的政治立場出發闡發自己的文學觀念,發起文學運動,參與文學論爭。梁啟超早在世紀初便大聲呼吁:“今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1]P211這在理論上將小說視作是革新政治的強有力的工具。魯迅也認為,“現在是多么迫切的時候,作者的任務,是在對于有害的事物,立即給予反響或抗爭。”[2]P1魯迅在文學實踐中正 是強調文學的“匕首”和“投槍”的作用。我們甚至可以說,一部20世紀中國文學史就是一部文學的政治演進史。
文學革命時期,以魯迅為代表的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視閾中始終彌漫著對腐朽政治的強烈憎惡和對“合理”政治建構的強烈欲求。革命文學時代,不單是文學社團帶有“亞政治文化”的形態特征[3],文學論爭更是充滿“火藥、硝煙”味。李健吾在1930年代就說過:“時代和政治不容我們具有藝術家的公平。”[4]文學的政治化傳統,使我們看到了中國現代作家那一腔赤血參與中國革命復雜建構的熱情。
然而,建國后27年文學的政治化演進卻過多地順應于政治層面的導引與規范而缺乏文學層面的探索與開拓。如果說,五四時期的中國作家是出于以正義感為核心的政治倫理驅使其以文學的方式參與政治建構,那么,在“十七年”和文革時期的中國作家則過多地負載著政黨和國家權力話語和制度規范層面的脅迫,其創作自主性受到了來自政治話語方面的嚴重擠迫。這一時期,文學的政治運作與政治的文學實踐使該時段的中國文學承受了過多的非文學使命。文學的發展進程,自動地或不由自主地被納入“光明的中國之命運和黑暗的中國之命運”的政治選擇之中。[5]P5文學在整體上呈現出異化的頹敗景象。“文藝從屬政治”、“文藝為政治服務”并且“當然是服從那個實的(政權機構——政黨),虛的(政治思想、政治態度、政治觀點)怎么服從呢?”[6]P348文學成為歌功頌德的“流行音樂”。作家可以無視三年困難時期的現實而喝著“荔枝蜜”、唱著“茶花賦”。在領導層“三個結合”的創作指導下,假、大、空的人物形象塑造成為當時作家的創作追求。50到70年代發生在中國文學中大規模的批判運動,將中國文學的異化現象推向高潮。當時文學反應的現實,其實是一種“偽現實”,與現實嚴重脫節的一種現實。現代中國文學經過近60年的發展,其結果是只剩下八個“樣板戲”。而大批曾經為中國文學創造了巨大精神財富和思想資源的作家因眾所周知的原因或不得不放棄寫作,或面臨被批斗、被改造、被下放甚至被摧殘致死的命運。以至我們今天重提這么一個話題,心情依然是十分沉重。這使我們不由得要問這么幾個問題:中國文學為什么會走向這么一個“悲慘世界”?
在20世紀,我們與西方一樣,都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而為什么西方文學能將戰爭的苦難經歷轉變為其思想資源并創造出文學的輝煌,我們卻只能寫些“墻頭詩”、“槍桿詩”,唱些“新民歌”?這是作家的失職還是其它一些什么原因呢?當然,面對這些詰問并試圖回答這些看似簡單的問題在今天仍然是十分困難的,但有一點卻是應該引起我們重視并深思的,那就是在文學的政治化演進過程中,中國作家逐步被政治所“規范”,從而喪失了對自己作家身份進行確認的自覺和與現實進行心靈對話的姿態和情緒。文學呈現異化,關鍵就在于作家喪失了自由和對自由的追求。如薩特就認為文學的本質是自由,寫作的目的就是呼喚自由。文學的政治化并最終導致文學的異化,其教訓至今仍應該引起我們深思并值得認真進行總結。
二 “去政治化”與“回到文學本身”
20世紀中國文學在20世紀80年代前的過度政治化及其導致的文學異化處境使中國文學一步入新時期便產生對政治的“反彈”和“撤退”。在“反思”極左政治給中國人的心靈造成的“傷痕”,并進而提升到文化“尋根”的思想高度之后,便發生了歷史性的轉換。這種轉換的顯目之處在于中國作家在新的時空結構中煥發出新的藝術想象,即對于純文學的理論倡導和藝術實踐,并開辟出了如“尋根文學”、“現代派”、 “先鋒派”等廣闊的藝術空間。這種理論倡導與藝術實踐根由在于人們意識到20世紀中國文學是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文化語境中展開的,20世紀特殊的時代特點和特殊的歷史任務,使這個時代的文學在整體上呈現出不利于純文學發展的態勢,文學在大多數時段始終未能避開政治浪潮的裹挾。于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學在大量去除政治強加的非文學使命后,獲得了較大的自主自律性,這就為文學在新時期的轉換提供了可能性。
新時期文學的轉型是在時代變革、社會轉型和純文學呼聲高漲的背景之下進行的。這種轉型,自然有其歷史淵源與現實依據。回顧歷史,在20世紀30年代,無論是“左聯”、“新月”,還是“海派”、“京派”,都是從各自的政治立場及其對政治的預設出發,以文學的方式參與當時的政治角逐。五六十年代特別是文革十年,文學被欽定為“為政治服務”,“文學從屬于政治” 的工具性處境大大玷污了文學的純潔性。文學參與政治,政治干涉文學,中國作家在此過程中受到了嚴重的傷害,在其意識與潛意識中均有著對過去文學參與政治建構歷史行為的摒棄與排斥。
面向現實,八九十年代的社會轉型,市場大潮洶涌,作家在“沖浪”中重新對自己的角色進行定位。如王朔自稱是碼字兒的,馬原反復強調自己只是在講故事。新時期的作家心態趨于平緩,過去革命時代知識者“政治焦慮”心境被取而代之的是重新進行了角色定位了的知識者的“政治疲倦”。表現在文學實踐中,便是新時期作家的“去政治化”的文學努力。首當其沖且口號宏亮、應者云集的便是八十年代的文學吁求:對于“純文學”的倡導。值得肯定的是,“純文學”的吁求和“去政治化”的文學努力,確實有著非凡的時代意義和文學價值,確實開拓了新的想象空間和話語空間。然而,“問題在于,究竟什么是‘文學本身’?有沒有一種在歷史運動中與社會、政治、經濟、法律、道德、倫理、宗教等等互動著的,卻又被宣稱為與它們毫無關系的純粹的‘文學本身’?試想,把一切都剝離掉了,還能剩下什么?本能?食與性?”[7]回首20世紀80年代特別是90年代文學的發展歷程,面對文學的現實,文學的“去政治化”與“政治化”的效果,同樣存在漏洞與缺失,同樣存在對廣泛豐富的社會生活進行抑制與遮蔽的令人擔憂的征象。
從作品題材、題旨上看,文學的“去政治化”抑制與遮蔽了政治與政治文化在當代文學中的投影。以近年來的文學觀之,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文學形態豐富,題材多樣,但時代質素卻被抽空。新寫實小說從描寫重大題材的“高度”降下來,以“零度情感”去書寫生活的“原生態”。新生代小說、女性寫作刻意回避大眾的現實生活,潛入到對“私人生活”的個人化書寫和“下半身寫作”的密集圖景當中。許多評論家對文學“不寫內心,專寫內分泌”、“‘吶喊’的聲音稀薄而‘欲望的尖叫’卻被高分貝放大”的現象深表憂思。[8][9]再往下延,所謂“70年代寫作”、“80后”更擺脫了“宏大”的社會政治書寫,而進入對“草樣年華”、“像狗尾巴一樣晃悠的青春”的成長煩惱和新新人類“獨特”生活場景的描摹當中。即便是一度以極大的熱情介入社會政治的張承志、張煒、韓少功、王安憶等人也把筆觸轉而伸向民間、種族、部落等等。似乎相當一部分的作家普遍降低了對現實社會的政治熱情,而表現出一種“政治冷淡癥”。當下許多現實生活的矛盾,作家不是在回避,就是在撫摸。即使是政治內涵較大、以“反腐”為主題的文學作品也難以觸摸到創作者嚴肅的政治使命和嚴正的社會責任感。怪不得批評家喟嘆,這些作家和作品是在“誨淫誨盜”。
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成為20世紀中國文學歷程的一塊鮮明的“界碑”,前近六十年的政治化演進在此被“去政治化”和“純文學”“撞了一下腰”,而發生了歷史性的轉換。急變的革命時代,現代中國作家自覺將文學納入政治的軌道,“以筆為旗”主動參與中國革命的建構,傳統在新時期漸被降下帷幕。然而,“回到本身”的文學同樣無法解決“文學本身”的問題。“什么是文學本身?”、“何謂文學本身?”的問題同樣令文界、學界寢食難安、頗費思量。
20世紀中國文學近60年的政治化演進和20多年的“去政治化”趨向的經驗與教訓是本文引出“新世紀文學‘再政治化’問題”的兩個“平臺”或“坐標”,本文試圖對此作一最初的嘗試,以引起學界探討。
三 新世紀文學的“再政治化”問題
美國當代著名的學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遜斷言,政治視角構成“一切閱讀和闡釋的絕對視域。”[10]P8而同時代的牛津大學教授、英國首屈一指的理論家特里·伊格爾頓也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以獨特的“文本——歷史——政治——文化和理論——創作”的批評方法,將文學的文本、歷史的敘述、審美的再現、政治的闡發相互闡釋、交相輝映,從而開創出一種批評的“霸權。”[11]P20雖然他們均是從批評的角度來討論文學的問題,但引出的話題是,新世紀的中國文學如何以新的姿態進入廣闊豐富的現實社會生活的問題。在綜觀20世紀中國文學“政治化”與“去政治化”的演進和演變的軌跡后,我們將這一問題再具體、再細分,那就是新世紀中國文學的如何“再政治化”問題,這關系到中國文學在新世紀如何進行自主性重建這一重大課題。
討論這個問題,我們是基于這樣一種認識,即政治作為意識形態,其包容量極大,同時又具有極大的社會能量,它可以輻射至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政治文化是民族或國家長期積淀下來的政治價值觀念、政治信仰、政治情感和政治心理等,它對人們的價值觀、情感、心理、倫理、道德、認知等均會產生巨大的作用力。將政治和政治文化納入文學的場域,在表現“人”的文學中顯示其巨大的投影,應是作家的自覺。試圖消減政治和政治文化外在或潛在的作用力,將文學固定在“文學本身”的場域來構建文學的烏托邦,在短期內對文學發展的負面影響也許會不甚明顯,但長此以往,必然會使文學“短足”。
同時,也是基于這樣一種現實,即在處理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問題上,中國作家形成了一個可怕的心理和思維定勢:將政治等同于黨派和國家政治,認為政治就是斗爭,就是伐異,心靈深處感受到的仍然是從政治立場出發介入文學論爭以及文革時期政治對文學的粗暴干涉所帶來的苦痛記憶,由此而產生“政治恐懼癥”和“政治疲憊感”。誠然,文學介入政治以及政治干涉文學的慘痛教訓我們不能忘卻并應該認真總結。但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的文學態度卻是有害的,我們不能在把洗澡水潑掉的同時,也把嬰兒扔掉了。很久一段時期以來,我們看不到一針見血、深沉博大的作品,缺乏觸動思維,牽引靈魂的佳作。試問,遠離現實,逃避政治的文學難道不就是這個樣子嗎?
新世紀文學應該如何“再政治化”?首先仍然是作家身份確認與身份自覺的問題。20余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體制、文化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特別是政治民主化進程加快了步伐,取得了突破。在全球化語境中,人類性的力量和眼光是考察“地球村”事物的共通性標尺。而文學是最宜于表現人性和人類性的文化學科。文學生長環境的適宜變遷為文學提供了肥沃的生存土壤。這就要求作家進行自覺的自我調整和身份確認。表現在處理政治和政治文化如何進入文學這一問題上,作家應擺正自己的位置,以文學家而不是政治家的身份出場。而且文學家在把握政治問題是,“必須是通過對人的靈魂審視而達到對人的精神關照,他更多地側重于政治與人的內在關系的角度。”[7]其次,我們認為,新世紀文學將政治和政治文化引入文學,在其中必然要有一個審美轉換和平衡的問題。轉換和平衡的過程,就是從政治話語向文化政治的轉換過程。作家要有面向現實并穿越現實特別是現實政治的勇氣,貫注著充滿著人類學眼光的憂患意識并高揚批判精神。他們精神視閾中的政治維度是多向并互闡著的。他們對政治的感受應該是獨特的、多向的。其心靈飛翔在廣闊的政治域地里,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心理、政治文化和政治美學均是其展開靈動翅膀的廣袤之地。他們以文學的方式將現實政治與政治文化在文學處整合。特別是在現實遇挫時,作為“靈魂工程師”的作家,其憂患意識和批判精神會沉重而富有熱力地被喚起、喚醒,從而擔負起社會和人類靈魂“守夜人”的歷史責任。只有在以上兩點的基礎上,我們才有資格有依托來談論新世紀文學場域自主性重建問題。
政治對文學來說是把“雙刃劍”。中國文學有著悠久的政治化傳統,從孔子的“興、觀、群、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論語·陽貨》),至白居易的“補察時政”、“泄導人情”,再至梁啟超“今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1]中國文學始終對政治或現實充滿了熱情關懷和體認。然而,由于在處理文學與政治關系時的簡單化、粗暴化,文學和作家均受到了傷害。中國文人的“非正常死亡”至今仍是“血的教訓”。
現代中國的文學經過近一個世紀的發展,在處理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問題上,應該說我們既儲備和積淀了寶貴的經驗,也存留了永遠值得銘記的教訓。從經驗的層面論,中國現代作家以文學的方式參與政治建構所積淀起來的直面現實的文學精神是滋養中國文學的養料。從教訓的角度看,“前車之鑒”將永遠是我們文學前進的“紅燈”,從而避免“重蹈覆轍”。因此,我們在處理這一問題時將會是更加聰慧與靈動的。在世紀之交,我們似乎聆聽到一種新異的文學足音:中國文學關注社會現實、關懷現實生存的話題的重新升溫。1996年,以劉醒龍和被稱為河北“三駕馬車”的何申、談歌、關仁山等作家為代表,創作出的一批反映當代改革生活和社會現實的小說,給多年沉溺于文本探索和歷史探尋的文壇帶來了一次文學轟動。近幾年來,“現實主義沖擊波”、“現實主義回歸”的文學沖動一直在中國文壇活躍著。而以周梅森、張平、王躍文、陸天明為代表的新一代官場小說作家,其作品在貼近現實中展現政治力量的較量,其觸及問題之多,社會涵蓋面之廣,以及對人們思維與情感觸動之大更是近年來少見。這些現象,是不是預示著中國文學在總結政治化演進與演變的經驗與教訓之后在新世紀的一種更高層面的智性接續?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我們可以這樣設想,即在現代中國作家所累積起來的直面現實的文學精神的燭照下;在新時期“純文學”試驗所探索出來的藝術創造經驗和資源的充分利用之下;以及逐步完善起來的文學生產機制制導之下,新世紀中國文學正是曙光泛起的時候。
新世紀文學處在一個新時代語境之中。在新的時代語境中,文學與政治結緣的方式是新異的,同時也是具有探索性的。中國文學在“去政治化”之后進行“再政治化”,應該是文學在“政治化”和“去政治化”的兩極搖擺之后的一種轉換和平衡。文學要在政治新的域地里翱翔,作家必須培養新的政治文化思維,具備新的政治心理想象結構。在全球化時代,開放的時代與多元的文學格局使作家的審美感官自主自在地“完全裸露”。在少有“禁區”的文學園地里,政治這一具有極大社會能量的話語、制度、作用力和政治文化這一文學與作家生存的闊大的文化背景和文學生產的素材應該也完全有必要進入作家的審美視野。當作家以新的審美姿態來表現或再現政治與政治文化在人們心理和行為上投射的斑駁圖景時,豁亮的政治通道必將給中國文學帶來新的輝煌。
[1]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A].郭紹虞.中國歷代文論選(第四冊)[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魯迅.且介亭雜文·序言[A].且介亭雜文[Z].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
[3]朱曉進.論三十年代文學群體的“亞政治文化”特征[J].求是學刊,2000,(3).
[4]轉引自洪子誠.不要輕言“終結”[J].鄭州大學學報,2004,(3).
[5]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6]周揚.思想解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A].周揚.周揚文集(第5卷)[C].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
[7]雷達.當今文學審美趨向辨析[N].光明日報,2004-06-30.
[8]鄭國友.從《吶喊》到《有了快感你就喊》[J].作品與爭鳴,2004,(4).
[9]鄭國友.當前文學的迷失與救贖[J].作品與爭鳴,2004,(9).
[10][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遜.政治無意識[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11][英]特里·伊格爾頓.歷史中的政治、哲學、愛欲[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責任編校:王晚霞)
Depoliticization Trendency of the New-era Literature and Re-politicization Issue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New Century
ZHENG Guo-you
(School of Chinese ,Hunan first normal college,Changsha,410205,China)
The special situation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get Chinese literature involved into political position. The political operation of literature and the literary practice of politics make Chinese literature bear too many non-literary m issions. Literary imagination of de-politicization of the new-era literature is a rebellion to the politicization of literature of the past. However ,more than twenty years’ efforts to make literature far away from politics ,which embraces social and powerful words ,systems and functions, equally make literature into crossroads and dilemmas.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new century must face the issue of re-politicization.
The new-era;The new century;Literature;Depoliticization; Re-politicization
I206
A
1673-2219(2010)05-0042-04
2010-01-20
鄭國友(1974-),男,湖南瀏陽人,湖南第一師范學院文史系講師,文學碩士,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