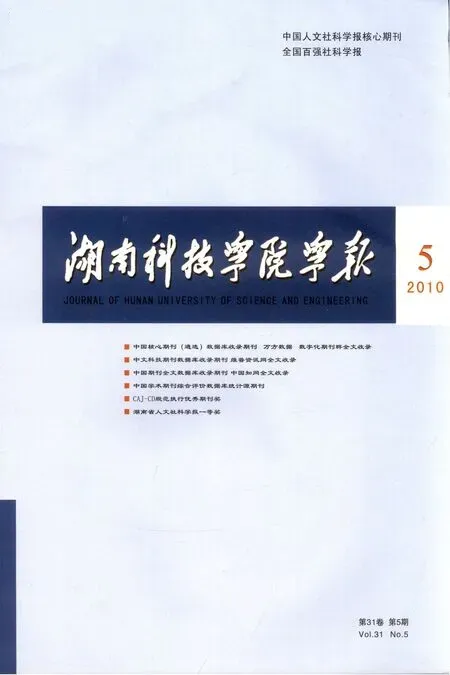人文關懷下的底層敘事
——讀劉翼平長篇報告文學《腳手架》
谷顯明
(湖南科技學院 中文系,湖南 永州 425100)
人文關懷下的底層敘事
——讀劉翼平長篇報告文學《腳手架》
谷顯明
(湖南科技學院 中文系,湖南 永州 425100)
進入新世紀以來,底層書寫越來越成為關注的焦點,其中農民工題材寫作毫無疑問成為底層敘事的一大重要分支。劉翼平的《腳手架》就是以紀實性報告文學的形式,講述了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一批湖南零陵人背井離鄉上廣西打工討生活的人生經歷,生動地描繪出湘南農村如詩如畫美景背后的生存艱辛,形象地再現了瀟湘大地一代農民進城之路掙扎裂變的生命圖景,堪稱為一部人文關懷下的底層敘事作品,隱含著作家對城市化語境下農民工命運的關注與思考。
民工題材;《腳手架》;人文關懷;底層敘事
一
“底層”一詞來源于葛西蘭,在曹雷雨等譯的《獄中札記》中,此詞被翻譯成“下層階級”、“下層集團”。[1]許多專家認為,對底層的關注在社會與文學發展過程中始終自然地存在。如魯迅先生對當時處于被壓迫、被剝削地位的國民命運的關注,對阿Q等發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感嘆;鄭振鐸先生倡導關注“被損害者與被侮辱者”,可以說是中國現代文學中關于“底層書寫”的最早表達。然而,進入90年代中 期以來,“大多數作家并沒有把自己的寫作介入到這些思考和激動當中,反而是陷入到‘純文學’這樣一個固定的觀念里,越來越拒絕了解社會,越來越拒絕和社會以文學的方式進行互動,更不必說以文學的方式(我愿意在這里再強調一下,一定是以文學的方式)參與當前的社會變革。”[2]在這種情形下,文學界便展開了對“純文學”的批判性反思,出現了諸如“‘底層’如何文學?”、“當代文學如何表述底層?”、“文學如何面對當下底層現實生活”等一系列關于底層研究的話題。“述說底層”也成了作家們通過文學表達各自內心焦慮和人文關懷的一種獨特方式。進入新世紀以來,便在文學領域頻頻出現一大批底層民工題材寫作,并逐漸成為當代中國底層敘事的一大重要領域。如尤鳳偉的《泥鰍》,荊永鳴的《北京候鳥》、孫惠芬的《民工》、劉書宏的《盲流》、賈平凹的《高興》、鄧建華的《鄉村候鳥》等作品,將書寫視角聚焦城鄉對立格局下底層民工群體的生存苦難和靈魂病痛,表現出堅定的底層關注的傾向,傳達出悲憫的人道主義情懷。另外,像安子、林堅、張偉明、周崇賢、盛可以等作為深圳百萬打工者中涌現出來的打工作家,基于自己的打工經歷和人生體驗,透過“漂泊者”的藝術視角“在生存中寫作”,創作了《青春驛站》、《別人的城市》、《下一站》、《隱形沼澤》、《北妹》等作品,展現出進城鄉下人游蕩在城市邊緣留下的創傷與疼痛,表達了對農民工的生存狀況和悲劇命運的深刻思考。而作為永州本土作家,劉翼平先生則同樣為本土農民工的生存狀況而揪心,為他們在異鄉的奮斗經歷而感動。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創作出紀實性長篇報告文學《腳手架》。這部作品通過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一批湖南零陵人背井離鄉上廣西打工討生活的人生故事,生動地描繪出湘南農村如詩如畫美景背后農民生存的艱辛,形象地再現了瀟湘大地一代農民進城之路掙扎裂變的生命圖景,堪稱為一部人性關懷下的底層敘事作品。
二
千百年來,在傳統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的村落社會,人們聚族而居,安土重遷,常年以種地為生,正如錢穆先生所說:“農耕民族與其耕地相連系,膠著而不能移,生于斯,長于斯,老于斯。”[3]無論老一代農民,還是新一代農民,都對土地有一種難以割舍之愛和企圖擁有更多土地的愿望。因此,“賦予土地一種情感的和神秘的價值是全世界的農民所特有的態度”[4]。處于天地間的生民,對于天地化育尤其是對于母性大地的感激,直至當代,仍作為鄉土文學的詩意源泉。正如趙圓所說:“在自覺的意識形態化,和不自覺的知識、理論背景之外,有人類對自己‘農民的過去’,現代人對自己農民的父、祖輩,知識者對于民族歷史所賴以延續、民族生命賴以維系的‘偉大的農民’那份感情。在這種懷念、眷戀中,農民總是與大地、與鄉村廣袤的土地一體的。”[5]綜觀現當代鄉土文學,知識者鐘愛他們發現并大大地豐富了、詩意化了的“人與土地”這一重關系,這也是人與自然物的關系中被人描繪最充分的一種關系。李廣田在《地之子·自序》中寫道:“我是生自土中,來自田間的,這大地,我的母親,我對她有著作為人子的深情”,這正表達了人對土地的眷戀和熱愛。中國知識分子,往往自覺其有承繼自“土地”的精神血脈,“大地之歌”更是成為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習慣性吟唱。劉翼平也對故土有著一份深沉的愛,有著一份摯熱的情,他筆下的都龐余脈的“柴君山”、大慶坪里的“石腳盆”、湘桂交界的“黃花嶺”、湖廣兩省的“楚粵亭”、湘南邊陲的“觀音山”,都充滿著詩情畫意:
站在柴君山巔,俯瞰這向北鋪展的南國田園,農田、水庫、丘陵、村莊遍布其間,河流、道路縱橫交織,儼然一幅美麗素雅的織錦圖、田園畫。畫圖中,蜿蜒的湘江帶著秦始皇在靈渠的文治武功自黃花嶺的邊沿由西向東而去,與從九嶷山帶著舜帝傳傳自南向北傳來的瀟水在傳傳傳傳,然后向北傳騰,入洞庭、注長江、下東海。因為這兩條河,“錦繡瀟湘”的美譽便由此而生,“瀟湘夜雨”便成了湖湘八景的第一景。(《柴君山上打柴難》)
然而,“圖畫是美的,可作畫、織畫的人卻是勤勞艱辛的,仿佛造物主故意要磨練這一方百姓,只將一小片土地交與他們耕作生息。”柴君山下的這塊土地,經歷過中國農村的屢屢陣痛,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用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這塊有限的土地上,忍耐、克服、戰勝著這塊土地帶來的陣痛。但“在這塊土地上,人們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卻是跳蚤。”為了生存,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只能“向山上進軍,向水里要糧”,展開一場場爭山、爭水、爭樹、爭竹的生存大戰。“山下跟山上打,楊姓跟李姓斗,水庫左邊渠跟右邊渠爭”,“砍柴的柴刀、看水的鋤頭,這些平時最基本的生產工具變成了隨身武器,松樹炮、棕櫚炮、滾珠炮是陣地戰的殺手锏”。更有甚者“為爭樹爭竹,山下山上兩個村還要喝血酒、下戰書”,村約還規定“誰要是為了水、為了山被打死,村里便劃一片山、劃一塊田,將其老人養到老,小孩撫養成年”。由此可見,“這塊土地,就像一曲憂傷的田園牧歌,盡管不失千百年來農耕的溫馨,卻無法改變貧窮的基調。”
又如大慶坪鄉的“石腳盆”,這里自然條件更為艱苦,其水荒之苦更是讓人驚嘆:“一線比童子尿還細的泉流從石縫中流出。先民們在石底上鑿出一個腳盆大小的裝水盆,裝著這生命之水,每天由村里年長的輪流發水。一線線、一滴滴,石腳盆400多人就靠這腳盆水活了一代又一代。”而海拔最高的毛坪里村,因缺水,更是一個月難洗3次澡。面對“出門就爬坡,到處有陰河,水在地下淌,半月干死禾”的艱苦自然環境,正如閻連科《日光流年》中對抗死亡的三姓村人一樣,這里的人們前仆后繼踏遍山沖嶺坳,開鑿隧洞,引出千年陰河水,修筑野牛巖底下水引灌工程和貓兒巖中型水庫,從而結束了大慶坪“干旱死角鄉”的歷史。但這兩大壯舉的背后掩藏了慘烈的代價:黨支部書記唐錦光被巨石奪取年僅37歲的生命,“鐵姑娘隊”的姑娘們扛著大旗,揮著淚水……。由此可見,在湘南美景背后,鄉民過著“日光流年”一樣的苦難生活。進入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農村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從根本上動搖了傳統的土地觀念的根基。同時,改革開放的深化把農村卷入整個市場經濟體系,落后的生產方式與保守的經營理念使農村與城鎮的差距越來越大。“面對日益開放,充滿誘惑的外部世界,這一代人明白,要想致富,村莊是不可能提供資源和機會了,村莊已經喪失了經濟上的重要意義,不再是一個終身依托的錨地。”[6]于是,新一代農民開始掙扎著,嘗試沖出黃土地,到更廣闊的外面世界去尋求一種新的生活。這也正是作者在《上篇》中所要表達的上世紀80年代以來零陵山民掙扎出走的原因。
三
進入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新一代農民在這誘惑中躁動著,開始紛紛卷起鋪蓋,丟開祖祖輩輩賴以生存的土地,不約而同地邁著堅實的步伐從不同的角落、不同的方向走出貧困的鄉村,走出封閉的山區,涌入對于他們來說陌生而又充滿希望的現代化大城市,呈現出“農村包圍城市”的壯麗景象。在這種大的時代背景下,位于湘南邊陲的水口山、大慶坪、石巖頭及其相鄰鎮的農戶,因為人多田少,也紛紛扮演著盲流和打工仔的角色外出務工。“他們進桂林、下柳州、入南寧,填補著廣西農民外出務工留下的空缺,從事著以建筑和廢品收購為主的行業。”然而,對于大多數進城打工者來說,通往城市的道路“絕不是鋪滿鮮花的康莊大道,而是一條沾滿了污穢和血的崎嶇小路”。[7]像那些從瀟湘土地上走出的這些“泥腿子”、“破爛王”,誠惶誠恐地在人生的河流里一步一步艱難地行走著。作品“立足”篇中牛背嶺下的楊祿福和妻子背鄉離井下南寧,“在天橋下睡了兩個晚上,這沿街的門面已被他問個遍,就是沒能找份事兒”。后來,在一家酒店他做上了鍋爐工兼宰殺工,妻子做上了洗碗洗菜的服務員,干著最臟最累的活,“冬天,當他從暖暖的鍋爐旁出來把手伸進那冰冷的水里拔毛時,他深深體會到了什么是冰與火、什么是冷與熱。妻子與他一樣,一雙手因為經常泡在冷水里,手背腫得像包子,手指上長滿了凍瘡。”可是,老板卻欠著他們本來就少得可憐的工資不發。到第二年臘月,他還被老板娘誣陷,不但工資分文沒有,而且被老板帶著一幫人趕出酒店。妻子無奈,只能到大街上去撿破爛換點錢養家糊口。同樣,唐玉青15歲到桂林開始小鐵匠的“馬釘生涯”,在場地窄、爐子多,熱得不得了的工棚里,光著膀子打著赤手腳干,手腳上被鐵花燙出一個個疤印;而蔣松兆14歲就跟著村里人上桂林,在建筑工地打小工,幼少的手被紅磚搓出血,頭發被泥灰漿得挺直,白天在工地上頂風冒日,晚上在工棚里蚊蟲叮咬,變成一個活脫脫的“流浪三毛”,等等。作者通過一個個進城謀生者酸甜苦辣的生活故事,勾勒出這些生活在社會底層人群的生存狀態和城市體驗。透過這些故事文本,我們看到的是作者強烈親近底層勞動者的敘事立場,而且他所充當的角色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旁觀者,而是置身其間的切身體驗者。可見,作者通過底層敘事來關注民生苦難,用自己的真誠來寫出時代的真實。
而相對其他作家而言,劉翼平不僅僅在于再現上世紀80年代以來零陵山民在廣西八桂大地的生存苦難,而更在于“將這一個群體、一個個人物立起來,以此來反映中國農民工的形象和蛻變歷程,反映中國改革發展的富強之路”。作品以腳手架人個人艱苦奮斗為典型,表現了改革開放中的創業歷程:背井離鄉下南寧的楊祿福成立了祿福鋼管出租有限公司,資產超過千萬;苦后方為人上人的唐玉清成立了湘南建材租賃公司,如今他的鋼管已有2000多噸;打拼場上不言棄的蔣松兆成立了兆鑫建筑材料租賃公司,擠進了南寧建筑外架大市場;從一文不名到富翁的唐順福注冊了福灶建筑裝修公司,在桂林小有名氣;為搶市場不叫累的楊隆云成立了玉隆勞務分包公司,并被評為南寧市重合同守信用優秀單位,等等。可見,作品所展現的農民工形象是積極向上的、是充滿理想的,是富于激情的。他們為中國城市現代化建設做出了不可替代、不可磨滅的貢獻。正如作者在《腳手架·后記》所贊譽的,“他們是中國城市發展的腳手架,是共和國的腳手架”。
在《下篇》中,作者還述說了進城富起來的民工所表現出的種種生活方式,出現安居熱、購車熱、落戶熱、商會熱、轉行熱、文化熱、回報熱、出國熱等,以他者的視角抒寫出對民工兄弟的新市民生活現狀,并對他們的未來出路進行了預設。有專家提出,在大眾敘事的語境中,報告文學應該是農民生活的代言人,也應該是農民情感的撫慰者。我們在宣揚進城創造成功者的同時,更應對那些依然痛苦掙扎在城市邊緣的底層民工給予更多的關注和關懷。因此,作為創作者只有站在尊重農民、體恤農民的立場,去了解農民的真實生存境況和情感訴求,懷著悲天憫人的現實主義情懷進行創作,才能為改革開放大背景下的農民工抒寫出真正的心靈史。
(劉翼平著,《腳手架》,中國言實出版社,2008年)
[1]薛毅,劉旭.有關底層的問答[J].天涯,2005,(1):28-34.
[2]李陀,漫說“純文學”——李陀訪談錄[J].上海文學,2001, (3):7.
[3]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弁言[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4][法]H·孟德拉斯.農民的終結[M].李培林,譯.北京:中國科學出版社,2005.
[5]趙圓.地之子——鄉村小說與農民文化[M].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3.
[6]吳毅.記述村莊的政治[J].讀書.2003,(3):108.
[7]丁帆.“城市異鄉者”的夢想與現實[J].文學評論,2005,(4): 34.
(責任編校:王晚霞)
book=222,ebook=281
I207
A
1673-2219(2010)05-0222-03
2010-01-11
本文為湖南省教育廳資助項目“現代化背景下的‘鄉下人進城’文學研究“(項目編號09C450)、湖南科技學院青年課題“轉型期以來‘鄉下人進城’文學研究”(項目編號08XKYTB001)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谷顯明(1976-),男,湖南零陵人,文學碩士,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