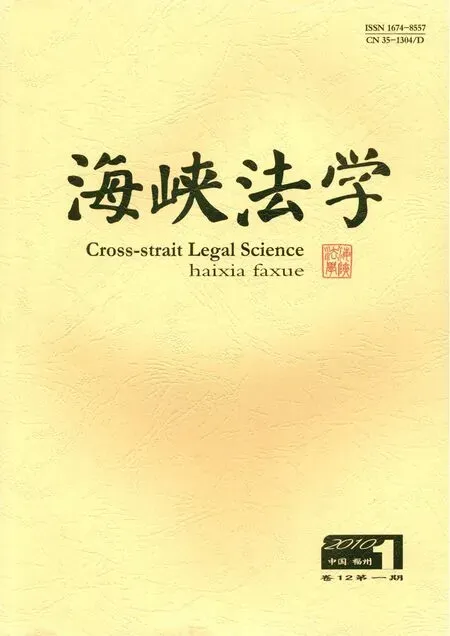試論作為義務的認識錯誤
吳振興,張 偉
(1.2.武漢大學法學院,湖北武漢 430072)
試論作為義務的認識錯誤
吳振興1,張 偉2
(1.2.武漢大學法學院,湖北武漢 430072)
不作為犯以行為人違反作為義務為構成犯罪的必備條件。而作為義務的地位及其與故意的關系則直接關系到不作為犯中行為人主觀方面的認識內容及其法律評價。而行為人對作為義務發生認識錯誤時,如何正確評價行為人的主觀方面,不僅關乎到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成立問題,同時也影響到行為人刑事責任的輕重。
不作為犯;作為義務;認識錯誤
根據危害行為的方式的不同,犯罪可分為作為犯與不作為犯。所謂不作為犯,即以不作為為其構成要件之規定形式,并以不作為為其實現犯罪之具體的行為者屬之。[1]而按照以不作為形式實施的犯罪的法定構成為標準,不作為犯又分為純正的不作為犯與不純正的不作為犯。[2]而不論是純正的不作為犯抑或是不純正的不作為犯,都要求以行為人違反作為義務為其構成要件,在這一點上,他們具有同樣的構造要求。正如日本學者日高義博教授所言:“法定作為義務是構成不真正不作為犯的核心要素,它從客觀方面及主觀方面兩個角度來劃定對不作為犯責任譴責的界限。如不存在法定作為義務,不真正不作為犯也就不能成立,如果不作為人對法定作為義務沒有認識,認定他構成故意犯罪就很困難。”[3]雖然日本學者日高義博教授是針對不真正不作為犯來闡述的,但是如前所述,在對作為義務的要求上,純正的作為犯與不純正不作為犯是共同的,即首先存在法定的作為義務;其次,在不作為犯罪中,要求行為人認識到該作為義務,至少具有認識的可能性。當行為人因為主客觀方面的原因對法定的作為義務發生認識錯誤時,該錯誤是否能阻卻犯罪故意的成立,阻卻故意犯罪之后是否有成立過失犯罪的可能性,要解決這些問題首先就應當正確界定作為義務在犯罪論體系中的位置以及故意的認識要素及其地位。
一、作為義務錯誤之定性
有關錯誤的界定,國內外刑法學界眾說紛紜,尚無定論。例如日本學者大谷實所言:“所謂錯誤,一般是指客觀的實在與主觀的認識的不一致,完全不認識實在,作為全面的不一致的‘不知’也是錯誤。”[4]意大利學者杜·帕多瓦尼則認為:“一般說來,可以將錯誤定義為‘對任何事是真實的自然或法律性質的不正確認識或缺乏(應有的)認識’。”[5]在國內,也有部分學者對認識錯誤做過界定,例如有學者認為,刑法上的所謂錯誤,是指行為人主觀上對自己的行為在法律上的意義或者對其所危害社會的事實情況的不正確的理解;[6]有學者則認為,刑法上的認識錯誤,是指行為人在行為時對自己的行為在法律上的意義或者構成事實上的不正確認識。[7]在本文中,筆者將不在錯誤的概念問題上做過多的闡述,需要指出的是,不論學者對錯誤持何種概念,但一般都認為,刑法中的錯誤一般可分為法律錯誤與事實錯誤(或者構成要件的錯誤與禁止的錯誤①)。不作為犯中的作為義務的錯誤無疑也屬于刑法中的錯誤問題,但是有關作為義務的錯誤屬于事實認識錯誤抑或法律認識錯誤,由于不同的學者對作為義務在犯罪論體系中的地位持不同的觀點,而立場的不同直接影響到對法定作為義務及其錯誤的界定,從而影響到故意的存否。
有關作為義務在犯罪論體系中的位置,國外曾經有三種觀點。正如日本學者日高義博教授介紹的,法定作為義務處于犯罪論體系中的哪個階段?……在學說史上,這個問題從因果關系說經違法性說轉移到構成要件相符性說。在今天幾乎沒人支持因果關系說。[8]
(一)因果關系說與作為義務的錯誤
持因果關系說的學者一般將作為義務問題在因果關系中加以研究,主要考慮在不作為犯中行為人的不作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問題,包括不作為的原因性、不作為與作為行為的等值性等問題。[9]臺灣地區的洪福增也持此種觀點。[2]587在國外,大多數學者都從不同的角度力圖說明不作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也產生了諸多的學說,如他行為說,現行行為說,他因利用說,干涉說等。[9]97當然,也有站在自然機械主義的角度否定不作為犯的因果關系的,例如,在早期德國的威爾澤爾(Welzel)就認為不作為不是行為,無中不能生有,因而否認不作為的原因力。前蘇聯刑法學家M·沙戈洛茨基在其著作中說道:“在不作為的情況下,完全不存在因果關系。這里需要解決的問題不在于不作為在什么情況下是所造成的結果的原因,而在于主體在什么情況下要對其不作為承擔責任。”[10]由于主要在探討不作為的行為性、作為與不作為的等價性問題,作為義務的錯誤就被淡化或者直接認為由于該錯誤對行為的因果關系沒有影響,故而不作探論。
(二)違法性說與作為義務的錯誤
持非法性論的學者是在構成要件符合性判斷之后,在對行為的違法性進行分析時研究作為義務的,即從實質的違法論角度探討不作為的違法性。也就是說,如果堅持違法性說,法定作為義務就是決定行為是否違法的關鍵要素。德國的邁爾就持此說,他指出:“符合構成要件的作為,只要根據法規或法秩序不被認為是正當的,就是違法的;與此相對,符合構成要件的不作為,只要不是法規或法秩序所禁止的,就不是違法的。因此,在不真正不作為的領域,原則與例外是倒過來的。”[9]97另外,德國的梅茲格、弗蘭克也贊成此說。在日本,牧野英一持此說,“我認為,作為理論上的見解,作為的因果關系問題與關于違法性的問題,應當區別開來進行考慮,而不作為中的義務違反應當作為違法性的要件。”[9]97由于在違法性中探討作為義務,因此,作為義務的錯誤就被作為違法性的錯誤問題。而違法性的錯誤與故意的關系問題又是中外刑法學界長期爭議的一個話題,在長期的論戰過程中大致形成了以下幾種學說:
1.違法性意識不要說。該說堅持“法的不知有害”的羅馬法格言,認為違法性的意識不是故意的要件,即使存在違法性的錯誤也不阻卻故意,不影響犯罪的成立。在日本,泉二新熊、莊子邦雄、大谷實等學者持此說,但是該說在德國現今已無支持者。[11]很明顯,如果堅持違法性意識不要說,在不作為犯中,行為人對作為義務發生認識錯誤時,不管該錯誤是否能夠避免,都不影響犯罪故意的成立。
2.嚴格故意說。持該說者認為違法性的意識是構成故意的要素,即成立故意不僅僅要求有對構成要件的事實有認識,并且還要有違法性的意識。所以,要認定行為人存在犯罪故意,就必須要求其實施行為時現實的存在違法性的意識。例如佐伯千仞教授就認為:“故意,不僅如上述要求可罰的違法事實的認識,進而實現這樣的事實的自己的行為法上不被允許的意識是必要的,就是所謂違法的認識的問題。”[12]有些學者在此基礎上認為,在過失犯罪中,就不要求違法性的意識,而違法性的意識恰恰就是區分故意與過失的分水嶺。在日本,持此說的學者還有小野清一郎、瀧川幸辰、大塚仁、中山研一、吉川經夫等。若認為作為義務的錯誤是違法性的錯誤,而違法性認識又屬于故意的組成要素,那么在不作為犯中,當行為人對作為義務發生認識錯誤時,犯罪故意就不能成立。
3.自然犯、法定犯區別說。此說立足于社會責任論的立場,認為就自然犯而言,其本身的反社會性、違法性是不言而喻的,任何正常的人在實施構成要件的事實時,就已經認識到其刑事違法性,所以沒有必要將違法性的意識作為成立故意的要素;與此不同的是法定犯或行政犯,由于這類犯罪多是基于政策上的考慮,所以要認定行為人的反社會性,必須還要求行為人認識到該行為的違法性。在日本,牧野英一、木村龜二、八木胖、八木國之持此說。由于堅持兩分說,所以關于作為義務的錯誤就必然會產生兩種不同的結論:在自然犯中,作為義務的錯誤不影響故意的成立;但是在法定犯中,行為人對作為義務發生錯誤時,自然阻卻故意的成立。
4.限制故意說。所謂限制故意說,是指主張作為故意的要件,違法性的現實的意識并不必要,只要有違法性的意識的可能性就足夠了的見解。德國學者Hippel、H.Mayer,日本學者井上正治、板倉宏等持此說。[11]438在筆者看來,該說與嚴格故意說相比,雖不要求有現實的違法性認識,但也只是在違法性認識的程度上有所降低而已,但這并不掩蓋其“成立犯罪故意要求違法性的意識”的面目。所以,堅持限制故意說就會認為,在不作為犯中,當行為人對其作為義務發生認識錯誤時,同樣屬于違法性的錯誤,阻卻犯罪故意的成立。
5.責任說。認為應當嚴格區別違法性的意識(或其可能性)與故意,認為違法性的意識或其可能性是與故意并列的另一個責任要素。違法性意識的錯誤與故意是否成立沒有必然的關聯,當該錯誤不能避免時,阻卻責任的成立;若該錯誤可以避免時,減輕責任。該說認為正當化事由的錯誤是違法性的錯誤。在日本持此說的學者有西原春夫、大谷實等。由于嚴格責任說認為違法性的錯誤并不阻卻犯罪故意的成立,所以在不作為犯中,即使行為人對作為義務發生認識錯誤,也可以成立故意,只是當其錯誤不可避免時,阻卻責任的成立;作為義務的錯誤可以避免時,減輕行為人的責任。
(三)構成要件說與作為義務的錯誤
按照構成要件相符性說,法定作為義務是構成要件的要素,是故意的認識要素的對象。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那格拉、博爾特(Boldt)、加拉斯(Gallas)、恩吉斯(Engisch)、朗格(Lange)、木村龜二等。該觀點認為,法定作為義務的錯誤是構成要件的錯誤(事實錯誤),通常阻卻故意。[3]149有學者將此稱為絕對構成要件的解決,依此區別下面要談到的相對的構成要件相符說。該說認為,應當區分保證人的地位與保證人的義務,前者屬于構成要件的事實,后者則應屬違法性領域;與此相應,在作為義務發生錯誤時,應當分析行為人是對保證人的地位發生了認識錯誤抑或是對作為義務發生錯誤,前者的場合系構成要件事實的錯誤;后者的場合為禁止的錯誤。②
二、觀點檢析
由上可知,作為義務的錯誤與作為義務在犯罪論體系中的地位以及違法性認識與故意的關系具有不可分割的聯系,不同的學說立場必然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但是,針對作為義務的錯誤應當根據哪一種觀點進行定性呢?對此,我們必須進行深入的分析。
首先是因果關系視野中的作為義務的錯誤問題。筆者認為,在因果關系中重點探討不作為的行為性、不作為與作為的等價值性這是正確的,也是必要的。但是這并不能取代對作為義務的認識錯誤進行認真的分析研究。因為如果堅決貫徹因果關系說,作為義務只是成立不作為犯時在因果關系中加以考慮的,但是“對因果關系,也不需要不作為人有認識。因果關系的錯誤和作為犯的情況一樣,不影響故意的存否。……即使不作為人對因果關系、構成要件的等價值性等要素沒有認識,只要認識符合構成要件的事實,就足以能夠形成反對動機。”[3]149但是,在行為人沒有認識到其具有保證人的地位與義務的情況下,讓其承擔故意的責任,這與故意的概念是不相符的,也不符合現代刑法責任主義的要求,是非人道的。正如日高義博教授所言:“如果不作為人對法定作為義務沒有認識,認定他構成故意犯罪就很困難。這是因為,連自己是法定作為義務人(保證人)都沒有認識,認為它形成反對動機也不可能。”[3]149
其次,是違法性說與作為義務的錯誤。由于違法性說認為作為義務的錯誤問題與違法性的意識相關,而違法性的意識又與故意的成立與否緊密相關。所以就不得不考慮作為義務的錯誤與不同學說的契合問題。如果堅持違法性意識不要說,在作為義務錯誤的場合,其處理結果與因果關系說在結論上是一致的,即都不阻卻犯罪故意的成立。如堅持故意說,不論是嚴格故意說還是限制故意說,都認為作為義務的錯誤不阻卻犯罪故意的成立。而故意說中的另一種觀點即自然犯、法定犯區別說則針對不同的犯罪得出不同的結論;由于責任說將犯罪故意的成立與違法性的意識相分離,所以,如果將作為義務的錯誤作為違法性的錯誤,必然也得出該類錯誤不阻卻犯罪故意的成立這樣的結論。但是,很明顯,上述結論在解決實際問題時都會得出不恰當的結論,因為行為人連自己所負有的作為義務都沒有認識的情況下,不可能形成反對動機,那么行為人的反社會性意識又從何而來呢?所以,故意說與責任說明顯不妥。另外,作為刑法上的事實,不應當是“裸”的事實,而應當是具有社會意義的、進入刑法視野的事實,而什么樣的事實能進入刑法的研究視野呢?也即刑法介入社會事實的契合點在哪里呢?筆者認為,必須存在這樣的契合點,這樣刑法的介入才是正當的。具體到作為義務的錯誤上來,我們認為,行為人在作出具有刑法意義的行為時,必須就認識到的現象進行相應的評價,即事實的評價,通過這種評價就將“裸”的認識與法的評價聯系起來,而這種行為人對事實的評價本身又成為刑法評價的對象,正是通過這一點,刑法才與行為人的主觀方面發生接觸,才尋找到了規范的對象。這樣看來,違法性意識不要說也不科學。同時,正如學者批評的那樣,該說一方面是基于權威主義的法律觀,假定國民都必須知道法律,但這明顯與實際不符;[13]另一方面,該說只不過是為了處罰的方便而做出的沒有根據的擬制,明顯違反責任主義。[14]
最后是把絕對的構成要件說將作為義務的錯誤問題納入構成要件的范圍內進行研究,認為作為義務的錯誤一律阻卻犯罪故意。但是就筆者看來,由于在德日刑法學中,采取遞進式的犯罪構成模式,行為是否符合犯罪構成的判斷是一種抽象的定型的判斷,所以在這種判斷過程中不涉及對行為價值的判斷,否則這種判斷就變得模糊不清,并且與后面的違法性判斷發生沖突。因為如前所述,對構成要件事實的認識這僅僅是成立犯罪主觀方面最基本的一點,也可以說是最基礎的“素材”,重要的是對事實的評價,即行為人對該“裸”的事實是做何種評價的,這才是刑法關心的。例如,同樣是看到一個未成年人落水,生命處于危機狀態,未成年人的父親認識到這一事實與過路的第三人在主觀上認識到的是完全一致的。刑法不會對該第三人的“無動于衷”作任何評價,盡管他也認識到該未成年人落水生命處于危機狀態這一事實,因為刑法沒有干涉的契入點。但是,刑法就可以對未成年人的父親的不作為進行責難,其原因之一就是它處于保證人的地位,且他也認識到自己負有救助的義務,自己的不救助行為是與法的精神相悖的。但問題是,這種對事實的評價在德日刑法學的犯罪構成理論中,已經完全超出了構成要件符合型的判斷范圍。所以這與他們的犯罪論基本體系不匹配。
三、遞進式犯罪構成與相對兩分說的契合
比較而言,筆者認為,相對兩分說則恰與德日刑法學的犯罪論體系相調和。因為將保證人的地位作為構成要件的事實,而將保證人的義務問題則分解出來納入違法論的范疇。這樣,在構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斷的場合,就保證了構成要件判斷的客觀性,而對保證人地位的認識無疑就成為認識的對象,即判斷的事實,這為后面的有責性判斷提供了基本的素材,也就是說成為評價的事實與事實的評價的關系。將保證人的作為義務納入到違法性階段進行考慮,這主要是因為,在不作為犯中,要判斷行為人是否構成犯罪,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作為與不作為的等價值性判斷,而在行為的等價性判斷過程中,作為義務又成為問題的關鍵。也即作為行為與不作為行為是否具有等值性,不僅要從結果上進行判斷,最重要的還要聯系行為人是否負有一定的作為義務,只有這樣才能為行為人承擔刑事責任奠定客觀的基礎。在日本有學者對這種相對的兩分說持反對態度,例如日高義博教授就認為,如果完全排除保證義務的存在,要想正確地判斷構成要件符合性也是困難的。另外,到底能不能把保證人的地位和保證人的義務完全分離也是有疑問的。[3]149有學者堅持保證人地位與保證人義務一體說,認為對于保證人地位與保證人的作為義務,應當在社會觀念上作一體化的理解,因為二者的區分是相當困難的(大塚仁、田前雅英)。[9]97在筆者看來,反對者的意見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為一般情況下,行為人認識到其處于保證人的地位時,也很自然的就意識到了自己負有作為的義務,從這一點看來,上述批評似乎也無可非議。但是,若進一步考慮,保證人的地位與保證人的義務是否會存在分離的情況呢?如果兩者可以分開,那么上述批評無疑就是站不住腳的。正如筆者在上面分析的那樣,是否處于保證人的地位,這是一種事實的判斷,而行為人在一定情況下是否負有某種作為義務,則又是一種價值判斷。這兩種判斷雖然存在緊密相連的關系,對前者的認識必須建立在對后者的認識基礎上,但是他們畢竟屬于不同的范疇。況且在現實中,認識到保證人的地位對作為義務發生認識錯誤的情況也不是不存在。那么我們又怎么能僅僅根據一般的存在實事作為邏輯判斷的根據呢?所以,筆者認為反對者的論據是存有疑問的,其反對意見也是不成立的。
四、作為義務錯誤與耦合式犯罪構成體系的調和
我們知道,與德日刑法學中的遞進式犯罪構成理論不同,我們國家采用耦合式的犯罪構成理論,這樣在作為義務的錯誤問題上,我們就不得不具體聯系我們的犯罪構成體系,考慮理論上的契合問題。按照傳統的犯罪構成理論,在不作為犯中,我們重點考慮不作為行為與結果的因果關系以及作為義務的來源問題,這一點與國外的因果關系說有相似之處,我們忽視了對作為義務錯誤問題的研究。所以,對作為義務的錯誤是按照事實認識錯誤處理抑或是法律錯誤處理尚未作深入的探討。
但是,正如筆者在前面談到的,在任何犯罪構成理論中,我們都應當從理論上分清事實的存在與價值的判斷、評價的事實與事實的評價,他們均屬于不同的理論范疇,他們也各自有著不同的理論意義,對他們的判斷或評價都會產生不同的結果。行為人認識到了一定的事實,這在刑法學中只是為后面的主觀行為奠定了基本的心理事實基礎,重要的是在認識到這一事實的基礎上它是如何加以評價的,而這種評價恰好是規則的要素之一。具體到不作為犯中,刑法不僅關心“行為人認識到一定的事實”,刑法更關心的是當行為人有這種認識之后是如何加以評價以及如何選擇自己的行為的。而這種評價就是違法性的判斷過程。刑法譴責的不僅僅是行為人選擇了違法(從法的角度講即客觀的違法)的“不作為”,刑法還譴責行為人在認識到行為的違法性的情況下形成的反對動機。那么,當行為人連作為義務都沒有認識到的情況下,其反對動機又怎么會形成呢?所以,在不作為犯中,我們也有必要厘清“事實的認識”與“事實的評價”,前者為后者提供評價的素材或對象,認識到前者不代表就對后者一定會作出“適法性”解釋。
在此基礎上,筆者以為,在我國的犯罪構成體系下,不作為犯的主觀方面應當劃分為兩個層面,即認識層面與評價層面。而在作為義務錯誤的情況下,我們應當分清行為人是屬于對保證人地位的認識錯誤還是對作為義務的認識錯誤,前者應當屬于對事實的認識錯誤,后者則屬于對法律的認識錯誤;在前者的場合,錯誤阻卻犯罪故意的成立,在后者的場合則應當認真分析該錯誤發生的具體原因以及行為人當時所處的環境,區分該錯誤是否可以避免。具體來說,在行為人對保證人地位發生認識錯誤的場合,首先應當阻卻犯罪故意的成立,其次我們應當分析行為人對該錯誤是否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即行為人對該錯誤在主觀上存在過失時,可以以過失論處,當行為人已經盡了力,當由于當時的客觀環境以及自身的能力限制,根據當時的判斷,行為人不可能認識到該事實時,行為人在主觀上就不具有可譴責性。同樣,在法律錯誤的場合,我們也應當分析該錯誤是否具有可避免性、行為人對錯誤是否具有過失,當法律處罰過失犯,而行為人對作為義務的錯誤是因其過失導致的,則行為人就應當承擔過失的責任;如果法律不處罰過失犯或者行為人對作為義務的錯誤具有不可避免性時,由于他主觀上不存在過失,不具有非難的可能性,所以不應當承擔責任。
注釋:
① 當然,在國外有學者認為這兩種分類的稱謂代表不同的意義,從國外學說發展的情況來看,大多數學者開始采用構成要件的錯誤與禁止的錯誤。但我國學者則一般沿用通常的稱謂,即法律的錯誤與事實的錯誤。需要指出的是,意大利刑法學者帕多瓦尼認為,法律的錯誤、事實的錯誤應當與對法律的錯誤與對事實的錯誤做嚴格的區分。本文沿用學界傳統的稱謂方式。
② 這是在保證人的地位與保證人的義務的關系問題上堅持分離說得出的結果,如果堅持一體說,一般會認為,應當在社會觀念上對兩者作一體化的把握,作為義務的錯誤當然屬于構成要件的錯誤,不阻卻故意的成立。
[1] 陳樸生.刑法專題研究(第2版)[M].臺北:臺灣三民書局,1979:93.
[2] 高銘暄.刑法學原理(第一卷)[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550-587.
[3] [日]日高義博.不作為犯的理論[M].王樹平,譯.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2:149-152.
[4] [日]大谷實.刑法講義總論(第 4 版)[M].東京:成文堂,1994:201.
[5] [意]杜·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學原理[M].陳忠林,譯.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238.
[6] 馬克昌.犯罪通論[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317.
[7] 陳興良.本體刑法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370.
[8] 韓忠謨.刑法原理[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126-129.
[9] 張明楷.外國刑法綱要(第二版)[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97-131.
[10] 蘇聯刑法科學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4:59.
[11] 馬克昌.比較刑法原理——外國刑法學總論[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435-438.
[12] [日]佐伯千仞.四訂刑法講義(總論)[M].東京:有斐閣,1981:252.
[13] 趙秉志.犯罪總論問題探索[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225.
[14] [日]木村龜二.刑法學詞典[M].顧肖榮,等譯.上海:上海翻譯出版公司,1991:255.
D924.11
A
1674-8557(2010)01-0055-06
2010-01-21
吳振興(1946-),男,遼寧沈陽人,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張偉(1982-),男,甘肅正寧人,武漢大學法學院2008級刑法學博士研究生。
王魏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