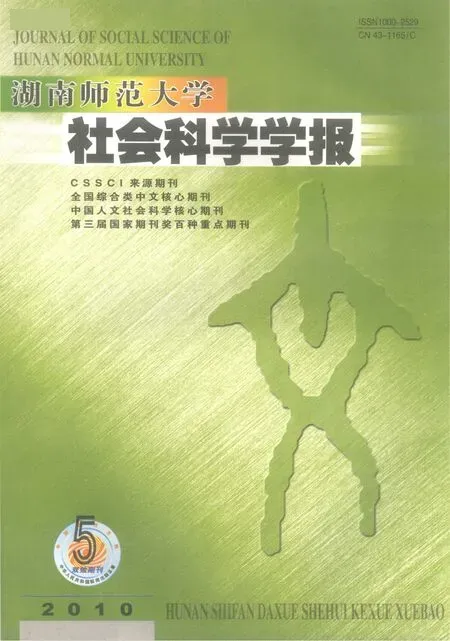社會信任與和諧社會建設
南京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 朱 虹
社會信任與和諧社會建設
南京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 朱 虹
和諧社會首先是一個有秩序的社會。社會如何有秩序?信任無疑是最重要的建立社會秩序的微觀機制之一。早在17世紀霍布斯就提出著名的“叢林假說”:人與人之間如果缺乏信任就將陷入人人相互為敵的生存困境。100多年前社會學家齊美爾對信任發出了“社會何以可能”的追問。他認為信任是促進社會整合的力量,我們的社會聯結是無法建立在對他人的完全了解的基礎上,如果人們缺乏起碼的信任,社會就會解體。如果說霍布斯和齊美爾對信任與社會團結的思考僅僅是哲學思辨的話,人類社會進入20世紀中葉呈現出高風險社會特征,信任與社會團結的關系成為一個重大而迫切需要解決的全球性的、時代性的課題。與此同時,隨著中國社會進入了全面轉型時期,信任的缺失成為亂像叢生的社會問題的根源之一。人們對假鈔、假證書、假貨、虛假新聞和廣告早已司空見慣;對專家的見解、知識技術的可靠性、對銀行、法院、政府的信任都表現出信心不足;“殺熟”現象的出現和蔓延,導致夫妻、父子、親友之間人人自危。信任危機確已成為導致社會秩序與人們本體安全喪失的根源之一。創建和諧社會就必須重拾社會信任。
重建社會信任,首先要弄明白什么是信任。關于什么是信任,心理學的視角將信任視為“發生于人與人之間的事件中所擁有的一種期待”,信任是一種個人動機,也是一種態度。為什么有的人傾向于信任他人;有的人則傾向于懷疑他人?心理學家的解釋是:信任依賴個體的人格結構,包括認知、情感、信心等方面。社會學家眼中的信任其實就等同于信任的社會功能。巴伯指出信任的社會功能一是維護社會秩序,為相互作用的行動者提供道德期望圖式;新功能主義社會學家盧曼開宗明義地將自己的著作取名為:《信任——一個社會復雜性的簡化機制》。在盧曼看來,信任本身其實就是對付不確定性的一種策略,是化解復雜性的社會機制。如果沒有信任,人類只能進行非常簡單的當場互動合作,而高度分化的現代社會,人們面對的是一個超級復雜的世界,因此,信任已經不是一個道德倫理問題,而轉變為一個認知問題。信任簡化認知,是人們進行復雜社會互動的基礎。科爾曼對信任的詮釋是從理性選擇的角度開始,他認為信任作為持久交易的“游戲規則”是在群體成員進行理性互動中自然而然地產生。守信用和信任他人將使雙方都獲得所期待的回報,否則兩敗俱傷。由此,科爾曼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社會資本,人們為什么要選擇信任他人和保持誠信是因為信任是一種重要的社會資本。綜上所述,信任具有多重含義:是一種對他人行為的樂觀的、積極的期待;一種正面的社會態度;是維護社會秩序的社會控制機制;是應對復雜世界不確定性的簡化機制;是一種能獲得高利益回報的社會資本。
有趣的是,文獻梳理可以得出有關信任的清晰含義,但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世界里,信任卻是一個很少使用,且語意不詳的概念。這是我們“社會誠信建設”課題在進行全國性的實證研究中發現的問題。比如,當我們詢問“你信任朋友嗎?”“你信任陌生人嗎?”被調查者常常表示無法回答,他們的理由是必須給出具體的背景,必須要有事件才能回答。無利害關系,或不打交道時對任何人都無所謂信任不信任。如此,我們每一道問卷調查題項都要設計一個具體的情景,而這一設計又必須是所有被訪者生活世界中熟悉的。我們的定量調查遭遇非常棘手的困難,但卻引發了對信任概念,以及當下人們糾結所謂信任危機的真正原由的重新思考。我們首先需要思考的是信任是一種現代觀念,還是許多持文化范式的學者認為的,信任是一種由來已久的文化特質或稱為地方性知識的集體習慣。在傳統社會,社會結構穩定、人們世代固定在鄉土社會,社會流動率低,傳統文化中的宗教、道德、倫理就足以確保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而無需強調信任問題。自給自足、田野牧歌式的生活模式,其實也是人們之間社會交往頻度很低,絕少與不熟悉的人與事打交道的社會。一切盡在掌握之中,是身處變化莫測社會環境的現代人的虛妄之言,卻是過去的現實。現在,人們對信任的普遍關注、或者成為一種本體安全的迫切需要,是因為在日常生活世界中人們必須與變化的、陌生的、利害交關的人和事發生社會互動。信任危機確已成為讓人們普遍感到不安的社會心理事件,但信任危機的發生并不僅僅是人們通常認為的道德層面或者與社會失范的問題。其實,信任危機就是一種現代性的危機,是人類在風險社會來臨后的不知所措。所以,我們認為信任是一種現代觀念,因此我們去糾結信任如何喪失的偽命題,還不如去探討現代社會如何建立社會信任,得以幫助人們適應并應對風險社會。
既然信任是一種現代觀念,那么當下熱議的重建社會信任的路徑,就無法從傳統社會文化中找尋和繼承。中國人的傳統信任關系,僅僅涉及到以鄉土和血親為紐帶的人際信任,是與不流動的鄉土社會結構相匹配,主要通過鄉規民約等習俗對人們進行熏陶、濡化而得以傳承。正如費孝通所說,“鄉土社會的信用并不是對契約的重視,而是發生于對一種行為的規矩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可靠性”。這種傳統的人際信任文化模式面對高流動性、高異質性的人群共同體是不能發揮社會控制作用的。
我們認為,社會信任的建設首先應當向西方現代社會學習,建立全面的信用體系。信用體系是基于技術分析和信息采集而形成,包括貨幣、知識、權力等社會交往媒介的甄別與評價。當然我們會說信用就是信用而不是信任,信任不是技術,也不是理性決策,而是一種普遍的社會態度,是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正面期待。我們認為,人們依靠信用體系能發展出一種新的信任模式,既系統信任。系統信任是通過利用信用體系的安全保障代替缺失的信息,進而賦予人類對待復雜世界偶然東西的穩定態度。比如,人們對貨幣信用的系統信任,就是通過連續性的、肯定性的使用貨幣的經驗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來的。“什么人都是假的,錢才是真的”、“養兒防老不如養房防老”的拜金主義價值觀背后,隱晦地揭示現代社會人們從人際信任向系統信任的轉向。系統信任的建立大大地簡化了紛繁復雜的由陌生人組成的、大量的一次性社會互動所需的信息收集與分析的復雜過程,使人們在無需通過人際信任,就能進行可預期的、有秩序的社會交往。隨著信用體系日益細化、完美和合法化,最終將成為人們的先驗信任態度,系統信任就建立起來了。從因熟悉帶來安全感的人際信任向系統信任過渡,是一種偉大的文明進化過程,也是我們建設和諧社會的努力方向。
其次,要培育嶄新的信任文化。在農民即將終結的時代,鄉土社會終將成為一個永逝的時代背影。我們已經踏上了現代性的不歸途,儒家傳統文化之余光難以照亮中國社會信任建設的未來之路。培育新的信任文化也許應該從理性的路徑,而不是道德和倫理的路徑切入。信任關系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后理性的,但很少是非理性的。我們把給予信任還是不給予信任、是守信還是背信作為一個人們理性選擇行為,兩害情相權取其輕,如果這種行為獲得積極正向的報償,守信行為就得以強化,使得行為者不斷地重復這種行為,那么它就漸漸成為一種習慣,成為人格的一部分。這種人格擴張到社會的層面就成為集體人格、國民性,進而固化為信任習俗,成為一種新的文化傾向,一種社會資本。總之,我們認為,信任關系是可以通過理性選擇而建立起來的,并且在適當的社會條件和環境下可以轉化為一種普遍的社會文化傾向。目前,一方面,我們要積極推進信用體系的完善,讓守信者能獲得更多的社會合作的機會;另一方面,還必須加強對不誠信行為的社會懲戒,方能形成培育新信任文化的社會條件和環境。
如果說以上兩個建議來自信任與現代社會結構之間的理論推演,本文接下來提出的建議則來自我們課題組的實證調查的結果。建設誠信社會涉及到對政府、專家、符號、商業、人際方方面面的內容。調查顯示,對政府的信任,尤其是對基層政府的信任首當其沖,是目前導致人們是否持有社會信任的基礎;另外,媒體大量充斥社會失信行為的報道,造成一定程度的社會恐慌,強化了民眾的信任危機感,進一步加深了社會猜忌和沖突。最有說服力的調查數據是,讀過南京“彭宇事件”新聞報道的人,不到8%選擇“看見老人摔倒,毫不猶豫上前攙扶”的調查選項;而沒讀過該新聞報道者則高達84%的人選擇“攙扶老人”。政府相關管理部門應當根據新聞報道可能產生的社會后果,對媒體議題設置進行前瞻性的監控;同時,還需著力培養民眾的媒體素養,提高民眾面對傳媒報道的各種信息時的選擇能力、理解能力和質疑能力。最后,社會情感也是影響社會信任的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我們的調查發現影響社會階層之間的信任,與是否有直接互動經歷,以及可信程度的理性考察關系不大,而往往是基于強烈的情感聯系。一個與同鄉五個小偷同居一處的民工,在接受我們的訪談時,明確表明他信任那些小偷同鄉,而不信任城里人;問卷調查中高達92%農村被調查者認為城市人不可信;那些有相同宗教信仰的人,對自己的教友則非常信賴。通過增進社會各階層、群體人們之間的社會團結與認同,是我們建設普遍社會信任的另一重要途徑。
(責任編校:文 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