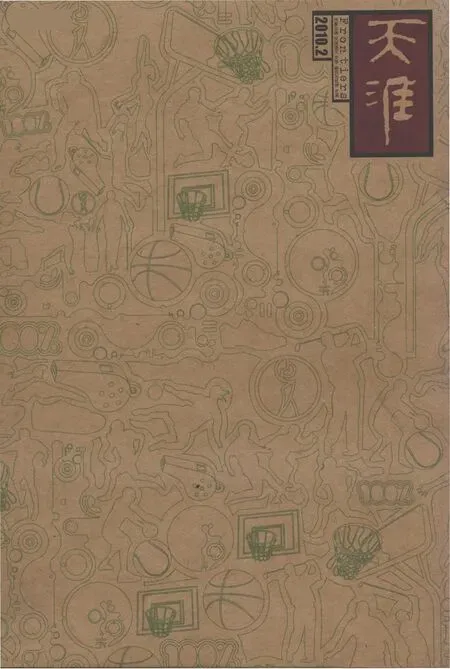繪畫的勝利
魏尚河
繪畫的勝利
魏尚河
盧卡·托馬斯被國人所識,是近幾年的事。他最早的薄薄的畫冊,出版于2002年,由湖北美術出版社編輯。
盧卡·托馬斯來自比利時的莫特賽爾,出生于1958年。1976年到1986年,托馬斯就讀于布魯塞爾和安特衛普的幾所藝術院校,學習繪畫、美術和藝術史。他在1985年之前,幾乎沒有參加過任何一個展覽,1985年,他第一次舉辦了個展。1990年起,他的繪畫展覽開始在國際上為人所知,例如以“迷信”為主題的巡回畫展,1994和1995年,相繼在芝加哥、法蘭克福和倫敦等地展出,逐漸成為國際藝術界里必談的重要人物。
托馬斯的作品,全是架上繪畫。他的繪畫尺寸一般都比較小,多半不超過一平方米,這是過往的事了。近幾年,他的作品尺寸越來越大,最大的有三五米。早在六十年代,唐納德·賈德就已經反對過托馬斯的這類繪畫:“既不是繪畫,也不是雕塑”,因為“它們在繪畫中的主要錯誤,就在于它們像一個規整的方盤子,平平地靠在墻上”。
時至今日,依然有人關注繪畫的死亡問題,在我看來,這不是一個根本問題,要緊的是,人類的思維方式如何開放和延展,認知世界的能力如何深入,繪畫,只是一個獨特的、無法替換的媒介而已。就像托馬斯,他貌似傳統的做法,實際上有他深刻的觀念和意義。“他已經把他的繪畫作為一種含蓄而委婉的策略,回應了那些‘極簡抽象主義’繪畫,對繪畫藝術本身的挑戰。”對于繪畫在當代藝術中的合法性,托馬斯并不在乎,重要的是,他的作品著重強調繪畫在當代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對于托馬斯而言,在某種向度上,繪畫的問題,即繪畫的主題。
繪畫與圖像
托馬斯的繪畫方法,很大程度上受惠于電影中的攝影術。上世紀八十年代早期,托馬斯曾經學習電影制作,返回繪畫創作中,他引入了一系列電影和攝影的技術與方法,如近焦距、剪切、取景框架、序列性等,這些技術至今還是他繪畫發展的重要因素,談論這一點尤為關鍵。
這種借助于電影和攝影的觀看方式,在當代繪畫中,托馬斯是一個先行者,因此,它有力地開拓了繪畫的觀看方式,使得繪畫在跨領域的互動中,成就了繪畫在當代藝術中的視覺前瞻性。它打開了一扇門,通往多元方向的道路。

但這遠遠不夠,在畫家的所有作品中,自始至終,都有一種顯著的影像形式語言:橫向的筆觸。“橫向的筆觸”對于托馬斯來說,是區別于美術史上一切畫家的典型性標志,是具有價值的標志,而絕非普通符號。因為,它是托馬斯的工作重點之一,在理論和視覺上,橫向筆觸對等于電影和攝影的某種視覺構成方式,這也是他突破傳統繪畫面貌的有力手段,既對應他自身在信息時代的視覺經驗,同時,也是對繪畫在文化出路上的嚴肅考量。結果,作者使得圖像更具圖像的性質(即圖像在視覺意義上的本質,杜絕簡單的社會、文學反映論),而繪畫,更成為真正的繪畫(保持了繪畫的自發性、書寫性和繪畫品格的高度要求),二者達成完美的融會。在今天的時代,這是不易的。具體來講,橫向的筆觸體現為,幾乎所有構成形象的筆觸,其方向都是橫的,即使在傳統繪畫里,物象的結構需要相應的縱向表達,比如,垂直的桌腿,而在托馬斯這里,他不用傳統的縱向筆觸,畫中所有的物象結構,盡量使用橫向的筆觸,即使微妙的細節也如此,以便高度保持和主題的一致性。
多元主題
托馬斯的繪畫,始終呈現出一定的距離,它與可見物的進行時態保持隔離的關系。與其說,他在繪畫中與眼前的可見物保持了一定的距離,不如說,他不相信眼見的就為真實。他眼中的世界,是逐漸褪色的世界,一切并不新鮮,事物停留在消失的邊緣,或輕微的運動于消失的過程中。事物回到它自身的“歷史”中,返回“記憶”的知覺中。只有與形象保持一定的距離,形象才能保持一定的真實性,這在哲學上和心靈層面都具有說服力。的確,托馬斯幾十年的工作生涯告訴我們,他對鮮活的正在發生的時代,并無興趣,而革命性的信息時代,衍生了無比豐富的影像世界,在此視覺經驗里,如何詩性地表達他的世界觀,他的繪畫哲學,他必須強有力地借助影像武器,這是他獨一無二的地方。托馬斯的繪畫是一個巨大的數據庫,其來源于照相、電視和電影的圖像。
這些圖像生活在現世之后,它們無法重疊于毫無距離的世界。它們更多的呼吸于事物自身的記憶片段中,以及“記憶的歷史”里。從某種意義上說,記憶是關于“歷史”的,更是有關“時間”的。對于時間與記憶的密切關系,身為一個畫家,托馬斯更像一個考古學研究者,他試圖用繪畫的元素將二者的關系逐步建立起來。就像他的一些作品標題,也是以探討、分析的方法和出發點,介入主題,如1989年的《研究之一》、《研究之二》、《研究之三》,以及1988年的《時間之一》、《時間之二》、《時間之三》和《時間之四》等。
托馬斯的記憶主題,一小部分,關于人類的歷史,其中有納粹暴行的記錄和比利時對剛果的政治干涉。即使如此,畫家依然保持他一貫的態度,作品并非簡單地凸現社會政治反映論,因為他對事件和觀念的表達并不明確;另外的大部分,他在觀照日常生活的平凡瑣事,包括那些非常微小的極不引人注目的事物。在他的繪畫中,許多原有圖像的細節被隱去,在不失大體的形象結構外,某些局部甚至不合現實邏輯,在簡單的輪廓和模糊的影像上,強調了繪畫的橫向筆觸以及褪失的色彩。托馬斯認為,再現不可能是真實的全部,記憶原本就是主觀的、凌亂的,記憶的內容必須經過修補。確實,他“通過對事物細微線索的暗示,創造出模糊的片段和細節,正如我們支離破碎的、片段的記憶”。值得贊嘆的是,托馬斯的繪畫輕松地呈現出某種難以忘懷的詩性氣質、古典浪漫主義意味和難得的高度繪畫品格。
作品回顧
我手頭收藏了一本大型托馬斯畫冊,英文版,印刷不錯,設計、排版俱佳,好像收錄了藝術家的訪談與評論,我看不懂,要緊的是,它囊括了他早期到近年來的重要繪畫作品,等于一個紙本回顧展。我們先觀看他早期的小幅作品吧。
作于1989年的《懸念》、《兇手》和1990年的《仆人》,以及《觀鳥》等繪畫,在主題、形式和語言上具有一致性。一個或二三個占畫面比例很小的人物,他們在較大的自然環境里,勾勒出日常行為。帶有普遍性的生活材料,是托馬斯經常使用的,但我們看到的畫面上,風景和人物已經與可見物產生相當大的距離,它們處于——更為遙遠的、更低的、更寂靜無名和莫名的狀態中,基本的輪廓和基本的色彩,構成有缺失、間隔、模糊感的主體形象。作者在其記憶與事物之間,永遠隔著一段中間地帶,他繪畫中的形象,向著記憶的方向逐漸靠攏,準確地講,記憶就是現實的遺骸,就是事物以不直接靠視覺顯現的存在方式,記憶是我們存在的某種死亡形式。但畫家,卻要讓它視覺化,從而成為我們的知覺經驗。
托馬斯采用回溯記憶的方法,我們看到在《仆人》中,風景的形象已經簡括至最基本的地步,綠色和黑色就完成了任務,人物簡單的如影子。“印象”——對于處于時間中事物的印象,不確定、游移的印象,是對托馬斯繪畫的一種簡單認識,這個認識是存在的,但事情往往沒有如此簡單——在這里,記憶、時間的基本特質和基本價值,才是他所專注的中心。他在事物的表面裹上了一層“印象”的外衣,強調了“大致”、“基本”和“陌生”等詞的作用,以此支持了距離的某種價值。在這張畫里,季節的特征和氣氛,我們能夠清晰地感覺到,人物的性別也能了解,但是細節,卻被作者有意地掏空了。沒有局部的“歷史”,只有整體的“印象”。在托馬斯的作品里,我們似乎無法把握客觀現象的真實,一切皆稍縱即逝,漸漸地,消失為記憶的標本。這個標本盛載時間,我們只能去研究這個標本的所有特性和價值,以此求證和認同人的存在的可能性。

1992年,托馬斯完成了重要的系列作品《病癥》。《病癥》由單幅的十件作品組織而成。它的創作源于一份題為《病癥》的醫療手冊圖解。它們排列在一起,靜止的畫面在不斷的變化和推進,構成整體的時間上的連續性和運動感,恰如電影鏡頭,針對于細節的一次次閃回。雖然,“病癥”系列中單幅與單幅作品之間,并無直接的線性聯系或上下文語境,但連續性的靜止畫面使得每幅作品都具有基本的內在關聯,那就是疾病的事實、疾病的表面形態和對于疾病的分析、記憶和視覺化的展示。事實上,有評論認為,“肖像的冷淡氣氛和他們全部的被動表情,正是由于這些肖像畫并不是關于這些人的,而是針對于他們的疾病,不是關于具體的疾病,而是關于疾病的現實”。托馬斯在這些圖像中,冷靜如醫生,對于疾病的現實進行簡練的描述,記憶的不同斷片在不同的時間區域中,連貫在一起,并保持了各自的差異性。在《病癥》中,作者對于記憶的陳述方式做了時間意義上的分解,在一個時間段上,將不同的圖像單位進行本質的排列,于此,繪畫的內容則漸趨擴散。用一組組圖像來形成主題的推進和完成,是托馬斯常用的一個演繹方法,一個獨特的有效的觀念。
有一點必須強調,截至2000年左右,托馬斯之前的大部分作品,在形式和內容上,都非常簡潔超然,如果說,這樣會讓我們覺得過于簡單,甚至甘冒危險的話,那么,在2000年之后,托馬斯的繪畫有了顯著的改變,除了多樣的形式變化外,最重要的,他的作品由原來的簡潔,轉成極為細致入微卻輕松悠然的敘述。他可能意識到,他的主題必須具有細節的說服力,這種說服力絕非多余的細節堆砌,而是繪畫在一定階段,自身的生命需求和對自足的渴望。近年來,托馬斯的作品尺寸越來越大,對于物象的變化也趨于微妙、精湛和豐富的書寫,作品《猴子》、《鴿群》、《塔》等,就是這一時期的杰作。在這些作品中,畫家依然沿用一貫的橫向筆觸,內容更加飽滿有力,不同的是,這些畫面有的更為模糊,很像電影或電視畫面的低質量的脫色效果。根據這種脫色效果,無論平庸的日常物品,還是比利時對剛果的政治干涉,都顯示出它們的不重要性。托馬斯似乎對圖像產生的過程和圖像背后的秘密,有認識和揭露其真相的愿望和努力。我們在生活里所看到的,只是事物的假象,“假象”,眼睛看不見世界的整體。而這些脫色的圖像,他們在被認同的同時,也暗含不確定性,一些在消失的過程中被確立的形象,因此常常顯得游移、寂滅。
繪畫的勝利
沉思默想要比直接引起視覺的刺激重要得多,這是托馬斯一直認為的觀點。這位杰出的當代畫家,他的繪畫淵源,可以聯系到佛蘭德斯古典大師們的傳統和西班牙二十世紀后期浮世繪畫的敏感性。在現代藝術的精神傳承上,他極有可能受到法國畫家塞尚和意大利畫家莫蘭迪的影響,我認為,這種影響非常積極、正面,且極具文化價值,尤其在當今歐美后現代語境中。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越了當代德國畫家里希特,比如,圖像與繪畫關系的開放性表達,圖像與繪畫的更深層的認識,以及繪畫在今天的合法性與價值突破。就某種意義而言,里希特試圖“拯救繪畫”,給它一個完全新鮮的出口,自然功不可沒,但對于今年五十歲、后勁正足的盧卡·托馬斯,無論從文化或者藝術的角度,他則取得了真正意義上的,繪畫的勝利。
魏尚河,畫家,現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我的美術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