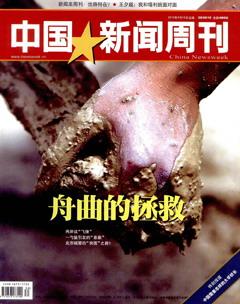NGO被購買的“錢” 景
王全寶 王 雪

北京香山腳下,一棟小二樓辦公室里,吳淑芝正與電話另一端的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韓俊魁教授探討聾兒抽樣調查服務問題。
吳淑芝現在的身份是北京市海淀區“莎利文康復中心”主任。該中心主要服務于聽力、發音有障礙的人群。7月12日,在北京市召開的政府購買社會組織公益服務項目推介展示暨資源配置大會上,吳淑芝的“莎利文康復中心”獲得民政局7.3萬元資金支持。
“盡管這些資金解決不了什么大的問題,但是它讓我們‘民非(民間非政府組織)看到了希望。”吳淑芝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資源配置
在7月12日北京市政府購買社會組織公益服務項目推介展示暨資源配置大會上,共有35個項目正式簽約,簽約資金為881.6萬元;158個項目達成合作意向,涉及資金為819.33萬元。大會現場共有386個社會組織和單位協商洽談了328個項目。
北京市社會團體管理辦公室(以下簡稱社團辦)負責人溫慶云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語氣中頗有些自豪,“資源配置大會在全國歷史上是第一次,獲得民政部高度肯定”。
會議當天,北京市副市長丁向陽積極評價:政府購買服務,有利于政府轉變職能、精簡機構、提高行政效率;同時也能填補政府公共福利服務的不足。“這是一項創舉,非常值得肯定。”
今年初,北京市民政局開始把社會組織、公益項目納入統一規劃,進行計劃性安排,試圖把社會組織公益資源和政府公共服務資源進行整合和對接。
北京市社團辦副主任于清源向《中國新聞周刊》解釋說,“動員基金會、民辦非企業單位包括一些愛心人士,安排有捐贈意向的單位和有資金需求的社會組織進行洽談,現場簽約。我們在前期會掌握一些資源,在大會上為他們牽線搭橋。”
據了解,北京市政府購買公益服務要經過幾道“工序”。首先要對服務項目進行評估。考查項目是否符合政府的倡導方向以及百姓需求,評估項目的可復制性和可持續性。評估通過之后由專家進行審定。而后決定以何種方式購買,與社會組織簽訂合同。完成購買之后,專業的項目評審委員會對項目進行監督,確保政府購買服務的質量和效果。
不過在專家看來,以上資源配置大會距離真正的“政府購買服務”還有一段距離。據知情人透露,盡管北京市有關部門已經起草了一份文件——《北京市政府購買社會組織公益服務項目試點工作意見》,但在“錢”的問題上,北京市民政局頗傷腦筋。
“實際上財政對購買服務沒有劃撥專項經費。購買哪些服務,怎么購買,如何監管購買后的效益都要經過深思熟慮,認真研究。不能讓錢打了水漂。”溫慶云說。
在7月30日的北京-陽光公益創新論壇上,北京市社團辦秘書處處長任淑菊作了如下表述:對規模大、影響范圍廣、社會效益好、可持續性強的公益項目進行全額購買。對有資金缺口的公益項目以補貼的行式給予資助,對社會組織自籌資金開辦的公益服務項目,實行資金獎勵。
在資源配置大會之前,吳淑芝的康復中心得到的政府補貼都是以獎勵的形式獲得。“做得不好就沒有這個錢”,“莎利文康復中心”之所以能夠得到補貼,是因為在每年的綜合評比中表現優秀,而更多的社會組織則沒有這樣的機會。
需求強烈
北京市社會組織建設與發展專家委員會成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NGO研究所所長鄧國勝認為,北京市民政局召開社會組織資源配置大會意義非常重大,這表明了政府購買社會組織服務的態度,向構建“小政府、大社會”邁出了一步。
2010年2月4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上,溫家寶講話指出,由政府保障的基本公共服務提供上,應該更多地利用社會資源,建立購買服務的機制。要逐步做到凡適合面向市場購買的基本公共服務,都采取購買服務的方式;不適合或不具備條件購買服務的,再由政府直接提供。要鼓勵社會資本投資建立非營利性公益服務機構。
溫家寶的講話,被業內專家看作是中央推進“政府購買服務”的一個信號。但實際上,在沿海發達省份,“政府購買服務”早已實行。
從2001年試點到現在,深圳市的大量公共事務委托外包給非政府的機構,已經全部社會化。深圳最早從園林、綠化、環保、環衛等距離政府權力中心比較遠的公共事務開始外包、委托、購買;再是機關事務管理局的后勤社會化,慢慢發展成為公共品市場化和社會化。從公用事業水電氣開始,到民營醫院、民辦學校、政府培訓機構??
2006年上海浦東新區社發局、經委、勞保局等8個政府部門分別與民辦陽光海川學校、陽光慈善救助社、街道老年協會等8家民間組織簽訂了購買服務的協議。
上海市楊浦區民政局副局長曾群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最近民政部與上海市民政局簽署了一個社會管理試驗城市的“部市協議”。其中就涉及社會組織管理方面內容。
2009年12月,一筆來自財政部的5000萬元撥款劃入了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小天使基金的賬戶,使1548名在小天使基金等待救助的白血病患兒每人獲得3萬元醫療救助金。
輿論認為,這是首例“中央政府用財政資金購買NPO(非營利組織)服務”,有著開創性的示范意義。
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韓俊魁分析認為,當前社會對公共物品公平供給有著強烈的需求。比如在艾滋病領域,有些特殊的人群不相信醫務人員和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員。如果想要解決問題,必須依靠民間的力量,依靠NGO去靈活地開展工作。另外,政府也希望能夠成為社會組織的資金源頭,來改善它們對于國際NGO長期以來的依賴關系。
任淑菊也認為,社會組織服務民生行動,覆蓋了社會廣泛的領域。通過政府購買社會組織公益服務,社會組織把政府不便做和企業不愿做的事務承擔起來,也形成了政府扶持社會組織發展的長效機制。
體制堅冰
2006年,為了使北京市殘聯成為“莎利文康復中心”的業務主管單位,吳淑芝軟磨硬泡,奔波四個月之后才注冊成功。吳淑芝認為自己還是比較幸運的。
登記注冊的困難無疑讓許多致力公益服務的單位和個人望而卻步。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公民社會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袁瑞軍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一般政府購買服務都要先看這個組織是否注冊。有很多小的組織找不到它的業務主管單位,這是一個比較大的瓶頸。”
目前北京市仍對社會組織實行雙重管理制度(“登記管理機關”和“業務主管單位”雙重負責)。面對各界對社會組織登記制度的質疑,溫慶云表示,廣東已經開始實行直接登記體制,“它不再是雙重管理,由民政部門直接登記”。
溫慶云認為,雙重管理體制有其存在的必然性,體制的改善還有待時日。“北京市民政局出臺了《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條例》,規定中關村的社會組織實行直接登記體制,同時可以不冠行政區劃名稱。”
盡管北京市開始對社會組織“松綁”,但是政府的職能轉變以及政府購買服務的理念還沒有完全樹立起來。
對此,北京市一位政府官員有著親身體會,“北京某城區把政府部門需要購買的服務項目列出來,剛開始很積極。但只有民政局列出了所需資金,其他各局均沒有做。這就涉及到權力的問題,涉及到利益的問題。”
政府內部職能的交叉,也導致政府購買服務的躑躅不前。上述官員表示,除了北京市民政局下屬的社會團體管理辦公室對社會組織進行管理外,北京市社會建設工作辦公室對社會組織的管理也有涉及。
社團辦屬于社會保障部門,社工委屬于政府機關。“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種內耗”。
從2009年開始,北京市提出“大民政”的理念,“大民政”其實就是“大民生”,就是要動員社會各方面的力量把民生做好。
上述官員表示,“大民政”不是大民政局,是指全社會都來關注民政工作。但改革的難點仍在于部門不舍得放棄自身利益。
曾群表示,要實現政府購買服務的良性發展,首先政府的思想要開放,能剝離的就剝離,該放手的就讓市場運作。其次要有明確的需求導向,不能為了政績去搞項目,為了招標而招標,要從老百姓的需求出發,同時要給這些社會組織一個寬松的環境。
北京市的政府購買服務已經起步,機制的建立需要破除一系列堅冰。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副院長張強認為應該對改革持寬容的態度,“在起步階段讓政府、社會組織各自起航,去摸索,效果或許會好些”。
對于政府購買服務的前景,吳淑芝充滿了樂觀,“政府在放權,另一方面,我們‘民非更要自律,要不斷提高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