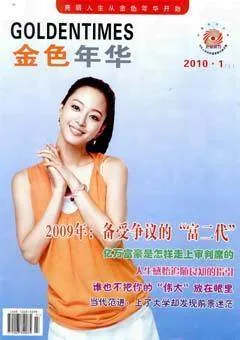全世界都學中國話
葉 研
姜松在白板上用水性筆寫了一個象形漢字——“教”。他轉過身來,向學生解釋教育的基本理念:“在中國傳統教育中,‘教,是手執教鞭,帶有管理、管制意味的知識傳授,而現代常見的教育,是一種平等的問答切磋的知識介紹。”
臺下坐著的15個青年,是美國夏威夷州瓦胡島上各類學校的漢語教師。作為夏威夷大學的漢語教授,姜松在對他們進行漢語培訓。他這天的課題是《中國“減負”與美式教育》。
姜松授課所在的夏威夷大學語言教學樓,正隱藏在濃蔭里,它曾見證大洋東西兩岸語言文化的首次全面接觸。
位于太平洋中央的夏威夷群島熱風吹雨,洪波奔涌。在洲際交通依賴航船的時代,來自東西兩大海岸的思想文化浪潮,千里萬里滾滾而來,在大洋中央交匯撞擊,鼓蕩起文化交融的壯闊波瀾。
在這座小樓里,中美兩國語言學者從事過早期中西語言文化溝通工作。中國首批現代語言學大家之一趙元任在這座樓里開設的是中國音樂課程。趙元任曾被推選為美國國家語言學學會主席、美國東方學會主席。上世紀70年代,周恩來總理曾和他探討漢字改革。另一位中國語言學大家李方桂也曾在這座樓里授課,后任美國國家語言學學會副主席。而美國漢學家約翰·狄方克則在這座樓里成功編纂了第一部美國漢語教科書《初級漢語課本》。
不過,在本世紀第一個10年,在夏威夷大學的校園內,又出現了新的學習漢語的生動景象。
這顯然不是某種漸進式的升溫。僅在夏威夷,歷經上世紀的數次漢語熱和中華文化熱以后,短短幾年內,二百多所孔子學院和二百多間孔子課堂如水銀瀉地,在人類長居的6個大洲普遍萌生,一陣不同以往的漢語與全球文化交融的清風,正撲面而來。
妮莎左手運毛筆,寫下“我愛中”三個字,“國”字沒地方寫了,拐到“愛”字旁邊,無拘無束
近十年來,各國政府推出的漢語教育計劃中,美國的動作比較引人注目。
俄勒岡州波特羅來納蘭州立大學(下簡稱波州大)已將漢語從次專業提升到主修專業。夏威夷大學、南卡羅來納大學(下簡稱南卡大學)、西密大等許多院校,都支持本校原有外語系和所屬學院的專業漢語教學,近年來,還逐漸在學分制度上增加漢語學習的分量。漢語教育從不記學分到次專業再到主修專業,已經成為一種趨勢。
美國聯邦政府推行“沉浸式”漢語教學,俄勒岡州是全美漢語教育的重點州,承擔試點。俄勒岡州的漢語教學被稱為領航項目。該州中小學漢語教學比其他州普及。“沉浸式”表示漢語教學要融入學習、生活、娛樂等等方面,并且漢語教育從幼兒園開始,直到大學畢業后的社會教育。還有人嘗試一種類似于中國“瘋狂英語”的教育方式,叫“瘋狂漢語”。
有聯邦政府支持,難怪州議員克利斯·伊德沃茨敢于開口說:“我們的目標是,不僅在某個地區推廣漢語教育,而想覆蓋全州各個地區。在所有的大中小學都推廣中國語言和文化,成為全美推廣中國語言和文化的先進州。”
州議員朱利葉斯·柯普爾表示了更大的雄心:“俄勒岡州有決心、有信心在漢語教學方面作全美的先導,甚至全世界的榜樣。”
在俄勒岡州,記者用一天僅僅跑了4所教漢語的學校,卻各有特色。
烏斯托克小學是全美第一家“沉浸式”漢語領航項目試點學校,一間教室里的孩子在做命題畫畫“橙色的柿子”,來自中國的老師教孩子們各種顏色的漢語讀音,用美術課帶動語言學習。另一間教室里,小孩子們用電腦輸入漢字。既學了拼音又學了文字,當然還有電腦使用,一舉三得。
浩津中學的學生稍大一點,老師在講南宋詩人葉紹翁的《夜書所見》。波特蘭國際學校是一所私立學校,校長奧馮索·歐西尼對漢語教學的意義,講得和州議員差不多一樣流暢。
“西北中國書院”(第一期)是一對印度夫婦投資150萬美元建立的。“西北”一是指俄勒岡州位于美國西北,二是指波特蘭市位于俄勒岡州西北;“中國人”和“漢語”在英語里是同一個詞;而“書院”卻是從幼兒園到中學。
這對印度夫婦的女兒妮莎,領著記者參觀整個學校,并用漢語介紹情況。妮莎9歲,戴個小眼鏡,身穿書院校服——咔嘰襯衫和淺棕色短裙。她去年參加全美漢語等級考試(HSK),是通過考試的年齡最小的考生。
“明星小考生”妮莎用食指立在唇上,帶記者躡手躡腳地穿過一間教室。教室里十幾個學齡前幼童在午睡。和幼兒園一樣,有一位老師坐在一旁守護。接下來妮莎帶記者樓上樓下地走,“這是我們的中文圖書館”、“這是我們的小班教室”、“中班教室”、“美術課教室”……妮莎打開一個大立柜,滿滿當當都是宣紙、毛筆,“所有中國教具都是專門去買的。”
妮莎左手運毛筆,寫下“我愛中”三個字,“國”字沒地方寫了,拐到“愛”字旁邊,無拘無束。
“不管你是否學漢語,你肯定要和亞洲打交道,和中國打交道”
一個跨國公司的老總,和一所美國高校孔子學院的理事會成員,這兩者聽起來似乎有些不太相關。
可吉姆·卡特似乎有些樂此不疲,這個耐克公司的副總裁,同時是波州大孔子學院的理事會成員。曾有人問他:你怎么想起抓教育來了?吉姆·卡特沒提教育,直接跳到經濟:“中國是美國俄勒岡州商業上最大的伙伴。任何企業忽視中國市場就會敗給對手。”
俄勒岡州議員克利斯·伊德沃茨也說:“俄勒岡州有很多企業和中國有貿易往來。我們的尤金區的企業從中國引進了太陽能利用裝置,這在美國處于領先地位。以前俄勒岡對東亞貿易的排位是日、韓、中,現在是中、韓、日。我們州已經注意到這一點,應該調整我們的策略。”
肇始于2008年的世界經濟危機,使世界的目光更集中到中國。“市場坨兒大”固然是原因之一,奧巴馬來中國就提到中國人講究儲蓄。而謀求雙贏共生的中國傳統策略,卻是外界接受中國和平發展的主要原因。
一個世紀以來,美國人幾乎不需要學外語。因為走遍全球各個角落,都有人講英語。南卡大學外語系主任瓦瑞西姆卻清醒地指出:“美國在外語教學方面是落后的。所有人對你說英語不是好事情。學語言對文化了解是有意義的。”
不過,美國是極富現實精神的國度。一旦朝野和學界看清了中國的重要性,許多知識分子立刻意識到了解中國、接近中國的必經途徑——漢語教育。
一種語言文化得到世界范圍的關注,必有其堅硬鑿實的原因。
以往,一種語言在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一個洲的推行,曾經伴隨著兵燹戰火、殖民擴張、強權奴役。一位菲律賓人對記者說過,“西班牙人在馬尼拉留下了天主教,美國人留下了英語”。這種歷史遺產,可以在整個“英屬印度”看到,可以在中亞諸國曾經的突厥語化和俄語化過程中看到。大至于洲,15世紀后,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語化(巴西的葡萄牙語化)和北美的英語化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例證。與此同時,數十種美洲土著印第安語言消亡。
英語在殖民時代取得日不落的世界強勢,又因兩次大戰后工業化國家主導全球貿易和國際計算機產業、網絡語言使用英語,其世界第一語言地位一再鞏固。
在十三億人口的中國,“反對蘇修”后的半個世紀以來,全國絕大多數中學生都在學英語,其他語種概無可選。除外語院系,全國絕大多數高校的公共外語課也只設英語,同樣是其他語種概無可選。以至于在中國的絕大多數場合,外語專指英語。上世紀一些好心的語言學家為增進世界溝通,集中多種語言的優點設計了十全十美簡便易學的“世界語”,并竭力在世界范圍推廣。人算不如天算,語言是社會行為,只按社會客觀規律發展。“世界語”自生自滅,英語大行其道,小語種繼續消亡。
就這個話題,美國南卡大學英語系主任瑞文斯發表意見說:“英語、美式英語有區域性。英國的殖民地時期是歷史。美國也是殖民地,小的本土語言在消失。語言和文化有關聯,民族的不同語言是各民族的文化傳統。學語言對文化了解有幫助。共同語加強了民族之間的交流。應該在保持母語的同時又學習多種語言,去了解別人。”
南卡大學默爾商學院負責人戴維說:“現在許多美國人學漢語,南卡本科生有漢語項目,18歲到22歲的學生對中國感興趣。我們商學院大部分學生愿意來中國企業工作。不管你是否學漢語,你肯定要和亞洲打交道,和中國打交道。”
“中國非常重要。美國人剛剛開始了解中國的重要性,要了解中國的文化歷史。”南卡大學教務長阿米瑞德斯博士進一步提出,“美國大學沒有很好準備,諸如師資、諸如……”
問題就這樣提出來了。現有的漢語國際教育規模滿足不了急劇增長的漢語教育需求。俄勒岡州議員朱利葉斯·柯普爾從小對中國感興趣。在大學學了一點漢語,又到中國學了兩年。但他懇切地說:“俄勒岡州許多人沒有這個機會,所以孔子學院非常重要。”
有需求就應該有服務。北京語言大學校長崔希亮表達了這樣的理念:竭誠為漢語學習者提供服務。只要有要求就應予滿足。
中國也的確需要世界的了解。中國政府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簡稱國家漢辦)于2006年在北京德勝門外建起了孔子學院總部,服務全球漢語國際教育,推動中華文化匯入世界文化的海洋。各國官員和大學負責人紛紛參觀中國國家漢辦,積極商議共同開辦孔子學院事宜。
熱心的俄勒岡州議員朱利葉斯·柯普爾在孔子學院總部“看到了漢字的發展和中國的文化歷史”。
“印象深刻。”他用漢語回憶說,“了解到明尼蘇達州有12間孔子課堂,我們當場表示要建12所孔子課堂。所有的漢語教學項目、文化交流項目,都會得到我們州的支持。因為位于西海岸的俄勒岡州和中國合作處于領先地位。”
俄勒岡州另一位年輕議員克利斯·伊德沃茨表示:“我們要建立更多的孔子課堂。我們不想做第二、第三,我們要做第一。我們要支持打造美國第一的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我們也鼓勵企業學習中國語言文化,更好地促進兩國貿易發展。”這位議員順便表示,“我已經在俄勒岡大學報了中文班,希望5年至10年以后能流利地說漢語。”
在2008~2009年的這段時間,密歇根州一下子冒出4所孔子學院。記者問:不嫌多嗎?不重復嗎?西密大國際教育學院院長麥克勞博士回答說,4所孔院差不多同時成立,反映了密歇根州的發展程度。每所孔子學院都有不同的側重點和辦學特色。底特律大學準備在城市推廣漢語教育,密歇根藝術大學側重教育理論、教學法的研究、教材的更新,密歇根州立大學側重網絡教學,西密大支持中小學的漢語教育。
看來美國人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西密大盡管受到經濟危機的影響,但為了促進本地區中小學漢語教育,不滿足于僅在東亞系設立漢語部,仍努力為該校孔子學院的建立提供各種條件。今年11月23日,該校舉行了與北京語言大學聯合開辦的孔子學院的揭牌儀式。該校東亞系主任王曉鈞教授擔任第一任孔子學院院長。
“缺一個,我還沒去過中國”
本世紀頭10年,漢語受到世界普遍重視,和平地走向各個大洲,但國際漢語教育并非自今日始,多年來,人們總能在世界某個角落聽到幾句漢語,就如驚鴻一瞥。
漢語走向東南亞,帶著自身的苦難辛勞。講漢語的人,以特有的勤奮推動當地經濟尤其是農業和商業發展,和當地民眾血脈交融,潤物無聲。
一個半世紀前,漢語被許多勞工帶到北美洲,經歷了百年血淚屈辱。講漢語的人,不少死在遠渡大洋的底艙,他們在異鄉幾乎被風雨抹平的墳塋邊,出現了橫貫北美的鐵路和連通大洋的運河。
在南美洲國家秘魯的首都利馬,你能看到數以千計的中國餐館,“炒面”、“白菜”、“餃子”、“米飯”等相當數量的餐飲類語詞,已經匯入當地的詞匯系統,甚至有當地的中餐館的招牌,直接就叫“吃飯”。
許多年來,各地華人社區在融入當地生活的同時,也在向后代教授漢語,少量中小學開設漢語課。這種教育或自生自滅,或經營平順。
記者2005年8月隨哈爾濱電視臺《睦鄰》攝制隊來到印度加爾各市答塔壩華人聚居區的全印最后一所教授漢語的學校——培梅中學。喜馬拉雅山脈的阻隔,使該校的教學內容、傳統宣傳內容原樣不變地保留下來。學校大廳里的標語是“禮義廉恥”,孫中山和蔣介石的畫像并排懸掛,已經陪伴過四代人。該校小學部的教室里,一位老邁的先生坐在木凳上領讀:“……山是栗(綠)的,水也是栗(綠)的”,幾十名華裔幼童齊聲復誦:“山是栗的,水也是栗的。”
在加爾各答,還有另一些漢語的零星留痕。1950年代在北京大學學過5年漢語的比·西·班納吉老人,曾參予過中印邊界談判。他說:“在印度能講漢語的人不多。現在兩國之間的貿易關系一天比一天增多,漢語人才也需要得更多,印度需要做好這方面的準備。”
當記者請老人對著攝像機鏡頭向當年北大的老師同學問聲好時,老人說:“我想再到中國,回北大看看。我想念他們……”隨即泣不成聲。
不過,老人可能不會想到,兩年后,印度尼赫魯大學同北京大學、印度韋洛爾科技大學同鄭州大學聯合建立了兩所孔子學院。
哈薩克斯坦共和國是本世紀在高校開展漢語國際教育較早的國家之一,就連他們的總統,都可以用漢語作大會發言。
哈薩克斯坦國立大學東方學系主任努爾諾莫爾教授說:“我們哈薩克斯坦國立大學是教中國文化、中國歷史和中國語言的重點大學。我們東方學系教授8種語言,學漢語的學生最多。目前有200多個學漢語的學生。今年58個學生畢業。我們的畢業生有的在駐中國大使館工作,有的在‘上海合作組織工作。哈薩克斯坦現在可以說是漢語熱,許多人都想學漢語。我們擴大了招生的計劃。”
法蒂瑪教授是哈薩克斯坦勞動和社會關系學院東方學系系主任,曾到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學習,喜歡跟著磁帶唱中國歌,包括鄧麗君的歌。她花了兩三年時間寫了一本書——《中國:傳說和真相》,介紹中國人的性格、中國菜和中國幽默。
1993年,法蒂瑪在新疆大學遇到學俄 語的中國男友。“以后他就到哈薩克斯坦來了,找我來了”。她送給記者一本書《現代漢語交際教程》。這是哈薩克斯坦國內第一部漢語教材,書的另一個書名是《我們一起來學漢語》。
哈薩克斯坦國立大學東方學系五年級學生薩爾謝姆別闊夫接受采訪時說:“我的中國名字叫成龍。今年五一節我去了哈爾濱。我覺得中國在發展,潛力很大。我想將來工作在外交部,或者工作在大使館。”
“成龍”的同學達烏果娃很不好意思地說自己的漢語名叫“張咪”。
“張咪”每天看書看報紙,每天上網,了解中國的情況。她認為每個民族的道德說起來都是一樣的,“如果你要當好的人,那么你就要當‘君子”。
有人問:“如果你學了中國語言、中國歷史、中國音樂,還缺什么?”
“缺一個,我還沒去過中國。”她說。
“孔子學院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來幫助我們的學生得到全球化的概念”
漢字是象形文字,好說不好寫,會說不會寫。常用的幾千漢字會造成相當大的學習難度。但在許多場合,漢語學習可以是快樂的。
南卡大學校園如畫,高大樹木間的草坪上,該校學生馬達凱給記者唱了一首周華健的《朋友》,還讀了一段漢語繞口令。黑皮膚的女生羅斯自己用漢語寫了一首短詩,參加詩歌比賽,這是首愛情詩:“我的男朋友很好看,也很機靈。我跟他有一樣的個性。雖然他住得不近,可是他經常在我的心離里。”
圖書館的臺階上,還有一群學生穿上中國各民族服裝,排練合唱《我和你》。站在后排的高個兒男生杜華倫,今年暑假曾到中國地震災區汶川擔當志愿者。他走進許多小學,了解災區情況。他帶去美國孩子寫給災區孩子的信,又帶回災區孩子給美國孩子的信。回到學校后設立了基金會,為改善汶川學童的教育條件募捐。另一位漢語名叫蘇寧的女生則到上海為世博會的籌備工作當志愿者。
草坪上,一個漢語名叫文大海的學生閃轉騰挪打了一趟長拳,然后平息收式。小伙子跆拳道和拳擊都學過,但他說:“太極拳有一種強大的力量。我還不知道這是怎么回事,我正在尋找這種力量的來源。”
剪紙、包餃子、包元宵等雜七雜八的民俗,已經走進許許多多接近漢語的外國人的生活。南卡大學默爾商學院負責人戴維說:“了解語言,文化、生活方式是重要的一方面。了解尊重別人的文化,是雙方受益的事,同時也讓文化碰撞。”夏威夷大學對東方、亞洲、中國的文化很注重。學生今年用英語排演了《白蛇傳》。
當然,影響永遠是雙向的。你來我往,雙方受益,是近年漢語國際教育的常見色彩。
走出去,才能發現自己的短處。本文開頭提到中國的“教”字現象,幾乎是所有在中國教漢語的人來到國外感覺最突出的問題。
南卡大學孔子學院院長臧清、波州大學孔子學院院長劉美如等許多教授無不深感,中國國內教法完全不能適應漢語的國際教育。走出去,才發現國內悶頭編的成百種漢語國際教材完全不適用、不管用、沒法用。劉美如院長索性根據當地學生情況自編教材出版使用。各地孔子學院積極進行“三教”實踐,涌現多種行之有效的教師培養之道。
波州大中小學漢語師資培訓主管呂麗娜長年培訓當地漢語教師,她對比當地高科技條件下教師自己做PPT智能板課件、演示觀摩為主等做法,列舉中國幾十年來教法呆板落后、課堂管理觀念陳舊等明顯差距,干脆提出,“希望中國將外派教師的培訓放在國外,在國內培訓沒用”。
有些事看起來是我幫你,其實未必不是你幫我。10月份,南卡大學“中國電影中心”揭牌。該校孔子學院看好圖書館的良好管理和數字化轉換能力,在此建立了“中國電影中心”。這事得到中國駐美大使館的高度贊同和傾力支援。
使館文化處贈送給中國電影中心700部珍貴的中國電影拷貝。南卡大學文理學院院長瑪麗安·菲茨帕特里克在年度經費減少50%的情況下,撥出15萬美元建造恒溫恒濕的膠片倉庫。她說:“電影結合藝術美學和文化,不光是電影方面師生有興趣,文理學院的教授都感覺到受益匪淺。”
大學圖書館館長托馬斯·麥克納利也說:“中國電影中心建在南卡大學只有好處。我非常高興有機會整理中國電影資料。中國電影中心的資料將來會向社會開放。現在正在做數字化轉換。轉換前,群眾可以來看,也可以巡回展映,膠片也可以復制。數字化轉換后,還可以建立網站頻道。”
對漢語來到身邊,國外許多有識之士表現出平和包容的胸懷。南卡大學英語系主任瑞文斯表示:“美國是熔爐式多民族國家。文化來自世界各地。美國對中國有各種各樣的興趣。”
南卡大學校長哈瑞斯·帕斯提德斯以“創新治校”著稱,他說:“創新必須有一個文化背景,中國歷史文化對創新性非常重要。我希望南卡能利用孔子學院,帶給南卡大學的學生一個更開闊的世界觀。”
波特州大副校長蓋爾·賴茨說得更實在具體:“中美關系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不可忽視。因為其中有誤解,會影響美中關系。不要因對文化不了解引起誤解。我們在大中小學開展領航項目,不僅僅是為了增加一門漢語教學,重要的是,對于中美雙邊關系的發展、中美世世代代永遠友好下去,都會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鼎力支持孔子學院和中國電影中心的南卡大學文理學院院長瑪麗安·菲茨帕特里克,曾熱情邀請孔子學院的中國教師觀看美式足球,在她看來,這類似于“中國人希望美國人了解京劇。”。
“有人說,美國南方的美式足球是一種宗教,所以想讓孔子學院的老師們享受一下這種感覺。比如,一個家庭全家都去,不會錯過一次比賽。比賽之前,提前4個小時在餐廳里聚會、喝酒、吃飯,是一個耗時很長的重要活動,而且是很多人在一起聚會的活動。孔子學院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來幫助我們的學生得到全球化的概念。”她說。今年11月,美國總統奧巴馬訪問中國時表示,美國近年將向中國派遣10萬留學生。
同月,在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俄羅斯總統梅德維杰夫的會談中,雙方再次申明辦好明年俄羅斯“漢語年”活動。
這并非巧合。同月,從互聯網名稱與編號分配機構(I-CANN)第36屆年會上傳來消息,該會議表決通過《“.中國”等非英文域名后綴快速通道實施計劃》,漢語網民將用中文域名無障礙上網。
12月10日,第五屆孔子學院大會也將在北京開幕。來自6個大洲的數百位孔子學院院長濟濟一堂。風云際會,四海融合,八面來風。漢語敞開平等、平和、平實的胸襟,緩緩遠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