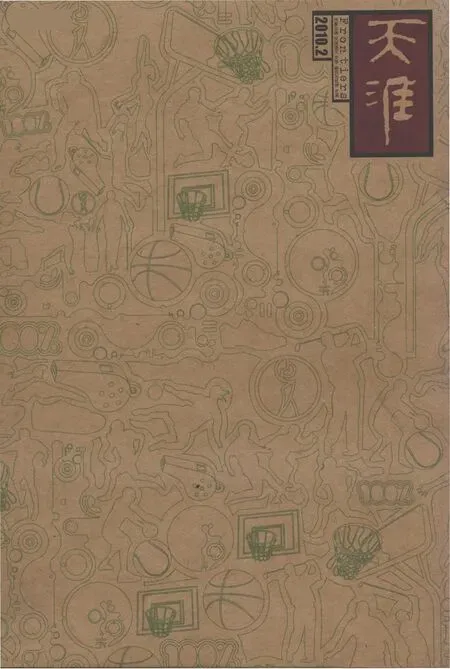侯麥眼中的中產階級女子
趙荔紅
“我喜歡這樣的兩個時間點:在晃動的光線明滅的從郊區開往巴黎的火車上,閱讀,我不喜歡看報紙,而喜歡讀書,報紙離現實太近,書卻是另一個世界,書有體積有質感,我能感覺到它與現實不一樣的存在;還有,是看車廂里的女子,自從我結婚后,我覺得所有遇到的巴黎女子都是美麗的,這并不妨礙我愛我的妻子海倫。事實上,當我偷偷贊賞地看著眼前一個陌生女子時候,我從未想過可能再遇到她,我只是愛慕她美麗的此時此刻。午后三點鐘,這也是個讓我沉溺于幻想的時間點,這時候我坐在咖啡館吃點心,窗外所有的一切都是迷人的,街道,車,人,尤其是女人。她們,孤獨的,焦慮的,心事重重的,安詳的,匆忙的,有伴侶在身邊甜蜜走過的,全都那么迷人,我幻想著和她們調情的開場白……每一天,在這個既不屬于工作,也不在家里的時間,我就心神恍惚,這個時間,只屬于我自己,連同這些美麗的女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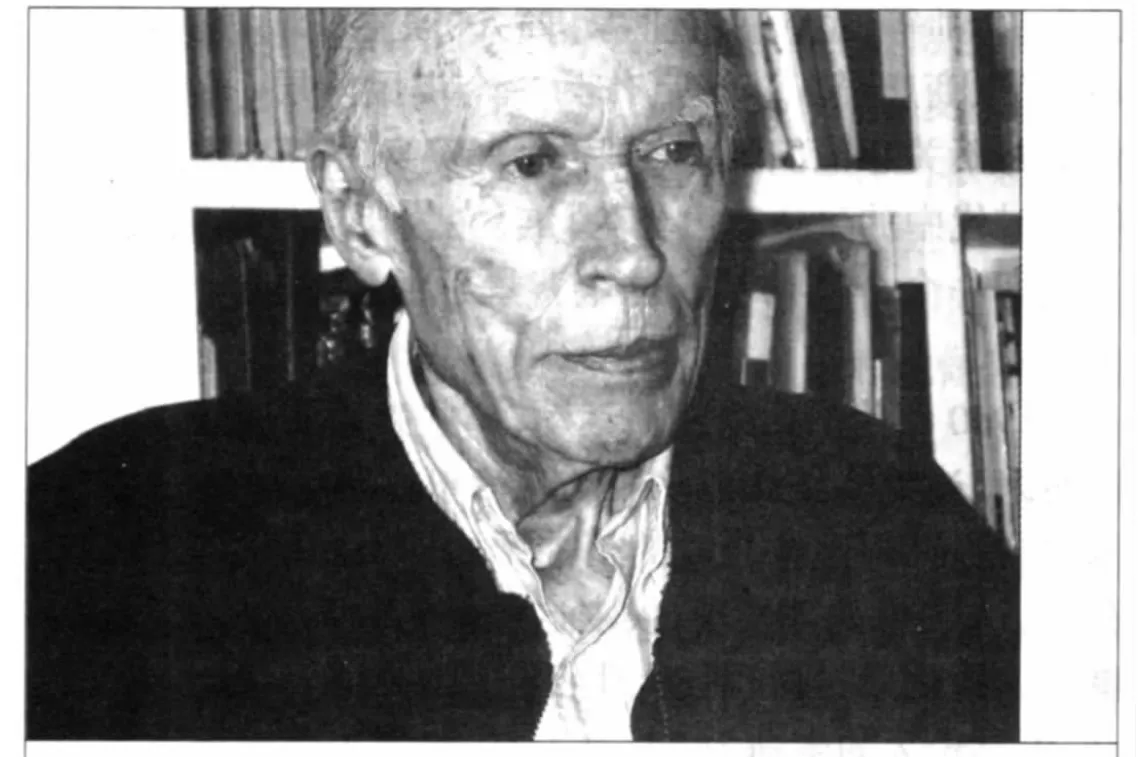
法國電影導演侯麥(1920—2010) 朱炯 攝
這個“我”是埃里克·侯麥的電影《午后之愛》中的男主人公費里德里克,一個小公司老板,優雅地憂郁著的,博學、內向、沉思的,有點保守拘謹的,猶豫不決,甚至膽怯的中產階級男子。侯麥電影中的男主人公幾乎都是這一型,或者說,他們就是侯麥自己。這個法國新浪潮五虎將之一的大導演,直到八十多歲,還拖著他極少的幾個攝影師、錄音師、演員,在巴黎街上拍攝他那些小制作低成本、色調溫情的電影。他從不高聲大氣宣揚自己的主張,也不高調在媒體出頭露面;他拍攝時,巴黎人就在街上走來走去,沒有圍觀、喧鬧,沒有人認出他,他甚至自己坐在輪椅上幫忙拍推軌鏡頭。這個出身于中產階級信奉天主教家庭的導演,似乎一生都在拍攝“同一部電影”,這些電影被認為具自傳性質。他如此固執,從不厭倦于題材和對象的重復,他說:“我很早就下定決心堅持不改,因為只要你堅持一種意念,就會有追隨者,即使發行商也一樣。”基于這個意念,他從不顧及周圍的批評、指責,諸如說他不關心歷史、政治啊,過于布爾喬亞趣味,過于自我,等等,一味將視角鎖定在巴黎及由巴黎出發延伸的外省。再沒有人比侯麥更熱愛巴黎了,巴黎的街市、風尚,巴黎人當下的生活處境,他們的道德、信仰、知識、愛情困境,被他關照著。尤其是那些巴黎女子,侯麥極其細膩地展現、分析她們的日常生活細節、捉摸不定的情感、豐富復雜的心理過程。“喜劇與諺語”系列六部,“四季”系列四部,都是以女性為敘述主體,“六個道德故事”里,敘述主體雖是男子,侯麥卻給予其中的女子相當突出的地位,或者說女子更具自主性,更讓人印象深刻。
反對變化多樣,強調導演的個人視野及獨特風格,正是新浪潮的電影美學理論。侯麥于1958年接替巴贊任《電影手冊》主編,在這個新浪潮電影理論的主陣營,發表了大量電影評論。期間,新浪潮的另一名主將,特呂弗高揚他的“作者策略”,即:導演應有自己鮮明的風格,他們比劇作者更為重要,通過“攝影機筆”,運用電影語言能夠將任何抽象觀念,像寫小說或論文一樣詮釋出來,他反對電影僅僅是改編文學作品的附庸,并在這個意義上反對傳統電影的“文學性”。實際上,侯麥電影的文學性非常之強,只不過這個文學性是導演自己“創造”的,運用的是電影語言,而非依附于文學作品。侯麥幾乎是通過電影來寫散文,傳達詩意,其結構又如小說一般精巧,他尤其重視人物對白,極盡挑剔,以能展現角色豐富多變的心理為能事。侯麥的另外一些觀點,諸如強調場面調度的真實感(不是真實性),反對片廠布景,將攝影機直接搬到大街上,采用自然光而不是復雜的打燈,長鏡頭攝影機運動,故事的開放性,喜歡群眾演員,等等,都是新浪潮的電影美學主張,侯麥一輩子用他大量的作品實踐了這些理論。但是,他卻與特呂弗一樣,被一些《電影手冊》年輕的激進分子視為新浪潮的“叛徒”,而不得不于1963年離開《電影手冊》,1968年后,更是與極左的新浪潮導演分道揚鑣。他被批評作品過于文學性,視角過于唯美,而題材又毫不涉及轟轟烈烈的六十年代西方左翼運動,不能反映時代精神。侯麥說:“我們不應該害怕現代化,……但應知如何對抗潮流。”潮流永遠只會追求更新、更左;不趨同潮流,堅持自己的風格,恰恰是新浪潮的電影美學觀。
將侯麥視為新浪潮“叛徒”的何止是當時激進的年輕人。美國影評人寶琳·凱爾就稱侯麥是“無性關系的情色主義專家”,諷刺他是“中產庸俗化”,說他“把半嚴肅半滑稽的雞毛蒜皮當成他的專長”,“自身沉溺在法國布爾喬亞的語言學中”。寶琳們大概只看到侯麥電影背景盡是沙灘、咖啡館,談論哲學文學,拿本文藝書(盧梭或帕斯卡),聽古典音樂,幾個中產階級男女在那里晃來晃去,絮絮叨叨,滿足于一些小情調、小憂郁、小別扭、小故事,而絲毫不管外面反越戰、反權威、反宗教,黑人民權問題、女性問題、環境問題,等等紛繁復雜熱血沸騰的時代聲音。的確是。但毋寧說寶琳們根本沒有體會侯麥的意圖。如果說,在《獅子星座》中,侯麥直接探討了階級問題,直接將矛盾指向“社會”,從拍攝“六個道德故事”開始,侯麥更關注的是中產階級內部,這些現代社會主流群體自身的困境,從他們最微小、最日常的生活出發,來探討他們行為的意念。這些現代都市人的無意義的疏離的生活,不安的、變動的生存狀態,他們在信仰上的困惑,情感交流的障礙,在科層化組織中的無力感,工具理性世界中的孤獨感,而未來充滿不可知的選擇,威脅感和焦慮感時刻降臨。選擇、焦慮、不可預測,這些存在主義的言辭,侯麥運用電影語言重新敘述。他所關注的中產階級,并非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內涵來考察,而是基于一種生活狀態及觀念態度,一種心靈狀態,指向極其廣大的人群,既包括作為知識分子的教師、醫生、律師等,也包括企業家、商人、雇主,以及大學生、公司職員、商店員工,等等,作為一個市民階層、一個群體,侯麥并不關心他們具體的職業、真實身份,只是將這個群體在時代中的生活態度作為社會文化背景,他更關心的是他們一個個“自我”在這個背景下的生活處境、思想意念。

《綠光》中的戴爾菲娜
1960年代的西方左翼運動,那些轟轟烈烈的,如同宣泄情緒、過集體狂歡節一般的政治事件早已過去,馬爾庫塞、薩特、福柯這些當時的精神領袖提出的問題如今依舊存在。人們回頭才發現,侯麥這些并不著眼于具體的政治事件,而刻意探討現代人生活處境的電影,似乎更有意義,更具長久的生命力。
本文僅僅著眼于以文字來重述、闡釋侯麥眼中的那些中產階級女子,事實上,侯麥電影所設計的現代“情境”多以各色中產階級女子為敘述主體展開,愛情多為敘述的“對象”,但愛情又不是僅有的對象,還有那些推動愛情的行為和言論。
成長的女性
“我喜歡一下子愛上某人的感覺。也許不是愛情,比友誼多一點。我愛的時候并不開心,甚至有點厭煩。我只是占有,呵,可怕的占有欲。……今天我很快樂,明天我可能很悲傷。”
十六歲的勞拉,在《克萊爾的膝蓋》中,對母親的朋友,一個即將結婚的外交官吉洛姆說這些話。她感覺她是一下子愛上了吉洛姆,但僅僅是一種愛上的感覺,體味一種愛的“意念”,而不是事實或行動上的愛;甚至僅僅是一種對年長的男子的依戀,一種“埃勒克特拉情結”(戀父情結)。這種思緒飄忽不定,她自己都難以肯定,令她一會開心,一會又沉浸在自我傷悲中。侯麥借著吉洛姆的目光愛憐地看著這個花季少女,對她并無男女之欲。女子的愛情,可能會因為一個詞語,一個眼神,某一種念頭忽然降臨,又因為某個小小的“事故”轉瞬消失;而男人對女人的愛,起初就是“物”的沖動,被某一個性征誘發。所以,當吉洛姆嘗試著去吻投入自己懷抱的勞拉時,勞拉迅速避開,她的愛,絲毫沒有和肉欲聯系起來,男人濕乎乎的吻只是令她厭惡,連同扎人的大胡子,都散發著動物性的味道,令她不適;對吉洛姆而言,勞拉顯然也不能激發性欲。
這樣的少女“意念”中的愛,對年長者的依戀,沖動的,輕率的,又是青澀滋味的,反復被侯麥敘述。在《秋天的故事》中,女學生羅欣對她的中學哲學老師的愛,其實是一種如夢似幻的曖昧感覺,而老師只想和她做愛。她要老師做一個選擇:“如果你只是要誘拐女學生,你就做得灑脫一些,勇敢一些,經常更換女學生,如果你是要找終身伴侶,你就要馬上選擇。”“選擇”的情境,在侯麥的電影中反復呈現,女子總是咄咄逼人,男子總是節節敗退,最后逃之夭夭。老師無從選擇,又禁不住欲念。羅欣對同齡的新男友根本無所謂,認為他沖動、粗率、不成熟,而對男友的母親瑪嘉莉,卻是“一見鐘情”。和瑪嘉莉在一起,安詳、寧靜、自然、溫暖,是模擬的母女關系,又不完全是,她無法將這種關系和依戀“歸類”。于是,羅欣天真地一廂情愿地設計出這樣一個情境:假如,她將老師和瑪嘉莉撮合在一起,她就可以放心地去愛老師,又同時擁有瑪嘉莉的愛,不必觸及“欲望”,又能保留“意念”的、純潔的或者說哲學的戀愛。
羅欣對年長老師的愛戀,依舊是“埃勒克特拉情結”;而對年長的瑪嘉莉的依戀,則如少女阿狄絲對薩福,類同于對母親的溫暖的依戀。所有青春期的少女,都會對男人的侵入及男性的占有欲、控制欲深感恐懼,對男人毛茸茸粗魯的
身體充滿本能的厭惡。正如薩福的詩歌:“像群山中的一枝風信子 /被牧人踐踏 /只剩下紫色的斑點 /殘留在地上。”這個風信子的殘破意象代表了處女之身的終結,想到“殘破”,少女們就瑟瑟發抖,一旦遭遇到比自己年長的母親型的人,她馬上轉移愛戀,渴求得到她如子宮一般溫暖的愛與庇護。羅欣單方面渴望老師與瑪嘉莉結合,這樣,她認為她的愛,就是安全的、長久的。侯麥非常細膩地體貼著少女這份隱秘的心理。
然而,少女抖抖瑟瑟與男人的交往,終于不可能躲在安全的年長者的愛護之下。風信子花早晚要被踐踏,留下點點斑斑的痕跡,伴隨苦澀的滋味。少女是在痛苦中成長為一個“女人”的。《克萊爾的膝蓋》中,吉洛姆對勞拉的“誘惑”并不動心,或者說,勞拉身上沒有誘發他沖動的性征。但是,當勞拉的姐姐、十七歲的克萊爾爬上梯子去摘紅櫻桃時,她短短的玉色裙子下,優美的腿,淺棕色、圓滑、靈巧的膝蓋與腿窩呈現著一個優美的弧度,就是這樣一節膝蓋,突然激發吉洛姆的欲望,他想去撫摸那膝蓋,想占有它。當欲望升騰,年齡就不再是面對勞拉時的借口和障礙,克萊爾僅僅是一個“女人”,一個欲望對象,膝蓋是欲望的“發動機”,連同克萊爾看人的眼神,她沒心沒肺的姿態,都讓他震動,他完全違背了自己說的不會為了欲望去接近一個女人,心心念念的,就是如何侵犯到她那塊膝蓋。克萊爾顯然與勞拉不同,她有個同齡的男友,被他撫摸,享受過年輕的觸碰的快樂,已經意識到了男女之間的“肉欲”關系。她已經不是一個躲在年長者的愛護中的女孩了。

《沙灘上的寶琳》中的寶琳與瑪麗安
然后,一旦男女性欲構成了戀愛中的主體關系時,少女就不得不承受著被誘惑、被欺騙,被傷害、被侵犯的痛楚。吉洛姆殘酷地密告克萊爾男友對她的欺騙。在風雨交加的午后,在無人的亭子中,克萊爾哭了,這時候,吉洛姆,幾乎是可鄙地,乘著克萊爾的軟弱、悲傷,被欺騙的憤怒,以一個安慰者的長者的姿態,將他的處心積慮的手,放在克萊爾的膝蓋上,溫柔地揉搓。傷心的克萊爾在這個瞬間,品嘗著男友的欺騙、背叛的苦澀、愛情的虛幻感,同時又被動地作為一具“肉體”橫呈在一個中產階級老男人不可告人的肉欲之下。克萊爾明白自己的處境,或者說,她明白,在以后的成長中,在與男人的交往中,她必將、始終不得不首先作為一個“物”或“肉體”存在,她同時也明白自己作為這個“物”的優越性,她將利用這個優越性享受對男人的占有欲和控制欲。克萊爾本能地沒有拒絕這個“手撫摸膝蓋”的侵犯,在克萊爾和吉洛姆的眼神交流中,完成了已經“長大”了的男女之間的第一次小戰爭,第一次侵犯與被侵犯,欺騙與控制。
這種現代男女之間的欺騙與控制,在《沙灘上的寶琳》中作為主題被探討。十七歲的寶琳隨離婚的表姐瑪麗安到布列塔尼海邊度假,遇到了表姐曾經的追求者彼埃爾、人類學家亨利、少年西爾維,由此發生微妙的情感糾葛。瑪麗安再一次迅速、沒腦地投入到她自己幻想的激情故事中,與亨利迅速發生性關系;彼埃爾揭發了亨利的不忠、混亂的性關系;西爾維則是一個同謀。誰在背叛誰?事情一層層被剖開,盡管所有的“在場者”都在自圓其說他的處境、思想,但是在少女寶琳那里,她體驗了一場成年人的欺騙與背叛:亨利號稱“不喜歡一個女人用這種或那種方式迫使我把她看作某種家具”,以此為自己的自由行為辯解。在寶琳眼里,他還是一個背叛者、栽贓者,一個好色而不負責任的男人;彼埃爾聲稱自己愛瑪麗安,寶琳則認為他是個被輕慢的憤怒的告密者,出于自私愿望的嫉妒者。短短一個假期,寶琳由懵懂的少女,成長為一個歷經情感磨難的女人,在以后的成長歲月中,這樣的痛苦,將在某個情境中一再發生,一再被自我消解,她無能為力,抉擇又往往不可預測。寶琳經由的是中產階級女子的必經之路,寶琳的困境,也是所有現代女性的困境。
從寶琳的角度看,她是痛苦的。但侯麥的譴責、諷刺是輕微的、克制的。他并沒有對人物作絕對的是非善惡的批判,只是著力于呈現某個情境下人們的思維狀況;他給予每個人物為其行為自我辯說的機會。侯麥電影被認為“是思想而非行動”的電影,關注的都是“道德”問題,但這個法文的moraliste,并不想游說什么道德教條,或呈現是非對錯,而只是展現想法與感情,侯麥說:“‘道德’可以指那些公開討論自己的行為動機、理由的人,他們好分析,想的比做的多。”侯麥電影中的人物,在每個情境中都構成經典的三角關系:兩男一女,兩女一男,既平衡又相互對抗。在這個關系中,對話喋喋不休展開,是對話,毋寧說是自我的內心獨白,有第二者的“傾聽”,對白得以進行下去,不至于單調;又因為第三者的“插入”,形成對抗局勢,推動情節的發展。同時,人物既是自我的敘述者,又是對方的評判者,為自己的行為和思想辨析的同時,也將自我展現在對方的眼里,侯麥將敘事者與評論者疊加在同一個角色身上。人物雖有輕重,卻不存在絕對主角,每個人都是獨立的自我。所有的思維都是“存在”的。
少女成長為女人,在《女收藏家》、《好姻緣》、《綠光》中,侯麥展現的都是年輕女人的復雜的情感和心理歷程,下文將重點敘述。到了《秋天的故事》中,四十五歲的瑪嘉莉已經走到了“秋天”。她不自信又自尊,憂慮、焦躁、自閉。但她依舊如少女一般,渴望重新“遭遇”不可預知的愛情。老侯麥在這部影片中依舊設置了這種渴望的悖論及背叛主題,但此時,他不愿如《沙灘上的寶琳》,將遺憾苦澀地呈現,他溫存地給予“秋天的”瑪嘉莉一線美好希望:誤會終將消解,內心似乎敞開,友情恢復了,愛情降臨了,自我疏離的生活有希望彌合了。但是,無論對于“春天的”少女,還是“秋天的”女人,純粹的愛情,如荒漠甘泉,是多么不可預測,多么不可靠,多么短暫,甚至,僅僅是女人的一個幻覺。
自主的女性
“我是魯道夫的情人。我還可能是尼基、肯塔、杰瑞……的女朋友,他們叫我女收藏家,收藏的是男人。阿德里安,我討厭他那種知識分子落落寡歡的樣子。他從我的窗下走過時,腳步略略遲疑,我知道他的目光會從虛掩的門游離到我的腿上。哼,這個懦夫,他為了掩蓋他的情欲,為了逃避他喜歡我,居然慫恿丹尼爾上我?好吧,這樣的話,他就必須、一定得成為我的收藏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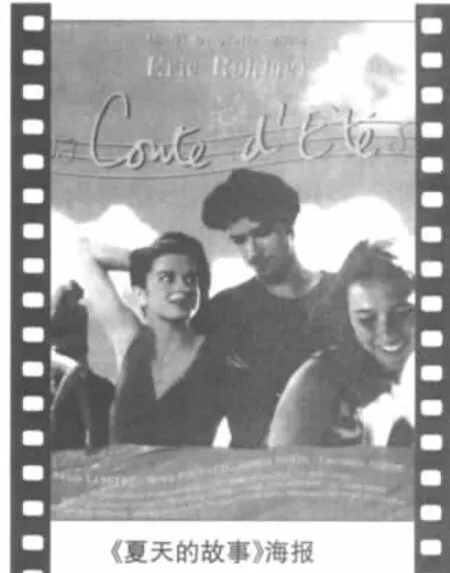


《女收藏家》的敘述主體是阿德里安,這里模擬女主人公艾德的口吻,從她的視角反觀。阿德里安無疑是想法很多,行為游移,既不能抵御艾德的誘惑,又沒有勇氣去行動。相比之下,艾德要坦蕩、自主得多。西方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瘋狂時期”開始的性解放運動,在六七十年代重新掀起,女性主義、男女平權運動如火如荼,性解放觀念螢蟲般四下飛揚。1968年的法國五月運動,甚至高喊“我們越革命,我們越做愛;我們越做愛,我們越革命”,將女性問題、性解放與政治運動聯系起來。侯麥電影雖不直接涉及政治,也間接傳達了當時的風潮。在自主的女性艾德眼中,遵循中產階級道德的阿德里安無疑是怯懦的、虛偽的。
自主、積極的女性,還有《在慕德家的一夜》里的女醫生慕德,她認為女子并非被動,而具有求愛的主動權,有分享性愛快樂的自由。當讓·路易到慕德家過圣誕節時,她好奇的是,一個恪守天主教信條的工程師面對性的誘惑,是否會放棄“不淫亂”誡命。她其實并不想與讓·路易做愛,也并不愛他,留讓·路易過夜,僅僅是設置一種情境游戲。面對兩個男人(另一個是追求她的哲學教師),她掌控著情境游戲,極盡展現美麗肉體,揮灑著她的誘惑力。讓·路易在誘惑的漩渦中掙扎,他告訴自己,追求女子不等于遠離上帝,但必須是一種愛情而非肉欲。他愛慕的是偶遇的一個金發女子,天主教徒弗朗索瓦茲,但路易也困惑,對弗朗索瓦茲的“一見鐘情”僅僅是精神的,難道沒有肉欲的成分?事實上,在慕德家一夜,他在思維上已經接受了慕德的誘惑,行為上卻猶豫不決,經歷一整夜的內心斗爭后從慕德家逃離而去。頗具諷刺和悖論的是,這個圣潔的弗朗索瓦茲竟然曾是慕德丈夫的情人。《在慕德家一夜》公映時,法國左翼運動剛剛結束,在反宗教、反權威的聲浪中,侯麥通過電影,委婉地質疑讓·路易內心的困惑與猶疑,再次將主人公放置于存在主義的“選擇”情境中。讓·路易更多的是一個“思想著”而非“行動中”的人。相比之下,慕德從思想到行動都更自主,更積極,更坦率。
侯麥電影,常常是一個沉思的、內向的、猶豫不決的男子,處于必須“選擇”的情境中,左右為難。《夏天的故事》也是如此。賈斯柏是個數學系碩士,能作曲,他到布列塔尼度假,遇到自主的“美惠三女神”——智性的瑪戈、性感的蘇蓮娜、情緒化的蒂娜時,不知如何選擇,他游離在三個女子之間,不停地改變行動計劃,和任何一個在一起時,都覺得最愛她,當三個人同時逼迫他時,他就逃之夭夭,不作選擇。有趣的是,當男子一定要作出選擇時,往往會放棄那些自主的女性,而選擇貌似被動的女子。《女收藏家》中阿德里安將惑人的艾德丟棄在路邊,駕車逃走,次日就乘飛機返回到女友身邊;《在慕德家一夜》中讓·路易逃離了富有誘惑的慕德,選擇貌似圣潔的弗朗索瓦茲;《午后之愛》中費里德里克滑行在婚外情的邊緣,從自由瘋狂的克羅伊身邊逃回到家庭中;還有《沙灘上的寶琳》中的瑪麗安,美麗性感,尋求激情的自由的愛情生活,迅速投入亨利懷抱,卻反被亨利拋棄。為什么這些自主的女性,在感情中反倒更容易受挫?
六七十年代性革命之后,女性發現,性解放并不能真正帶來男女平權,相反,倒給予男性享用性欲的好機會。女人在男女性愛之中,依舊處于屈辱、被動地位。性的解放,只會將這種屈辱、被動進一步擴大。女性并沒有獲得更多的尊重。侯麥眼中的這些自主的中產階級女子,總是處于“變動”狀態,并不落實在“家”或“居所”中:《女收藏家》中的艾德是借住在情人的別墅;《在慕德家一夜》中的慕德離了婚,所愛的人又死去了;《午后之愛》中的克羅伊居無定所,和不同的男人同居、分離;《沙灘上的寶琳》中的瑪麗安是去度假,才離婚。她們在巴黎與外省間來來去去,在道路中尋找情感的機遇。和那些被動的女子一樣,性別決定了她們也在尋求“家”的皈依感,自主是暫時的,最終渴望安居在愛情的樂園中。既然和被動的女子追求一致,那么男人,在肉欲得到滿足后,寧可選擇更牢靠、穩妥的女子作為房子里的“家具”,或許因為他們對自己駕馭情欲的能力不自信,或許是他們寧可退回到傳統規則中。這是一個悖論,男人欣賞“自主”的女性,卻逃避她們。
等待的女性
當自主性成為一個悖論時,女性只能等待。
“一些男人追求過我,他們僅僅想從我這里得到一些表面的東西,從來不會深入下去。我可能會選擇一個中意的人,處一陣子,卻令我更孤獨,每次回到和男人睡過的地方,那里的氣息令人憎恨,我只想迅速逃走。越孤獨我就越找不到滿意的人。就不斷地做夢。我只能等在那里。”
《綠光》中的戴爾菲娜在等待什么?突如其來降臨的愛情。一個真命天子。一次內心的全部敞開。一個幻夢。《綠光》這部被認為是“杰作之極致”的電影,極其細膩地寫戴爾菲娜的假期。戴爾菲娜兩年前與男友分手。假期里,她不愿呆在工作的巴黎,也不愿和家人去度假,這兩個狀態都是“社會”的、“日常生活的”。她需要一個完全的、自我的、有別于現實生活的浪漫的假期。她先跟女友一家人去瑟堡,又去曾和男友呆過的地方,再到布列塔尼海灘,她在巴黎與這些地方來回奔跑,就是為了一個完全的假期。她不斷地尋找、逃走,再尋找。始終空落落孤單一人。
侯麥設計的情境,總是發生在工作及日常生活之余的時間。《午后之戀》在從家里往巴黎的地鐵上,或午后的咖啡時間;《夏天的故事》、《綠光》、《沙灘上的寶琳》、《克萊爾的膝蓋》、《女收藏家》里的假期;《圓月映花都》里一周工作后的周五夜;《好姻緣》中正要畢業還沒工作的時候。在這些時間,主人公的行為游離于社會組織之外。當一個現代人在組織中時,他所有的行為都是被安置、被制度化、被管理的,他不必考慮該干什么、怎么干,體制和組織會替他選擇,一切只要照規程做就會井井有條;家庭(包括已穩定的同居關系)也是屬于社會組織范疇。侯麥抓住了那些游離于“組織”之外的時間點,將人物安置在特定情境中。在這些飄忽不定的、短暫的,完全屬于自己的,出離日常規范的時間中,自我悄悄復蘇。可是一個被日常規范約定慣的現代人,在屬于自我的時間中,常常忘記了自我。他的面前是一個等待填補的空白,可以自我選擇,卻不知如何選擇,選擇什么事。習慣于被安排的社會人,失去了交流的能力。一個一個“自我”,封閉、孤單,所謂的交流,僅僅停留在公共的知識、技能上,或大家熟悉的話語上。心靈不可能敞開。或者說,他們也忘記了什么是敞開的心靈,什么是本真的交流。
戴爾菲娜顯然不滿意這樣的狀況。她珍惜游離于科層化組織之外的假期,她要好好利用這個完全屬于自己的時間,過一個完全與日常生活不同的、夢想的、浪漫的、在別處的生活。但是,她似乎找不到這個感覺。她既不喜歡那些表面的技能性的娛樂活動,游泳啊,劃船啊,又不得不費勁地向那些將她視為異類的人解釋她為什么是一個素食主義者,花有生命,動物不能吃,在人群中,她得不停地辯解、解釋,渴望獲得認同。在更多的人群中,她擁有更深的孤單。她多么渴望,突然出現一個那樣的人,不必辯解,只要敞開,他就能懂得。希望縹緲如海市蜃樓,她唯有哭泣,來宣泄漫溢的悲傷。當山風搖曳郊外的林木、花草,她淚流滿面。她不知道該怎么辦,既無法獨處,也無法在人群中,她在巴黎、外省之間跑來跑去,如同沒有歸宿的鳥。
但是夢想或者就在不可預測的某地。侯麥再一次在電影中探討了某種神秘、不可知的存在。路上不時出現的黑桃皇后撲克牌,綠色的文字,都預兆著某種可能性。凡爾納小說《綠光》中講,看到綠光的人就能看懂人的內心,海邊的老太太聚在一起等待綠光,說綠光是太陽落下瞬間的最后一道光,非常短暫,極其美麗,須是天色極其晴朗時才能偶然看到,看到綠光的人會找到幸福。絕望極了的戴爾菲娜再次逃離人群,但就在火車站,她等車回巴黎的時候,一個男子坐在斜對面,他們互相對視,會心微笑……誠如法國諺語說的:“時機到來,即是鐘情之時。”于是他們一起留在那個島上,等待綠光。綠光真的顯現了,戴爾菲娜喜極大叫,淚水洶涌而出,她等到了,“觸電般不可思議像一個奇跡 /劃過我的生命里/不同于任何意義你就是綠光/如此的唯一”。
侯麥將一絲灰白的安慰給了戴爾菲娜。她所等待的綠光,是那么縹緲不可想,如同幻影,但總是一個希望。潘多拉帶到人間的,除了災難,還有希望。當我們看到微弱的希望的綠光時,心中傷感,卻時時等待。侯麥,這個拍攝《冬天的故事》已經是七十二歲的老人,和所有的女子,一起含著眼淚等待。所有愛的,都是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