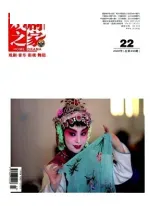談京劇的“繼承”和“創新”
□王 巖
京劇的“創新”應該在“繼承”的基礎上,不能拋開傳統,而且“創新”也不能隨心所欲地去改,應該“移步不換形”;微觀來看,每個京劇演員,絕對不能拋棄傳統戲的基礎,更不能停止學習繼承傳統戲,而且在編排新戲的同時應該不斷地回顧和反思,與前人的藝術對照,找出不同,總結經驗,吸取教訓。
要既重視繼承戲曲的優良傳統,又鼓勵發揚創造精神,強調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去創造革新。要反對對傳統不加分析的盲目崇拜,又要反對拋開傳統去動大手術另搞一套,去搞空中樓閣的“創造革新”。吳小如先生曾經說過:“作為一位改革家,首先是一位善于繼承和發展藝術遺產的人。具有高度的藝術素養,精通各種藝術技巧,并在廣而深、博而精的基礎上來進行穩扎穩打的改革,因此藝術革新才是卓有成效的。”
中國的戲曲,特別是京劇,是近代中國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戲曲藝術也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我們說繼承傳統,首先是尊重歷史,尊重歷代勞動人民的創造,尊重各個時期專家的勞動積累。這是很光榮的,而非卑下的,有些人用“亦步亦趨地模仿”這樣的貶詞來否定它是站不住腳的。京劇來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京劇里的程式都是固定的,這些程式取材于生活,但是又不同于生活,比生活中表現得更美,要更有節奏;而現在的很多新編的戲都是脫離程式,在舞臺上任意發揮,把京劇話劇化了,其實話劇舞臺上也是有程式的,新編的京劇脫離程式,就難以表現出京劇的那種寫意,把真的實物搬到臺上,那還不如去拍電視劇。離開了程式,戲曲鮮明的節奏感和歌舞性就會減弱,它的藝術個性就會模糊。
今后還是需要做好繼承傳統和創造革新兩方面的工作。繼承傳統是要付出艱辛勞動的。各種藝術創造是經過精雕細刻、千錘百煉的,并已形成獨特的藝術體系,要把它繼承下來并不是輕而易舉的。如果能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確有新的體會,高瞻遠矚地有所突破,當然應受到贊賞。如果一時水平還達不到這樣的要求,也還是可以允許的。但更應該反思、回顧,并不斷打磨,吸取失敗或者不成功的教訓才好。
突破傳統,革新創造自然是難能可貴的,這既要演員有堅實的基礎,高度的藝術修養,吃透劇本規定的人物性格及其環境,有豐富的知識,開闊的眼界,還要有善于識別精、粗、美、惡的能力和善于吸取集體的智慧。童芷苓在《宇宙鋒》演出中,通過脫帔(由下場改為當場)這一細節處理的修改加工,使這出戲更為緊湊,增加了新的表演手段,增強了對趙艷容裝瘋抗婚決心的表現。這是她作為一個有幾十年舞臺實踐經驗的成熟演員,對劇本作了透徹的分析,并具有熟練的表演技巧結出的碩果。
當然,誰都愿意成為戲曲的改革者,都想創新,編排出自己的劇目,并且受到觀眾的歡迎,可是目前的實踐證明,除了劇本本身的問題外,還有很多主觀和客觀的因素影響著創新;有些戲,由于演員善于集思廣益,跟其他演員配合得好,不斷加工修改,取得了很好的成績;有些戲則由于基本功差、粗制濫造、失掉的傳統太多,又不善于吸取經驗、不斷打磨加工,弄成“四不像”,令人看了生厭聽了刺耳,甚至演一出,丟一出。所以說京劇“創新”要緩行,不能一窩蜂地都排新戲,不能不思考,不研究,隨隨便便就排,這樣花費大量人力、物力,確實勞民傷財,而又得不到什么實際成果,一切要由時間來檢驗。廉價的勞動是難以達到真正的成效的。為此,我們必須審慎地實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評價革新創造。王瑤卿先生有一句名言,我覺得對京劇“創新”問題說得很精辟,他說:“不是改了就好,而是往好處改。”
“藝術貴在創造”,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問題是如何創新?目的和手段是不可分割的,只有重視對于傳統的借鑒和運用,恰當地加以改造融化,使之符合創新要求,這樣的創新才會符合“京劇姓京”這個要求,這樣創新取得的藝術成果,才是廣大觀眾所喜聞樂見的。反之,離開傳統去片面孤立地空談繼承“革新精神”,必然達不到真正創新的目的。“繼承”和“創新”都不能偏廢,把傳統的東西更好地保留下來,顯得尤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