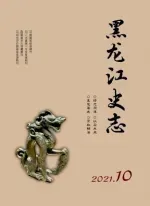陳獨秀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的貢獻、失誤及啟示
徐治彬
(浙江長征職業技術學院 基礎部 浙江 杭州 310023)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一開始,就是一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的黨,就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偉大而又曲折的歷史進程。作為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和早期主要領導人的陳獨秀,從一大到五大,均被選為中央委員,先后任中央局書記、中央局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中央總書記等職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位偉大的踐行者。他為開啟和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功不可沒。同時,由于主客觀方面的原因,在開啟和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他也有一些理論和實踐上的重大失誤和不足。我們采取歷史主義的態度,正確認識他在開啟和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方面的貢獻和失誤,對于我們今后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
陳獨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懷寧(今屬安慶市)人。陳獨秀一生思想的變化歷程,學者們多有深入研究,一般認為陳獨秀的思想大致經過早期激進民主主義、馬克思主義到后期的托派主義等幾個階段。他受舊式教育長大,處于一個多變的時代,其政治思想越來越激進。1920年當他轉向馬克思主義之后,開始創立中國共產黨和實行國共合作。在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當中,作為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的陳獨秀作用不可低估。
其一,大力傳播馬克思主義,為開啟和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理論前提。十月革命之后,陳獨秀胸中涌動著一股革命的激情,他要把他剛剛接觸到的一些革命理論,哪怕是他對這些理論的認識和理解還不甚深刻,也要急于傳授給工人群眾。1920年前后,他在《談政治》、《社會主義批評》、《馬克思學說》中宣傳了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唯物史觀、階級斗爭和勞工專政的學說,批判了無政府主義和第二國際機會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他不僅是《新青年》的創辦者和主編,而且是主要的撰稿人。從五四運動到黨成立期間,《新青年》先后刊載了100多篇介紹馬克思主義和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文章。此外,自1919年1月至5月,陳獨秀和李大釗創辦的《每周評論》,發表了大量的關于社會主義革命的報道,最先摘譯發表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在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成立前后,陳獨秀主持創辦《勞動界》、《伙友》等刊物,直接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宣傳社會主義思想。陳獨秀等人所創辦的刊物說理深入淺出,通俗易懂。他的文章被輿論界稱為“研究馬克思學說的最好的入門書”。[1](P39)
其二,積極開展黨的創建和建設工作,為開啟和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干部條件。1920年5月,陳獨秀在上海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并從研究會成員中培養建黨的骨干。在陳獨秀主持下,經過醞釀和準備,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漁陽里2號《新青年》編輯出版部正式成立,定名為“中國共產黨”。從1920年秋天到1921年上半年,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廣州等地陸續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旅日、旅法華人中的先進分子,也相繼建立了共產黨早期組織。由于陳獨秀在五四時期的重大貢獻和社會聲望,以及他在五四運動以后傳播馬克思主義中的影響尤其是他擔負了黨的最初發起者的重任,因此,當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時,在他沒有到會的情況下,仍然選舉他為中共領導機構中央局的書記。以后,直到1927年4月黨的“五大”,他一直被推選為黨的主要領導人。為加強早期黨的建設,黨制定了一系列路線、方針、政策。黨早期的路線、方針、政策實際上大多是在陳獨秀主持下制定的,其中大部分是正確的。陳獨秀以啟蒙運動的方式培養造就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一代新青年,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杰出代表。
其三,闡明了為何要和如何能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為開啟和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認識基礎和重要方法。陳獨秀認為要想馬克思主義學說能夠在中國發揮實際作用,就必須結合中國實際對其加以改造和發展。他說:“本來沒有推之萬世而皆準的真理,學說之所以可貴,不過為他能夠救濟—社會—時代弊害昭著的思想或制度。”[2](p177)在如何能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上,一是他認為要聯系時間和空間的變化來理解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我們要懂得和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復雜的錯綜的全部理論與政策,首先要懂得辯證法的時間與空間之變化性。”[3](p58)二是他認為要以一種世界的、時代的寬廣眼界來運用馬克思主義。他說:“不但要懂得本國的真實狀況即其歷史發展到了甚么階段,并且要懂得世界的真實狀況即其歷史發展到了甚么階段,更要懂得本國和所處的世界之革命的關系是什么一種形勢。懂得了這些,然后所定革命的策略及行動,才適合實際,才不至于落后或空想。”[2](p1060)否則,“口中雖說贊成世界革命,實際上仍舊是關門革命”[2](p1061)。
其四,在開啟和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產生了一些理論成果,這些成果成為形成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理論資源。一是陳獨秀對中國的基本國情有了比較正確的認識。1922年6月,陳獨秀起草的《中國共產黨對于時局的主張》指出中國是一個“半獨立的封建國家。”[4]二是陳獨秀對中國革命的性質進行了正確的闡明。由他起草的黨的“二大”文件中,文件闡明了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民主主義革命,含有對內的民主革命和對外的民族革命兩個意義,以達到民族獨立和民主政治。三是陳獨秀提出了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思想。1922年6月陳獨秀在《對于現在中國政治問題的我見》指出,中國革命不得不分為兩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資產階級對于封建軍閥之民主主義的爭斗,第二段是新起的無產階級對于資產階級之社會主義的爭斗。”[5](P185)四是初步提出并踐行了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思想。他認為,在半殖民地中國,革命的敵人是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軍閥,它們互相勾結,力量十分強大,因此中國革命必須是統一的國民運動[5](p247),其參加者是包括資產階級、無產階級以及農民、商人、學生在內的社會各階級。盡管上述這些理論成果還不十分確切、完備,但這畢竟是中國共產黨人努力“應用馬克思主義于中國國情的工作”[6](p311),其方向基本是正確的。
二
由于當時陳獨秀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中國國情缺乏深刻的認識,還沒有形成和掌握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自覺意識和科學方法,因此他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道路的探索上也具有明顯的局限性。
從方法論的層面上說,陳獨秀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方面的失誤主要表現在對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經驗采取教條化的態度,對中國傳統文化沒有采取吸收其精華、剔除其糟粕的辯證態度。
陳獨秀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方面出現失誤的根本原因就是對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經驗采取教條化的態度。他“不是注重于掌握馬克思主的立場、觀點、方法和活的靈魂,往往把它當作概念的邏輯演繹體系;不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得出符合中國實際的特殊結論,卻試圖從中國革命尋找符合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的因子。這樣既忽視了馬克思主義在運用中的民族性問題,自然不能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實踐有機地結合起來。”[7](P334)同時,陳獨秀把俄國一國革命的經驗教條化,試圖從俄國革命成功的經驗中來設想中國革命的步驟和前途。陳獨秀以俄國先在城市從事工人運動、然后再聯合起義的經驗為藍本,設計了一條“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暴動”的革命道路。大革命失敗后,他無視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農村武裝割據的戰績,頑固堅持“城市中心論”,要求黨把重點放在城市,致全力于“國民會議運動”[3](p77-82),攻擊工農紅軍是“土匪與潰兵”[3](p177),最后自絕于黨。
陳獨秀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也是不正確的。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對封建制度和以儒學為代表的傳統文化進了尖銳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動搖了封建正統思想的統治地位,這就打開了鉗制人們思想的枷鎖,起到了思想啟蒙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陳獨秀在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的時候,過分地強調了傳統文化的消極作用,而沒看到它的積極方面,因而也不可能提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問題。
在理論層面上來說,陳獨秀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方面的錯誤的最大之處和最集中的體現就是他對中國革命的領導、動力、前途的認識上存在重大缺陷,提出了“二次革命論”。
中國革命是許多階級共同參加的革命,那么究竟哪一個階級應當居于領導地位,哪一個階級是忠實可靠的同盟者呢?對于這個問題陳獨秀卻作出了錯誤的回答。1923年陳獨秀在《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中國農民問題》、《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等文章中對中國社會的階級狀況作了初步分析。通過對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階級狀況的分析,陳獨秀得出以下結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會階級固然一體幼稚,然而資產階級的力量究竟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國民運動若輕視了資產階級,是一個很大的錯誤觀念。”[5](p365-368)他認為資產階級雖然亦幼稚,但它的力量“究竟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比較起來,資產階級更有可能領導國民革命,作為國民革命運動代表的國民黨的革命“軌道”應該是“統率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產階級,實現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這場革命的結局自然是資產階級的勝利,而無產階級只有參加革命“才獲得若干自由及擴大自己能力之機會”[5](p259)。至于“共產黨奪取政權,乃是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事。”[8](p263)
根據列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理論以及該理論指導下的革命階段論,并結合自己對中國社會經濟狀況和政治狀況的分析,陳獨秀認為中國的革命分為兩段路程:民主革命階段和社會主義革命階段。陳獨秀對中國革命兩個階段的分析既符合列寧的革命階段論又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因而是正確的。但是,陳獨秀的“二次革命論”,卻偏離了列寧主義。列寧強調無產階級對民主革命的領導權,而陳獨秀大部分時間忽視了領導權;列寧認為東方國家可以跨過資本主義[9](p336),而陳獨秀卻割裂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聯系,機械地堅持中國革命必須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
在實踐層面上來說,陳獨秀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方面的失誤主要體現在他放棄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權,逐漸陷人了右傾機會主義的泥坑。
陳獨秀在立場和世界觀上并沒有由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徹底地轉向馬克思主義,在急劇變化發展的革命實踐中,他又缺乏自我改造的自覺性,看不起群眾。因此,在黨成立以后,他逐漸陷入了右傾機會主義的泥坑。具體表現在:第一,對國民黨右派叛變革命一再妥協退讓,為蔣介石的反革命活動辯護。從國民黨二大到中山艦事件再到整理黨務案,陳獨秀對國民黨右派叛變革命逐步退讓,縱容了國民黨右派的反革命行為。第二,全面放棄無產階級領導權。1926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特別會議。會議只字未提“無產階級領導權”,而且全面放棄了黨權、政權、軍權以致群眾運動的領導權。陳獨秀的報告和會議決議規定當時黨的策略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扶助汪精衛取得國民黨中央、國民政府和民眾運動的領導地位,用以制約蔣介石的軍事勢力。第三,下令解散工人糾察隊,解除農民武裝。1927年間,一些國民革命軍軍官不斷發動反革命政變,進攻武漢國民政府,收繳工人糾察隊槍械,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陳獨秀簡單地認為是工農運動的“過火”行為導致了事變的爆發。為了防止汪精衛集團右轉,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采取了一些限制工農運動的措施,下令解散工人糾察隊,解除農民武裝。第四,在革命危急時刻采取投降式的挽救措施。“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后,大革命運動遭受重大挫折。陳獨秀仍然本著維護國共合作的天真愿望,寄希望于以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中央和武漢國民政府,錯失了挽救革命的時機,最終又引發了汪蔣寧漢合流,導致大革命運動慘遭失敗。
三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日益結合的過程。“黨在幼年時期,由于理論準備和實踐經驗都不足,對于中國的歷史和社會狀況、中國革命的特點和規律不甚了解,還不善于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10](P.6)陳獨秀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探索是中國共產黨人早期對待馬克思主義不成熟的表現,這是新的理論在新的實際中產生作用的必經階段。陳獨秀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探索過程中的貢獻與失誤,對我們今后要更好地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有以下幾點啟示:一是注重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和活的靈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原理和科學精神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前提。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實踐的科學,具有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它要求我們在運用馬克思義指導實踐的過程中一定要以發展的眼光看待馬克思主義,以具體的時間、地點等條件為轉移,反對教條主義傾向。馬克思主義是人類智慧之樹上的一顆碩果,是人類知識寶庫的一枚瑰寶。無論是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恩格斯本人或馬克思主義的內在本質都反對將某種學術思想、理論尊為教義來頂禮膜拜。二是科學分析和正確把握中國國情,立足基本國情,反對“左”和右兩種錯誤傾向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客觀依據。正確認識和把握國情是考慮和解決中國問題的首要出發點,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備前提,是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基本前提。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靠背誦和機械地重復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不行,靠盲目照搬外國社會主義實踐的經驗和模式也不行,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國情出發,把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三是大力推進理論創新,在實踐中檢驗真理、發展真理,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活力源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質,不僅是要求結合中國實際去應用馬克思主義,更重要的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去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對馬克思主義進行大膽的理論創新,提出新原理、新思想、新觀點。創新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活的靈魂。四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充分維護好、實現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根本保證。離開人民群眾,離開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科學理論就將失去其真理性和指導性,變成毫無意義的東西。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條重要經驗,也是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強大動力和根本保證。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集體在理論上思想上政治上的成熟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鍵因素。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現,人民群眾和理論界都作出了重要貢獻,中國共產黨成熟的領袖們作出了杰出貢獻。沒有一批批在理論上思想上政治上成熟的領袖人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國經驗馬克思主義化是不可能實現的。六、大力弘揚中華文化,把馬克思主義根置于中國的優秀文化之中,是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化底蘊。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它是在民族發展的長河中形成并發揚光大的,又是在長期的與各個國家的文化交流、融合的過程中相互吸收、相互借鑒而發展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既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照搬,也不是對中國文化的復制,而是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文化中的優秀成分結合進而達到融合。在這個過程中,就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對中國文化進行認真的清理,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華。
[1][美]莫里斯·邁斯納.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M].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
[2]陳獨秀著作選:第2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3]陳獨秀著作選:第3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4]陳獨秀.中國共產黨對于時局的主張:第9號[J].先驅,1922-06-12.
[5]陳獨秀文章選編:中冊[M].北京:三聯書店,1984.
[6]瞿秋白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7]何一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專題研究[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8]陳獨秀文章選編:下冊[M].北京:三聯書店,1984.
[9]列寧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2009年修訂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