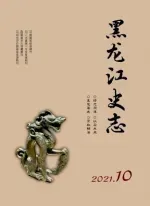法家思想對現代企業管理的啟示
童康勝
(青海師范大學法商學院 青海 西寧 810008)
一、法家思想概況
1.社會背景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社會出現了巨大的社會變革。首先,在經濟生活方面,以奴隸占有式的剝削方式,逐漸地被封建的地租剝削方式所取代;其次,在政治格局方面,舊的宗法等級制度被無情打破,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第三,社會結構亦發生重大變化,新興地主階級的政治、經濟力量日益強大,舊的血緣貴族日益沒落。代表新興的生產方式和社會關系的地主階級成為了社會的主導力量。
這種社會的深刻變化,正是先秦諸學派學術思想產生發展的社會基礎。法家是戰國時期興起的一個學術派別,其思想之源可追溯的更早。該學派以力主“依法治國”的“法治”而得名,其理論的哲學前提是“趨利避害”的人性論。他們的社會基礎是由非貴族的平民通過各種途徑上升為土地所有者的新興地主階級組成的。法家思想的基本特色是“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漢書·藝文志》)。
2.代表人物
法家的代表人物大多是戰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思想家。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戰國初期的李悝、吳起,中期的商鞅、慎到、申不害,末期的韓非、李斯。法家的思想淵源可以上溯到春秋時期的管仲、子產。
3.主要思想
①法家的“法治”說
法家所提出的“法治”口號,即所謂的“依法治國”,最早是由《管子》提出的,又稱“垂法而治”(《商君書·壹言》)。以“法”作為治理國家、統一天下的主要方法,這是法家思想的核心。依法治國,對外關系到國家的國際地位,“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韓非子·有度》);對內關系到君主統治地位的鞏固,“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法審則上尊而不侵”(《韓非子·有度》)。
為了保證法治的預期目的的實現,韓非提出了刑法的實施原則。首先,君主必須獨操刑罰大權,“威不貸錯,制不共門”。這樣,就能保證法為君主服務的功利性。其次,君主必須維護法的客觀性和權威性,“法不阿貴”、“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能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非子·有度》),這與儒家“刑不上大夫”的政法觀念相比,無疑有著極大的進步。
②法家的“術治”說
在先秦法家中,申不害一派以重“術”而著稱。在如何實施“法治”的問題上,提出了著名的“術治”說,其所謂的“術”,即權術,具體是指維護君主專治必須具有一套駕馭臣下的“君人南面之術”,才能使臣下忠于職守,嚴格地遵守法令。他認為靠正確的法令就足以治理好國家。因此,法令的地位非常重要,“君之所以尊者,令。令不行,是無君也。故明君慎令。”(《慎子》佚文)另外,申不害一派還主張君主應依靠法令而不用自己的個人智慧,也就是“圣君任法而不任智”。與此同時應嚴格區分名分的差別,將之作為區分君臣的政治標準和駕馭臣下的手段。“術”大致有兩方面的內容:一是任免、監督、考核臣下之術。“術者,因任而受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君臣之能者也。”(《韓非子·定法》)二是駕馭臣下之術。“術者,藏于之胸中,以潛御群臣者也”(《韓非子·難三》)。
③法家的“勢治”說
所謂“勢”,即權勢,勢并非單獨存在,而要依法。而法要借勢,法與勢是相互依托的,沒有法何以保證勢,沒有權勢法又不能順利貫徹執行。韓非關于“勢”的思想比慎到更前進一步,表現在其“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韓非子·難勢》)的法勢相結合的思想。
二、法家思想與現代企業管理的聯系
法家所講的“勢”是行法用術的必要條件,并貫穿于行法用術之中;反之,法和術是勢的具體表現。因此法、術、勢三者是密切結合,不可分離的。這在《韓非子·難勢》篇中有過論述。他主張依法治國、用術御臣、以勢制人。韓非這種對法術勢三者之間辯證關系的見解,是他對前期法家思想的發展,也是他法治理論的核心。
在現代企業管理中也要一方面有良好完善的管理制度,即法家所講的“法”;另一方面也需要領導者的合適的管理方法,即法家所講的“術”。再好的制度沒有領導者的領導藝術也不能很好的貫徹執行。而良好的領導藝術沒有完善的制度也是空中樓閣。將法家思想中的法術勢有機的結合并有機地運用到現代企業管理中去,可以使企業得到更好的發展,在市場競爭中處于更有利的地位。
三、現代企業管理概況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經濟水平得到很大提高。這得益于我國企業實力的進一步上升。與此同時,企業的管理水平和管理經驗都有明顯提升。許多著名的企業在轉換經營體制的同時逐步形成了自己獨有的且卓有成效的管理方法。但隨著對外開放程度的加深及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中國現代企業管理中的不足亦逐漸顯現,主要有體制、人力資源及領導者素質幾方面的原因。
四、法家思想對現代企業管理的啟示
1.對體制方面的影響
中國企業管理的發展不同于西方企業管理的發展,比起西方企業管理產生時間短、規模小。中國企業的體制和管理受政治和文化的雙重制約,文化上主要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在很多程度上“人治”管理現象嚴重存在。中國歷來重禮教輕法治,重感情而不重制度,因而管理者僅憑個人喜好辦事的現象嚴重存在。領導人的個人權威越大,對企業生存與發展的影響也越大。這往往導致領導的決策代替了企業的制度,使企業的命運維系在一個人身上,加大了企業經營的風險。
韓非子曰:“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強,奉法者弱則國弱。”(《韓非子·有度》)這強調了法律制度對一個國家的重要影響。同樣,對于一個企業來講,企業要生存、發展也需要有一套完整的規章制度。包括企業的經營責任制度、技術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勞動制度、分配制度、財務制度、物資管理制度等內容。“治法之至明者,任數不任人”(《韓非子·制分》),說明國家的治理依靠的是明確的法律條文,而不是依靠一兩個人才。從企業來講只有依靠嚴格、明確、規范的規章制度來管理,才能使其成為一個統一、規整的組織。
2.對人力資源方面的影響
人力資源是現代企業最為重要的資源。人才作為科學的管理理念和技術的載體,是企業經營不可或缺的。
現代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曾說過:“企業只有一項真正的資源——人,管理就是充分開發人力資源以做好工作。”
韓非指出,君主治國不能放棄法術而憑主觀臆斷,施行賞罰不能沒有法制而根據主觀好惡。“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在《韓非子·八經》中韓非還說:“明主之道取于任,賢于官。”這指出高明的領導者其用人之道,應該是錄用有才能的人,讓有德有才的人去擔任各種管理職務。
法家思想中對人才的主要考核方法是循名責實,具體講就是要依下屬的職務去追究其應有的功效、業績,以下屬的言論去衡量他所做的事和所取得的功效是否與其言論相一致。現代企業管理的實踐中亦存在對員工的工作考核,雖然內容和手段不斷革新、完善,但實質仍未變,它所發揮的“擇優選能”、“獎勤罰懶”的激勵效用將會在當今人力資源管理實踐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3.對領導者素質方面的影響
《韓非子·主道》篇體現了法家“君道無為,臣道有為”的思想。君主要順應客觀形勢推行法治,讓臣下貢獻出自己的才能去建功立業。“明君無為于上,群臣悚懼乎下。”(《韓非子·主道》)這說明了領導者無為而治的重要性,所謂“虛靜無為”并不是指無所作為,而是在用人過程中,通過充分授權,最大限度地調動和發揮下屬的智慧、能力,而不必親力親為、事無巨細。“皆用其能,上乃無事。”說的是成功的領導者的領導藝術,是無為而治,而權勢卻都掌握在手中。
韓非子認為,領導者在管理企業時不應逞用自己的才能,而應依據法度,這樣才能使下級各展其能,達到企業治理的目的。否則,如果領導者逞強好勝、展露才華,下級就會利用這點進行欺騙,這樣企業就難以治理了。所以他認為,領導者的作用在于無為,不表現自己的好惡,而下級的作用在于依法辦事。這就是“上有所長,事乃不方。”(《韓非子·揚權》)
五、結語
針對我國企業管理中剛性管理不足的現象,法家的法治思想給了我們很好的啟示。作為先秦時期的一個學術派別,法家思想有著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其思想中不乏對現代企業管理有益之處。一方面針對領導者自身心性中的本質、動機及想法,提出了應對策略;另一方面,則提供被領導者的常情心態,以利建立有效的管理機制,制訂法律法規,構筑治理藍圖。這些對當今企業管理亦很有借鑒意義。
[1]張覺.韓非子校注[M].岳麓書社,2006:1.
[2]陳東升.《韓非子》與中國式管理[M].企業管理出版社,2006:1
[3]武樹臣,李力.法家思想與法家精神[M].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7:1.
[4]張一弛.人力資源管理教程[M].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1.
[5]曹軍.法家的法術管理-領導者的權與勢[M].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7:1.
[6]紀寶成.中國古代治國通論[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1.
[7]楊玲.中和與絕對的抗衡-先秦法家思想比較研究[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1.
[8]楊伍栓.管理哲學新論[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1.
[9]徐從根,陸鵬.法家思想的現在管理之道[J].北方經貿,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