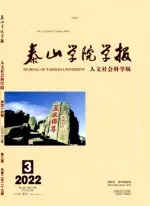中國文化中的“暴力”傾向
劉 凌
(泰山學院漢語言文學院,山東泰安 271021)
古今中外,均盛稱中國自古“熱愛和平”。確實,中國外侵,即非絕無,也是少有。成吉思汗及其子孫的鐵蹄,雖曾踏遍歐亞大地,但我們卻可辯稱,他們是“非我族類”,盡管毛澤東在《詠雪》詞中頌其為“英雄”。即使想征服外國,也大多主張“講信修睦”、“修文德以來之”。以至有人批評中國對外過于“文弱”。大約,作為一個自給自足的食稻(谷)民族,它既無擴張的沖動,也無擴張的能力吧。
然而,對內還能否這樣說呢?
關于“武”的字義,人們每稱“止戈為武”,并由此判定傳統文化的反戰傾向。但這尚需具體分析。楊伯峻先生指出:甲骨文中“武”字實乃“象人持戈以行”[1]。足見最早的“武”字,是“持戈”,而非“止戈”。本字何時演變為“止戈”字形,難以確考。“止戈為武”釋義,始見于《春秋左傳》宣公十二年。文稱:楚莊王大敗晉師,大臣請求“收晉尸以為京觀”,即積尸封土以示眾;而莊王未許,并以“止戈為武”開示。其語云:“非爾所知也。夫文(指“武”字——引者),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罪無所(犯),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顯而易見,他是在談“武”的最終目標和個人理想,而并非給“武”下定義。既然晉國已降,也無大罪,其人民又都能為晉國君盡忠獻身,我們又何必要積尸示眾呢?這不過是表示楚王的悲憫心腸和寬大為懷罷了。實際上,“止戈為武”只是楚王的個人解釋,并非“武”字的基本含義。人們更多的是把“武”理解為“力”、“勇”、“伐”、“勘定”、“刑之大者”[2],也即視為一種強力征服手段,此有眾多辭書釋義為證。
中國古代軍事文化發達,已為舉世公認。據統計,古有兵書三千部,留存者也有三四百部,真可謂舉世無雙。《孫子兵法》研究,則已成國際顯學。常言說:“實踐出真知”。任何理論,無不從實踐中來。這如許兵書,實乃建立在無數血腥戰爭之上,而非從“和諧”中來。研究《孫子兵法》的專家李零估計:僅戰國四次大戰,即殺人百萬;山東六國爭戰,約死傷四百萬,完全是“世界大戰”水平[3]。可見,《孫子兵法》一類兵書,實為數百萬人的鮮血所澆灌。以此而論,兵法發達,既是我們的驕傲,也是吾邦的悲哀。而《財富論》闕如,則令人不無遺憾。
中國古代,號稱“憲章文武”,“各隨時而用”;而且是“制勝御人,其歸一揆”(《舊唐書·魏元忠傳》)。可見,統治者從來沒忘過“武”也即“暴力”。《鹖冠子·近迭》還有“人道先兵”之論。齊魯“八主”之祠,其中就有“兵主”之祠。孔夫子是講過“焉用殺”(《論語·顏淵》)一類話。但他也主張“君子懷刑”(《論語·里仁》)和“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左傳·昭公二十年》),這“刑”和“猛”,就都與“暴力”有關。宋代理學家邵雍,也稱“文武之道,皆吾家事”(《文武吟》)。孝文帝《講武詔》謂:“文武之道,自古并行,威福之施,必稽往籍。故三五至仁,尚有征伐之事,夏殷明睿,未舍兵甲之行。然則天下雖平,忘戰者殆,不教民戰,可謂棄之。”(《魏書·孝文紀》下)可見,歷代統治者并未實行過“止戈為武”。
所謂“止戰”、“尚同”、“勝殘”、“去殺”、“慎刑”一類主張,不過是缺啥吆喝啥,對好戰濫殺力圖矯正罷了。但吆喝終究解決不了現實問題,濫殺終難制止住。我們的老祖宗黃帝,就殘酷得很,一點也不“和平”。他討伐蚩尤,活捉對手。為了警告作亂者,竟把蚩尤的皮剝下來,做成箭靶;把他的頭發剪下來,做成旌旗;把他的胃掏出來,做成蹴鞠;把他的骨肉剁爛,做成肉醬(馬王堆帛書《經·正亂》)。有人或辯稱,此乃不可靠的傳說。而夏、商時代的驚天酷刑,什么“刑辟”、“炮烙”、“脯鄂侯”、“剖比干”,可是史有明載的吧?后來,又花樣翻新,什么“抽腸”、“剝皮”、“凌遲”無所不用其極。中國的刑訊逼供,也是有名的。“請君入甕”的故事,就是一例。
已如前述,產生《孫子兵法》前后的時代戰亂頻仍,殺人無數,后來又如何呢?據有人統計,從秦皇統一,到 1951年,2171年中,戰亂就占了一半時間。歷朝歷代,都有“峰火連天”、“白骨蔽野”的記述。漢朝號稱“盛世”,但劉、呂權爭,劉姓內斗,以及株連臣民,竟至殺人如麻[4]。歷代殺戮,既有官殺民,也有民殺官,還有官殺官,民殺民,等等。其中或偶有“戰以止戰”之戰,“殺以止殺”之殺,但大多數卻是主動搶奪“權”、“利”之戰之殺。就是正統史書,也承認“春秋無義戰”呢。即使是止戰之戰,也不應坑殺降卒,而在中國卻司空見慣。秦趙長平之戰,秦將白啟就坑殺趙降卒四十萬。漢王莽攻破翟義之后,竟也夷其三族,誅其種嗣,至皆同坑 (《漢書·翟方進傳》)。據統計,自秦漢至明清共有皇帝 209人,被殺和被逼自殺的有 65人,約占三分之一;南北朝有皇帝 48個,被殺和被迫自殺的竟有 28個[5]。
無論朝野,均時有刺殺、劫持等恐怖活動,甚至被當作英雄行為歌頌。自古迄今,暴力執法和暴力抗法,不絕如縷。歷代農民起義,也未能避免濫殺。太平天國是古代規模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向有極高評價。然而,其暴力濫殺也創下紀錄。那位號稱被“天父”附體、代“天父”傳言的精神領袖楊秀清,就是一位暴力濫殺大王。他往往以“天父”名義審判、殺人,或斬首,或五馬分尸,或點天燈。他甚至“傳言”說:“凡東王打我們一班弟妹,亦是要(我們)好;枷我們一班弟妹,亦是要(我們)好;殺我們一班弟妹,亦是要 (我們)好!”似乎暴力濫殺具有了天然合理性。[6]現代農民革命和民粹式民主,也充斥暴力濫用,從斗地主到斗“走資派”、“學術權威”無不如此。那場以“文化”命名的大“革命”,盡管有“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還是動用了棍棒刀槍。在民間關系中,也每每靠拳頭爭老大,話不投機,即拔刀亮劍,伸拳擼胳膊。民眾對劍俠、武功和奇招暗器的推崇迷醉,當今大中學生對戰史、兵器的喜好,軍事文學的熱銷,青少年對暴力游戲的熱衷沉迷,無不表現出暴力崇拜。從古至今,家庭暴力不斷,而且往往發生在文人之家。
既然是“以暴力最強者說了算”,必然形成“搶到天下是王,搶不到天下是賊”、“成者為王敗者寇”的歷史觀。就象帕斯卡爾所說:“人們既然不能使服從正義成為強大,于是他們就使得服從強力成為了正義”[7]。斯大林所謂“勝利者不接受審判”[8],也是這種邏輯。
此種邏輯,乃至波及詩詞歌詠和詞語構建。岳飛《滿江紅》詞,竟以“饑餐胡虜肉”和“渴飲匈奴血”喻其“壯志”。江湖義氣,救人急難,被稱為“兩肋插刀”、“拔刀相助”。《史記·平準書》“以武斷于鄉曲”語司馬貞索隱稱:“謂鄉曲豪富無官位,而以威勢主斷曲直,故曰‘武斷’也。”凡此,都在崇信踐行“持戈為武”,“以暴力最強者說了算”,又何“和平”之有?俗諺云:“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其實是根本不讓你“說”。這充分反映了理性法則面對暴力法則的弱勢。
確實,“暴力”主宰話語權,“以威勢主斷曲直”,象一個幽靈,一直在中華大地游蕩。誰有暴力,誰就壟斷了真理。孔子以思想言論罪誅少正卯,儒學信徒多曲意維護。孟子將楊墨之“道”,誣為“率獸食人之道”(《孟子·滕文公》);荀子希望對“奸言”給予“勢以臨之”、“刑以禁之”(《荀子·正名)的懲罰;韓非則力主“禁心”、“禁言”(《韓非子·說疑》),“燔詩書而明法令”(《韓非子·和氏》)。古往今來,有多少人,因言獲罪,肝腦涂地啊!革命家也未能免俗。陳獨秀倡揚白話文時就主張:“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9]此種心態,實乃伴隨整個革命進程,故有鄧拓“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的詩句。時至今日,在最為“自由”、“平等”的網絡論壇和博客里,又有多少話語暴力啊!
“和平”、“和諧”是人類夢寐以求的理想,當然應大力提倡。問題是,中國幾千年,普遍存在過“和諧”嗎?海峽兩岸雖然政治制度有異,但文化根系卻多有相似。臺灣那種民粹式民主,就動輒訴諸暴力;連議會討論也時有拳打腳踢。所以,切勿以老祖宗提倡過“和為貴”,就以為我們的文化充滿“和諧”。我們而今重提“和諧”,不恰恰因為現實中有過多的不“和諧”嗎?
愚以為,在萬千論“武”(戰)言論中,惟“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克勞塞維茨)一語最為精辟。換句話說:戰爭就是從政治失序處開始。人類如能平等協商利益分配,在此基礎上構建公平合理的社會秩序,就不會有暴力和戰爭。然而,人們卻往往不愿或不會協商,轉而迷信暴力,視其為解決利益沖突的最佳或最后手段。這也是武俠小說常常表現的復仇兇殺、冤冤相報的社會根源。春秋戰國恰是個政治無序時代,必然峰煙四起,權謀聯翩。劉向《戰國策敘錄》即謂:戰國“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故孟子、孫卿儒士之士棄捐于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于俗。”荀子為戰國之后設計了“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荀子·王制》)的政治秩序。但由于由少數人主宰利益分配權,王權確定等級秩序和利益分配,各利益群體就很難“相兼臨(制約)”。生產關系和利益格局的調整,最終只有通過武力和戰爭。在某種意義上,戰爭的頻繁,暴力的泛濫,恰恰彰顯出政治的無能。對內的強橫,對外的文弱,又必然產生聯外打內、“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梟雄。因此,決不可對中國王權文官政治及其影響估計過高。
但不管怎么說,中國兵法謀略,確實豐富了中外軍事學寶庫,并換取了無數軍戰、商戰的勝利,煥發了文藝情采。它還催生出古代哲學,尤其是樸素辯證法。對此,兩岸學者都有精辟論述[10]。是的,兵道乃“詭道”,“兵以詐立”,西方文化也承認這一原理,至謂“暴力與欺詐在戰爭是兩種主要的美德”(霍布斯《利維坦》),“在戰爭行為中,欺詐卻是值得稱贊和光榮的”(馬基雅維里《論利瓦伊的 <羅馬史 >》)。但中國兵法畢竟捷足先登,而且發揮到極至。
然而,物極必有返。吾邦兵法的繁榮,也造成了“天地間無往而非兵也”(魏源)的濫用。這種濫用,首先表現于權力斗爭。政治游戲,本應公開透明,按游戲規則來玩,光明正大,君子動口不動手。但中國古代,卻是政不厭詐,政不離武,充斥陰謀詭計和暴力;王權更迭,也罕見和平過渡,而多是“馬上得天下”。后晉節度史安重榮一語道破:“王侯將相寧有種耶?兵強馬壯者為之爾。”(《新五代史·安重榮傳》)此與李逵“殺到東京去,奪了鳥位”,是一個思路。改朝換代,何時不充滿刀光劍影?“打天下,坐天下”,成為歷代統治者執政模式和執政心理。
宮廷權爭,也充滿陰狠詭詐、刀劍血腥,甚至君臣、父子、兄弟相殘,血案迭起。僅《春秋》一書記載,在紀元前 722至 481年的 242年間,臣弒君的事件就有 100多起。例如,齊悼公在周敬王三十一年 (前 489年)繼位,在齊悼公四年 (前 485年)被殺,在位僅僅四年。他的兒子壬繼位,是為齊簡公。頗為巧合的是,這位齊簡公也和他父親一樣,只做了四年皇帝,也被謀殺。殺手就是相國田常。而楚成王則死于兒子之手。根源在于兄弟爭權。成王偏愛長子商臣,宣布立其為太子,讓潘崇做他的老師。但成王后來又喜歡上商臣的庶弟王子職,便想改立王子職為繼承人。商臣確證這一消息后,勃然大怒。他在潘崇策劃下,發動宮廷兵變,扔給成王一條束帶,逼父親自縊身亡。晉獻公的兒子們,也上演過爭權丑劇。晉獻公原來確立申生為太子,為麗姬所妒恨。她想讓自己生的小兒子奚齊繼位,便誣告申生投毒謀害獻公,重耳、夷吾也參與其事。結果,逼申生自殺,重耳、夷吾出逃。周襄王元年 (前 651年)九月,晉獻公病死于宮中。他臨終托付大臣荀息輔佐小兒子奚齊作皇帝。然而,十四歲的奚齊卻在服喪的草廬中被大臣里克等人謀殺。荀息再立悼子為君,結果又被忠于重耳的里克等人殺死。荀息自殺身亡。里克得手后迎重耳回國就位,重耳不就,改立夷吾為君,是為晉惠公。其實,不僅春秋時代如此,其后的年代里,以詐術、暴力奪權的事例史不絕書。[11]在權爭中,王莽四個兒子,有三個被他殺死,唯一的侄子也無幸免。南朝宋文帝死于兒子劉劭之手,不久劉劭又被兄弟劉駿攻殺,劉駿又殺害其弟劉誕等。劉駿共有28子,竟被劉彧殺了 16個,被后廢帝殺掉 12個,一無善終。同室相殘,其酷如此!唐代玄武門之變,更是典型的兵不厭詐,和殺兄、害弟、逼父的殘酷表演。而李世民大權在握后,卻又大批“文不如武”,大講“文治”與“和平”了。歷代君王,無不以詐術治臣,使群臣生活在“伴君如伴虎”的恐懼之中。白居易有詩慨嘆:“君不見,左納言,右納史,朝承恩,暮賜死?行路難,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復間。”(《太行路》)
可見軍事暴力對王權是柄雙刃劍,既可為奪權掃清道路,也能傷及自身。為防不測,自趙宋之后,往往采取“以文制武”政策。然而,由于暴力與政治難以剝離,“以文制武”終要通過“以武制武”施行。歷朝歷代,最大的“文”也即“王”,無不以抓取“武”也即軍權為指歸。這就帶來政治、政爭、權力交接的詭秘、恐怖和不穩定。
確如馬克思所說,在封建社會,由于不以交換為中介,對剩余勞動的占有,往往以“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暴力統治為基礎”[12];在歐洲封建地產形成發展過程中,“起作用的往往是,而且仿佛主要是政治手段、暴力和欺詐”[13]。這話也完全適用于中國。洛克認為:“誰企圖將另一個人置于自己的絕對權力之下,誰就同那人處于戰爭狀態”;“凡是圖謀奴役我的人,便使他自己同我處于戰爭狀態”[14]。中國古代的極權奴役政治,必然使人際關系處于戰爭和“冷戰”狀態,“一個個象烏眼雞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集權專制,又激發出權力者最卑鄙的情欲,將人類最真純的情愫包括天倫之情扼殺盡凈。所以,洛克指明:“專制權力”,決不能“純潔人的氣質和糾正人性的劣根性”[15]。“仁”、“義”、“禮”、“智”、“信”的倡導與呼喚,只能是軟弱無力的的矯正和抗爭。
其實,這種兵謀詐術的濫用,又何止于王權爭斗,也滲透于仕宦縉紳之家的內部關系。父子算計,姑嫂斗法,兄弟鬩于墻,比比皆是。號稱封建百科全書的《紅樓夢》,對此就有淋漓盡致的揭示。榮寧二府上下人等未必都讀過《孫子》,但其斗智斗勇,大可為兵法作注。魏源將天地間之“兵”經由“道”溯源于“情”,但“情”卻變化萬端。大觀園中少男少女的情感“戰爭”,也不乏“兵法”運用,正可謂“情不厭詐”。在平民階層,也信奉踐行“知人知面不知心”,“見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多留個心眼”,“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一類人生準則,從而形成國人城府極深的人格特征。此也是“兵不厭詐”文化熏陶的結果。
孟德斯鳩和洛克都認為:一個正當的立憲政府擁有解決分歧的能力,無需訴諸武力;市民社會是一種和平狀態,政府仲裁和法律是和平解決爭端的工具;公民之間正當自衛權利,無須攻擊別人(見《政府論》、《論法的精神》)。蘇格拉底曾謂:專制潛主“總要挑起一些戰爭,好讓人民需要一個領袖”(柏拉圖《國家》)。霍布斯也說過:專制主義的國王和主權者,“始終是互相猜忌的,并保持著斗劍的狀態和姿勢”(《利維坦》)。這大概就是洛克所論之“理性法則”和“暴力法則”的對立吧。
正是市民社會和憲政的缺乏,才使中國長期處于戰爭和準戰爭狀態。種種“止戰”、“去殺”、“和為貴”的倡導,不過是力圖改革現實的烏托邦罷了。當然,社會也需要烏托邦,它們能成為批判、矯正現實的武器,并給人以希望。但要讓理想成為現實,必須有相應制度安排。否則,烏托邦就可能成為一種自我麻醉,將主張混同于文化現實,從而回避現實矛盾和時代任務。
這里必須指出,筆者稱中國文化存在暴力傾向,并非說其他文化就沒有這一傾向,也并不否認必要暴力的積極作用。恩格斯說得好:“只要有利益相互對立、相互沖突和社會地位不同的階級存在,階級之間的戰爭就不會熄滅。”[16]馬克思甚至還說:“暴力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17]我這里所說的暴力傾向,是指由于缺乏平等、權利和協商、妥協機制,充斥在整個社會生活中的暴力解決方式。
破除“中國自古和平、和諧”的神話,教育國人尤其是執政者,尊重每個人的合法權益,學會平等政治協商,不以暴力相脅迫,并做出相應制度安排,是否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以及政治改革的緊迫任務呢?
(本文為給美國華裔學者林中明《斌心雕龍》所寫書評的一部分,今次發表略有增刪)
[1]楊伯峻.春秋左傳注 (第 2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1:744.
[2]宗富邦,陳士鐃,蕭海波.故訓匯纂[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1182.
[3]李零.兵以詐立[M].北京:中華書局,2007:90.
[4]資中筠.君王殺人知多少 [N].文匯讀書周報, 2005-03-04.
[5]常力生.御座血 [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 2008:337.
[6]帕斯卡爾.沉思錄[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141.
[7]尼·費德林.我所接觸的中蘇領導人[M].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35.
[8]龔鵬程.近代思潮與人物 [M].北京:中華書局, 2007:145.
[9]李澤厚.孫老韓合說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何丙棣.中國思想史上一項基本的翻案[A].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有關《孫子》《老子》的三篇考證[Z].2002.
[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6卷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40.
[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542.
[12][13]洛克.政府論 (下篇)[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14]恩格斯.去年十二月法國無產者相對消極的真正原因[A].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08.
[15]馬克思.所謂原始積累[A].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