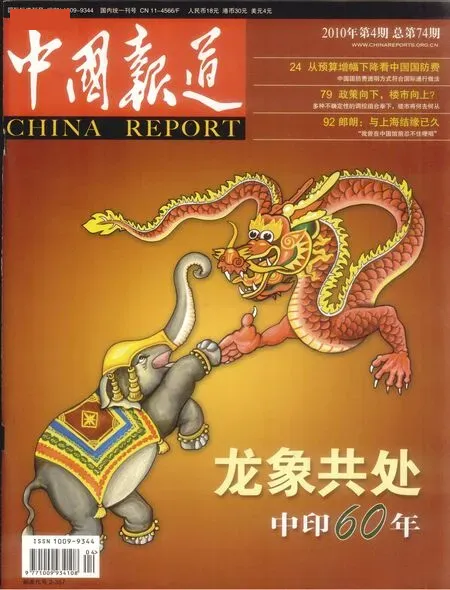見證澳門風云的詩家馬萬祺
口述 馬萬祺 采寫 本刊特約記者 余瑋
我從上世紀40年代到澳門,至今已有60多年了,其間澳門經歷了幾多滄桑,幾多坎坷,我離不開澳門,澳門也需要我。
在北京貴賓樓,記者見到了這位精神矍鑠、溫和儒雅的“澳門老人”。意外的是,老人的國語比記者想象的要流利,盡管采訪過程中仍不免有個別詞語聽不太清楚,但每遇這種情況,老人便會認真地取出筆來將記者聽不懂的話寫在紙上。盡管已步入耄耋高齡,老人的思路依然很清晰,他向記者講起了他的澳門往事……
從香港到澳門
1919年12月12日,我出生在廣東省南海縣南岸村。父親40歲才有我,在為我取名時他想到,亂世中的人們渴望有一個和平環境,使百姓能休養生息,恢復經濟,國泰民安,而《詩經·大雅·行葦》有“壽考維祺”句,《荀子》有“儼然壯然祺然”句,父親就給我起乳名“阿祺”好了,學名為“萬祺”。
我滿月后,母親卻因患了乳瘡不能哺乳。因為沒有奶吃,我腸胃不適應稀粥米糊這類食品,身體并不強壯。母親十分疼愛我,經過多位朋友介紹請奶媽喂奶,直到我會行走了才離開奶媽。對于這位奶媽的哺乳之恩,我長大成年之后沒有忘記,經常接濟她家人的生活,并幫助她至終老。
5歲半那年,我便入學接受啟蒙教育。在學社里我年紀最小,可每當老師叫背書我都能背出來,很受老師的喜愛。在學社里學《三字經》、《四書》這些古文,為我打下了一定的中文基礎。7歲時,我進入本村“民眾學校”讀小學二年級。在這所新學校里,我學會了珠算和算術,還接觸到了打倒列強、打倒軍閥的愛國思想,我最先學會唱的一支歌是《打倒列強》。
1929年夏,我讀完初小3年后便考入南海中學附屬高級小學五年級。1931年秋,我考入南海中學。南海中學一向以教書育人的優秀成績而蜚聲南粵。我入學的第一堂課便是由老師帶領新同學去校展覽室參觀校史。
開學不到20天,“九一八”事變爆發,整個中國都籠罩在濃重的民族危機與救亡咆哮中,南海中學的全體師生也組織了游行示威,抑不住心頭怒火,我也加入到示威游行的行列。站在廣州市西門口和河南同福路的商店門口的椅子上,因激動而小臉漲紅的我向路過的行人大聲演講。我還隨南海中學宣傳隊,沿著廣三鐵路向佛山、三水進發,每到一地就向當地的老百姓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
我后來曾8次回過母校,到校園里這里走走,那里瞧瞧,對母校有份深厚的感情。我曾對南海中學負責人說,要抓好德才教育,提倡新式教育方式,要做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中華民族重教育的優良傳統不能變,特別是愛國主義精神不能變。

1934年是我最不幸的一年,也是我一生事業追求發生突然轉變的一年。這一年8月,父親突發腦溢血而辭世。當時,我剛參加初二結業式,正懷抱將來進入大學繼續深造,為振興中華發揮更大作用的雄心壯志。南岸馬氏家族的馬合成堂的全部財政經營一向由父親負責。現在父親突然病故,幾位叔伯都認為我為人忠厚肯干,希望我繼承父業管理馬合成堂的財產物業。而我認為自己年紀尚小,缺乏經商和管理物業財政經驗,恐怕不能勝任。如果繼續升學直到大學畢業,將要花費8年時光。于是,我選擇去廣州公民學校上學——學校以教古典文學為主,也教授珠算會計等,是一所培養商業人才的學校。后來,我還跟隨其他學校的幾位國文老師學習賦詩填詞。
1936年底,我開始真正涉足商場。我為人隨和,商運通順,在大是大非面前涇渭分明,堅持原則。
1938年,中國抗日戰場先后取得了平型關、臺兒莊等戰役的勝利,這些消息鼓舞著我,于是我便與一些朋友相約去延安參加抗大。到了約定起程的時間卻不見聯絡人員來,我們才知道韶關的聯絡站被敵人破壞了,就沒有實現赴延安的愿望。
這一年廣州淪陷時,我經營的信興、信棧、升平、升昌、永和興等糧食、土產批發商行被日軍炸毀燒光。這時,我并沒有悲觀消極,我知道紅軍長征的偉績,寄予厚望。我在廣州淪陷后避居香港,成立泰生行和永裕昌行。1941年12月,日寇鐵蹄踏進香港,我創下的一點基業被日寇掠奪,所幸的是,我因處理商務滯留澳門,免遭戰禍。
香港淪陷后,我又移居澳門。從此,我再也沒有離開過澳門。到澳門后,我開始在這里拓展事業,先后在澳門組建了恒豐裕行、和生行、大豐銀號等公司。就在事業日漸興盛之時,我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作為中國人在澳門這塊自己的土地上并不是真正的主人。1948年,我加入了澳門最大的民間組織中華總商會。在澳門回歸以前,總商會一度是澳門各界人士從殖民統治者手中爭取權益的代言人。作為中華總商會的負責人之一,在維護澳門工商界正當權益的時候,我總是站在最前面。
我第一次到北京參加國慶慶祝活動,是在1954年。那是共和國成立5周年,我以港澳代表團副團長的身份在天安門觀禮臺觀看盛大游行,晚上還同10多萬群眾一起,在天安門廣場跳舞觀煙花。我長期不能釋懷的是,澳門當時還沒有回到祖國的懷抱。
我向中央建議澳門一定要駐軍
“蓮花喜愛艷陽天,安定繁榮美景妍,祖國關懷恩義重,前途似錦眾心堅。”這是我寫的一首詩,也是我對澳門回歸以來的總結。1999年12月20日,當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次跨境,威風凜凜地站在受殖民統治百年的澳門土地上時,10多萬居民自發地夾道歡迎,場面熱烈,不知多少澳門人為此流下了激動的淚水。
但許多人不知道,早在澳門即將回歸的動議之前,葡萄牙政府在與中國政府的談判中提出,多年來葡方在澳門沒有駐軍,中方也不能駐軍。當時中方一位談判人員認同葡方這一意見。我獲悉這一消息后,立即向新華社澳門分社(即現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聯絡辦公室)負責人表達強烈意見,請即向中央反映,非常堅決要求在澳門駐軍——駐軍反映國家主權,你沒有駐軍,有什么事情怎么辦,無論多無論少,一定得有駐軍,這是國家主權問題。
中央接到我對澳門必須駐軍的意見后,經過一段時間詳細研究,新華社澳門分社便轉告我,中央同意我的意見,“一定在澳門駐軍,請放心”。事后證明,中央駐軍澳門的決策與我的看法是相同的。
1998年9月18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錢其琛代表中國政府宣布,根據澳門基本法規定,澳門回歸后,中央人民政府將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派駐適量、精干的軍隊。對此,葡萄牙政府一再強調近20年來葡在澳門沒有駐軍,并表示,葡方知道中方駐軍的新立場時間太短,葡方將以其他方式考慮中國政府未來在澳門履行國防職責的提議。
針對葡方的態度,中國政府做了大量細致的工作,1999年6月28日,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0次會議通過“澳門駐軍法”,使葡方的態度有所轉變。10月,江澤民主席訪問葡萄牙時,葡萄牙總統桑帕約表示,愿同中方一道合力解決過渡期遺留的問題。兩國最高領導人達成的政治共識,推動了駐軍具體問題的加快解決。
1999年5月15日,澳門選舉產生了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人選——何厚鏵。投票結束后,會場內經久不息的掌聲似乎至今仍回蕩在我的耳旁。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呀!我們澳門人自己選出了領導人。400多年了,澳門經歷了127任葡萄牙任命的葡人總督,占澳門人口96%以上的華人不僅沒有任何選擇的權利,更絲毫沒有參與的權利。結束殖民統治是澳門絕大多數居民百年來的期盼。
同年12月20日,駐澳部隊進入澳門開始履行澳門防務職責。這是近400年來,駐軍澳門的第一支中國軍隊。
澳門回歸前,治安狀況很不好,社會上常有打打殺殺、綁架的事情發生,很多有錢人不敢在澳門逗留,有條件的家庭紛紛把子女送到國外讀書。很多工商界人士都想離開澳門,有些人想投資也不敢來,大家對社會治安狀況一度很悲觀。澳門回歸以后,治安好了很多,整個社會環境平靜、安寧。有駐澳部隊做堅強后盾,對黑幫和犯罪分子是強大的威懾,澳門的治安警察也更有膽量,腰板更硬了。
我從上世紀40年代到澳門,至今已有60多年了,其間澳門經歷了幾多滄桑,幾多坎坷,我為什么不到其他地方去,對澳門始終不離不棄呢?幾十年來,澳門的很多社團是由我負責的,如教育、體育、中華總商會等工作,實在是離不開。我離不開澳門,澳門也需要我。我幾十年來所做的這些工作也說不上有什么成就,只是心存愛國愛澳之心,做一些有益于國家、有益于人民的事。
我與葉劍英和鄧小平
我大兒子馬有建、二兒子馬有恒小學畢業后都被送到內地學習。1965年,馬有建在西安冶金學院畢業后被分配到北京首鋼工作。1967年,“文革”風暴席卷中國,葉劍英為了保護馬有恒,讓他住在家中,并叫他不要外出,惹來麻煩,并常叫馬有建到他家居住,對我的兩個兒子關心照顧有如子侄。
1967年,為了感激葉帥對我兩個兒子的照顧,我來到北京拜謁葉帥。我是“文革”開始以來較早去拜訪葉劍英的僑胞友人。當時,已是71歲高齡的葉帥邁著大步在寓所迎接我。葉帥對我談起“文革”的無政府主義現況,感慨萬分,但他還是充滿信心:“我們中國有句古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現在不報,時辰未到。”說罷,葉帥淡淡地笑了。葉帥希望我在澳門、香港做好團結工作,消除“文革”在海外的影響,告訴海外僑胞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對港澳和海外僑胞的關心和愛護。此后,我每年都來內地,看望葉帥等友人。

2005年,馬萬祺(右)和董建華在北京出席全國“兩會”
1978年“五一”勞動節前夕,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宴請華僑和港澳同胞的代表,我被邀請出席。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港澳同胞和海外華人華僑代表招待會由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政協主席的鄧小平先生主持。在人民大會堂幾千人的晚宴上,我有幸被安排坐在剛剛復出的鄧小平先生旁邊。那是他第一次和我談話,我感到很親切。他談到國家當時的情況和未來的發展計劃時,他希望港澳同胞和海外華人華僑團結起來,共同參加祖國的建設。我很贊成。我認為,我們一方面要繼承中國的優良傳統,總結成功和挫折的經驗與教訓,另一方面,吸收和借鑒外來好的經驗與技術,還要多引進科技人才。我的意見得到許多與會者的贊同。鄧小平先生十分重視搞好經濟,說明他非常有眼光。
我和鄧小平先生的交往后來日益增多。鄧小平先生平易近人,不擺架子。我們兩家人一直保持著友誼,我們的下一代也都是很好的朋友。在我眼里,鄧小平先生不僅是一個老朋友,更是一位偉人。
愛詩詞不愛煙酒
熟悉我的人都曉得,我愛寫詩詞。早在1931年,在廣州公民學校學習過程中,素喜國文的我就喜愛駢文詞句的精煉。
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沖進“總統府”,宣告南京的解放。我聞訊,興奮異常,夜不能寐,曾賦詩言志:“聞道大軍過長江,雄師勇猛世無雙。滔滔天塹等閑渡,楚楚南都旦夕亡。簞食壺漿迎解放,佳肴旨酒慶重光。倒懸已解人歡暢,殲盡頑軍早建邦。”
1998年12月20日,矗立在天安門廣場的澳門回歸倒計時牌揭幕時,我十分激動,曾當場即興賦詩一首:“卜燈屈指報佳期,告慰神州父老知。歷史廣場分秒顯,慈懷計日慶相依。”在澳門回歸這一舉世矚目的特殊時刻,我剛剛參加完澳門政權交接儀式,激動難抑,填過詞《調寄臨江仙》:“四百余年長盼望,澳門今喜回歸。普天同慶賀佳期,神州歌盛事,國土盡朝暉。領袖親臨情萬丈,五洲賓客增輝。政權交接紀威儀,光榮留史冊,媽閣展雄姿。”
大家都說,詩言志,詞詠情。我寫的每一首詩詞都記錄了我的親見親聞,都是有真實的感受才真情流露的。我的詩詞既是人生感觸的抒寫,也是歷史風云的記錄。 或抒情,或言志,或感時,或記事,或贊美祖國江山的壯麗,或有贈與至愛親朋。


1990年7月,澳門中華詩詞學會宣告成立,首次會員大會上,大家推選我為名譽會長。
前些年,夫人羅柏心因病離世。1943年1月,我們結婚、成家。婚后,我們盡管歷經風霜雨雪,但始終夫妻恩愛如初,相敬如賓,愛國思想忠貞不渝,服務社會熱情高漲。我和夫人志同道合,在思想上、立場上都是一致的。她和我一樣,有正義感、愛祖國、愛澳門,全身心投入婦女工作,促進澳門平穩過渡。她照顧家庭,關心我的健康,教育孩子,什么嗜好也沒有,什么要求也沒有。我們相濡以沫,其間不知經歷了多少人生困苦,但我們始終并肩而行。她走了,我一直懷念她。
讓我知足的是,我擁有一個美滿幸福的大家庭,孩子都是學有所長,事業有成,熱心服務社會。我向來重視對兒孫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我常告誡自己及子女切不可忘記坎坷苦難,必須向有困難者伸出援助之手;同時要“施己慎勿忘,施人慎勿記”。為國為民為社會而疏財仗義,是我為人的宗旨。
我對生活始終保持一種樂觀的態度,生活很有條理,心情開朗,不吸煙,不喝酒,以前打打太極拳,散散步,現在只是看看書,寫寫詩,看看孫兒,會會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