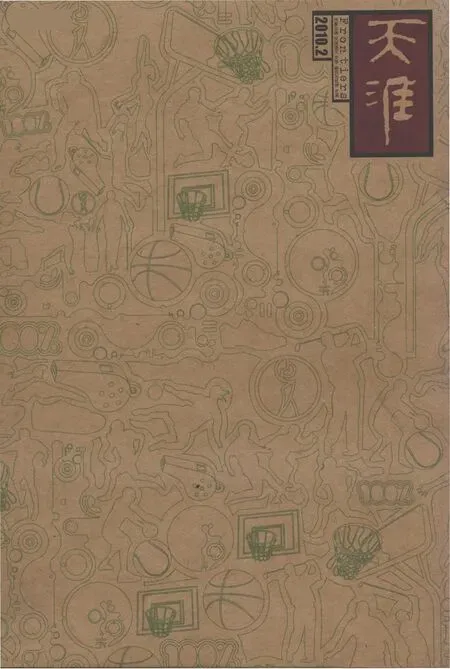離親淚
楊瑞霞
離親淚
楊瑞霞
2007年的今天,也是一個這么陰冷的日子。父親在老家縣醫(yī)院內(nèi)科病房去世。享年八十歲。
大雪與冬至兩個節(jié)氣之間的日子,陰氣盛極,陽氣衰微。今年的這幾天我開車出去,在縣城和鄉(xiāng)村又都看到了正在辦喪事的人家。
在我的記憶里,父親去世前的那次住院,是他一生里的第二次住院。第一次是兩年前,因為腦梗塞,在縣醫(yī)院住了五天院。出院第二天,他早晨自己起床,洗了臉,刮了胡子,出了屋門去拉開了院門的插銷。我在他身后跟隨著他,用數(shù)碼相機拍了一張他向門外張望的背影,然后,他回到屋里,見我拿著相機,他整了整衣領(lǐng),面對著我,我又給他拍了一張半身像。父親總是鄭重地對待每次照相。后來就是這張照片做了父親的遺像。這一點,當(dāng)時我和父親都沒有想到。
在我印象里,第一次看見父親輸液,是在十四年前,那年他六十六歲。那也讓我第一次意識到父親竟然也會生病,關(guān)于這一點,小父親一歲的我媽不這么認(rèn)為,她說他這一輩子從沒斷了那些粘乎病,比如說,他有從我奶奶那兒遺傳來的高血壓,高壓時常超過180;他中年時還腿疼過好幾年,還有他常年愛犯“胃潰瘍”。父親身高一米八七,瘦高,醫(yī)書上說,這是典型的胃潰瘍體征。
去年的八月份,天氣最熱的時候父親摔斷了腳踝。后來,父親去世后,我從一本書上看到,像他那樣高齡的人若是摔掉了腿,一般情形下是過不去半年的。果然,父親是在四個半月后走的。只是當(dāng)時我不知道,那其實是一道神的預(yù)言,提醒著我與父親即將到來的分離。
父親摔傷后,家里的保姆給大哥打了電話,大哥和幾個朋友從縣城過來,把父親搬上車,到鎮(zhèn)醫(yī)院拍了片,然后打上了石膏。等我趕回去,父親指著打了石膏的腿給我看,一臉無辜、委屈而又茫然不解的神情。
我媽告訴我說,我父親腿上的石膏要四十多天才能剝掉,她擔(dān)心到時候他就再也下不了床,走不了路了。我媽腦中風(fēng)已經(jīng)十多年,偏癱了十多年,每天在床頭坐著。但這不妨礙她在家里的每件事上都有自己的主張,而且一定要把自己的主張堅持到底。她說,她已經(jīng)打聽好了,在離我們那個鎮(zhèn)子六七十里的地方,有一家人有祖?zhèn)鞯膶V蔚驌p傷的絕技,骨折的人敷上他家的藥二十四小時就能下地走路。她一定要我去買那個藥,給我父親用。
為了滿足我媽的心愿,我開車去了那個診所,買回了藥,很沉的一坨,很濃的鮮姜和香油的味道,還有一些絲絲縷縷的東西。藥買了,可是要砸了父親腿上的石膏才能敷,誰能保證取下石膏父親的腿不亂動,斷骨不錯位呢,大哥說:“胡鬧!”我媽也不再說什么,最后我把花四百元錢買來的藥給扔了。
那次斷腿后,父親的身體狀態(tài)每況愈下,其實在此之前那幾年,由于小腦蔞縮,他已有老年癡呆的癥狀,也不怎么會說話了,但他依然能記著那些他以為很重要的事情。每年的臘月二十三,他要一個人走到集市上,買一包祭灶的糖瓜和一塊錢一掛的那種最小的小鞭炮,留著過年時給我兒子大衛(wèi),這個習(xí)慣他從大衛(wèi)出生時開始,一直沿續(xù)到前年,大衛(wèi)已經(jīng)是個身高一米八二的大學(xué)生了。如果他還能活下去,我相信,他還會每年給外孫買糖瓜和小鞭炮,哪怕他的外孫已娶妻生子。
父親還會很細(xì)心地把木頭劈成木柈,把大哥買來的大塊煤砸成小塊,他把爐子里的火燒得很勻很透,在上午十點就熬上中午喝的大米粥。他把他的百靈鳥也喂得很歡實,在鳥籠里跳上跳下地叫。
在那個已經(jīng)有些破敗的,建于五十年代的老鐵路家屬院里,像我這樣的孩子們一茬茬大了,像鳥一樣飛走了。和父親一輩的人們,有的去世了,有的跟孩子搬走了。而父親和母親一直留在那兒,過著他們過了一輩子的環(huán)保生活。年齡越大越像兩棵無法移植的老樹。在我看來,父親是離了那兒的地氣無法存活,而我媽是擔(dān)心離開了那兒便再也過不了她自己想過的日子。于是他們幾乎成了那里的“最后的守望者”。
四十天以后,父親腿上的石膏被剝掉,骨折的地方長好了,只是腳踝有一些歪。正像我媽預(yù)言的那樣,就是從那會兒起,他再也下不了床,走不了路了。不但這樣,他的大腦也似乎完全進(jìn)入了混沌狀態(tài)。我回家時,我媽問父親,你認(rèn)識她嗎?這是誰啊?父親的眼睛像嬰兒的眼睛一樣專注而茫然的久久地看著我的臉,然后點點頭,那是一種慣性的客套。父親對每一個走進(jìn)家門來看他的人都以這樣的方式表示他的感謝,唯獨對前來給他輸液的鎮(zhèn)醫(yī)院的吳醫(yī)生表現(xiàn)出極大的憤怒,每當(dāng)吳醫(yī)生一進(jìn)門,父親便瞪起眼睛,端起他的大手,做準(zhǔn)備打人狀,以此嚇唬吳醫(yī)生,讓她快點離開,否則他就不客氣了。
在此之前,父親的生活還可以自理。這時已完全需要照顧,喂水喂藥喂飯。保姆當(dāng)著我們的面給他換成人紙尿褲,他也像個剛出生的嬰兒一樣隨人擺布。這在以前是絕對不被他允許的,他一輩子是個特別在意自己的人,在女兒面前會避諱很多的事情。這時,他的老與病,他的癡呆,已經(jīng)讓他保護(hù)不了自己的隱私了。
那時的父親大部分時間是處于一種無知無覺的狀態(tài)里。在陪他的有限的時間里,我一直希望他能真正的明白過來,哪怕只有一會兒,以他父親的身份給我一些表示,雖然他一輩子都不善于語言表達(dá),而且早已經(jīng)說不了話了,但我還是希望他用眼神或者手勢給我一個明示或者囑咐,給我一個只有我和他的父女之間的交流。
沒有。
即使在他神智稍好一點的時候,他依然不認(rèn)識他的兒女,似乎他也不關(guān)心你是誰,他只是在急切地尋找一件東西,用手比劃著一個長方形的東西,啊啊的,用眼神問你,哪去了?它在哪兒?沒人知道他要找什么,他便焦急地用手拍他的大腿。咳——
讓人無限郁悶。
我多想知道,父親,在他的一生中到底曾經(jīng)丟失了什么重要的東西,以至于讓他在垂暮之年,用僅存的一點意識,如此執(zhí)著地苦苦地尋找。
夏天的一個晚上,七點多,我和保姆把父親和我媽都收拾好,他們在那張大床上,一個在東頭,一個在西頭,睡著了。兩人中間隔著一堆小褥子舊被單之類的零碎東西。保姆回自己家了,我一個人拿一個小板凳在院子里坐著。窗前的石榴樹死了,它是大哥二十來歲時栽的,已經(jīng)三十多年了,今年春天沒有發(fā)芽。我記得,在那棵石榴樹的下面曾經(jīng)有過一個魚缸,是個大瓦盆,里面有父親養(yǎng)的七條大金魚,墨龍睛,紅頂虎頭,似乎它們還在游,魚缸的下面是我媽種的繡球花,而那時他們還年輕……
我很無望地坐在那兒,屋里是兩個殘敗、孱弱的生命,這般無奈而無力的人生晚景,讓我的心里充滿哀傷和悲涼。一個念頭浮現(xiàn)出來,父親,與其這樣活著,或許倒不如早一點解脫得好。而這個念頭又是那么讓我害怕,淚水一滴滴地流了下來。
其實我們都知道,生老病死是人生的一個必然過程,這樣的事在這個世界上每天每時都在發(fā)生著,我們覺得自己已經(jīng)可以坦然面對,但實際情況卻并非如此,事到臨頭,我們依然很難相信自己的父母會離開,從來到這個世界的第一天起,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有他們的,怎么會沒有了呢?那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議的、不可能發(fā)生的事情,所以無論我們覺得自己做好了怎樣充分的思想準(zhǔn)備,當(dāng)這一天真的到來時,還是會覺得突然。
冬天來了。
立冬后的某一天,晚上我接到家里保姆的電話,她說,父親從早晨開始昏睡,整整一天不吃不喝,怎么也叫不醒。
第二天一大早,天還未大亮,我從車庫里把車倒出來,打開車的大燈,開始往家的方向開。城市的路燈還在亮著,有霧,但不是很大,出城不久,霧越來越濃,車窗外一片迷蒙,霧氣像乳汁一樣流動著包圍著車子,什么也看不見。我小心地慢慢地開出幾十里路。妹妹打來電話,說她已坐火車從北京趕回來,半夜到家,把帶來的一顆安宮牛黃丸用溫水化了,一點點給父親喂了下去。喂完后,天也快亮了,父親睜開眼睛了。她說,今天有大霧,姐你別開車過來了。我停下了車,車前和車后是一樣的大霧。我已經(jīng)回不去了。
幸虧那幾年那條路跑得很熟了。
中午到了家,父親的狀態(tài)和平時差不多,眼睛睜開了,但只是斜著往窗戶那邊有光亮的方向看。鎮(zhèn)醫(yī)院的醫(yī)生給輸上了治腦梗的藥。我們給保姆多加了一份工資,讓她丈夫也過來幫忙。父親雖然瘦,但身材太高大,骨架沉,每次翻身、擦洗、換紙尿褲,都得二三個人才挪得動。
第二天下午,我有事要回去,保姆給父親身后堆上被子,扶他倚著坐一會兒,我和他告別,他沒有任何反應(yīng),我舉了下手里的包,說,爸,我走了,過兩天再回來看你。父親像被突然驚醒的嬰孩,點了下頭,還抬了下手,臉上還好像有一絲謙卑的不好意思的表情。
很快,時令過了冬至,父親陷入了最后一次長達(dá)十一天的昏睡,再也沒有醒過來。
我和二哥、妹妹都從外地趕回了家。我們聚集在那兩間平房里。父親睡在里屋的大床上,還像平常一樣,他個子太高,而床的長度不夠,于是在床邊加一把椅子,椅子上放兩個枕頭。他已經(jīng)這樣睡了一輩子。
如果我們不去探究什么,如果我們愿意有意去逃避即將發(fā)生的不幸,父親的昏迷,其實在我們看來,更像是一場酣睡。那持久、有力而勻稱的鼾聲。是我們從小就聽?wèi)T了的,不但熟悉,還帶給我們安全感。
在我們兒時的記憶里,在很多很多年里,在那些無數(shù)的白天和黑夜里,父親經(jīng)常是這樣的酣睡,因為他在鐵路上三班倒,搬道岔,一班十二個小時,不能有絲毫的懈怠,所以他上夜班前要睡足覺,下了夜班要補覺。作為鐵路職工子弟,我們在很小的時候,就知道父親在睡覺,不能打擾。六七歲時我們就已經(jīng)會拎著飯盒去給父親送飯。長大后我曾問過父親,嗜睡的他,是怎樣在那間小扳道房里熬過那些漫漫長夜的?父親說,困了,就用手?jǐn)Q自己大腿。三十年的扳道生涯,沒出過一次差錯,更不用說事故,這是父親一生的自豪,而同時睡覺也成了他一生中最幸福的事。
父親已經(jīng)酣睡了四天,鼾聲依然長而有力。到家后第一天,我讓老家的朋友幫忙請來了縣醫(yī)院的腦系科主任,劉醫(yī)生看過,說病人這是又一次大面積腦梗塞,接下來就會發(fā)生水腫,會出現(xiàn)腦疝和并發(fā)癥,在家用些藥維持著吧,不用送醫(yī)院了,別折騰老人了。
此時,我們能做的只有等待,但那一刻又似乎永遠(yuǎn)都不可能到來。在家的第四天晚上,二哥給我們做了手搟面,用白菜和豬肉打鹵,很快家里彌漫著往日熟悉的味道,仿佛一切又回到了從前,某一天,媽媽做好了飯,我們放學(xué)回來,父親也睡醒了,全家人一起吃飯……
第五天,父親依然在睡,鼾聲的力度沒有絲毫的減弱,這來自于他依然有力的心臟,而大腦卻已經(jīng)被堵得亂七八糟了。但他的鼾聲和睡相,總給我們一種錯覺,仿佛他隨時會醒來,于是我們陷入不安,會不會是我們沒有盡力,如果把父親送去搶救,是否會有奇跡出現(xiàn)。假如有些事情我們該做而沒有去做,日后會不會因為懊悔而無法放下?
而我最不能面對的還有我媽那幾乎是帶有乞求的眼神,雖然看到孩子們都很辛苦,她不再自作主張,但每一分每一秒,她似乎都在問:“送醫(yī)院吧,把你爸送醫(yī)院啊?”我不能告訴她,我是多么不愿意讓父親在外面去世,而不是死在他最留戀的家里;我又不能告訴她,一旦父親出了這個房門,她將再也見不到他了。我說,媽,我爸一輩子最聽你的話,你讓他起來吧,別睡了……我媽說,他是一輩子聽我的話,可這回不聽了。我說,媽,醫(yī)生說了,我爸就算搶救過來,也是植物人了。我媽說,搶救過來你們就給我拉回家來,我用餅干蘸著水喂他……
“送爸爸去醫(yī)院吧!”我說。
120來了,鄰居們過來幫忙。父親被擔(dān)架抬出家門。妹妹和二哥跟著上了救護(hù)車。我開車跟在后面,車上坐著妹妹的兒子,我的小外甥,他從小是跟著姥爺姥姥長大的。家里只剩下了我媽和保姆。
縣醫(yī)院這些年沒有多大變化。從前邊的門診樓到后面的住院部,還是要通過那條狹長陰暗、地面高低不平的走廊。十幾年前我媽腦出血住院時,我曾走過很多次,后來它還曾幾次在我的惡夢中出現(xiàn)過。這一次又走進(jìn)它,感覺它像某個電影中的情景,類似于兩段劇情之間的鋪墊,讓你從生活的正面過渡到背面,從人生的一種常態(tài)走向另一種非常態(tài)。
經(jīng)過一番忙亂,父親的CT檢查結(jié)果出來了,和之前劉醫(yī)生的判斷一樣,父親這次是大面積腦梗,而且是在腦主干部位。我去交了押金,主治醫(yī)生給開了很多藥,有治療的也有營養(yǎng)的,整整一天都在不停地輸液。晚上我和二哥留下來守護(hù)父親。
縣醫(yī)院的住院部人滿為患,只有八人間的大病房還有張床。1床是個八十五歲的心臟病患者,老頭以平均每半個小時一次的頻率不停地折騰著他六十多歲的兒子,一會兒“尿尿——”一會兒“不尿——”。6床是個剛患上腦栓塞的七十歲老太太,一只胳膊不能動,半夜里她想把溜下去的被子重新蓋到身上,卻發(fā)現(xiàn)自己無論如何也做不到,便大聲咒罵她睡得死死的孫子,我過去幫她把被子蓋好。
夜深了,白天像集市一樣的住院部安靜了許多。好人病人都要睡覺。日光燈整夜地亮著,空氣很混濁。有人在夢里呻吟,還有大約四個人在高低起伏地打著鼾,其中父親的聲音最大最有力。
在此之前我的那些尋常日子里,我是不會去想有些人的有些夜晚是這樣度過的。這會兒我才知道以前我那些平淡安詳、心無掛礙的夜晚是多么值得感激。
下午有病人出院了,父親的病床旁有了張空床,我和二哥分別側(cè)身躺在床的一邊,都無法入睡。夜里二點多,我去外面停車場找到我的車,從后備箱里拿出一瓶老白干,然后敲開小賣部的門,買了火腿腸和咸鴨蛋,和二哥用水杯喝了些白酒。二哥喝了酒,睡著了。我依然沒有一點困意。一邊照看父親,一邊看索甲仁波切著的那本《西藏生死書》,我想了解一些關(guān)于生命的生與死的真相。書上說,我們可以把人的整個存在分成四個實相:此生、臨終和死亡、死后、再生。而“中陰”是指:“一個情境的完成”和“另一個情境的開始”兩者之間的“過渡”與“間隔”,我想知道父親此刻正行走在人生的哪一個階段,我該怎樣去幫助他,書上還說,接近死亡,可以帶來真正的覺醒和生命觀的改變。那么我又該怎樣去面對這生命中必然要發(fā)生的事情,并獲得心靈上的解脫……在那個夜晚,我才知道關(guān)于生命的真相,我和很多人一樣,有太多的不了解,并且缺少準(zhǔn)備,所以當(dāng)生命中的完美之相被打破,殘缺即將來臨時,才會有那么深的困惑和無奈。
父親住院的第三天,昏睡的狀態(tài)沒有改變。醫(yī)生的用藥量每天都在遞減。由于長時間仰臥,又一直在輸液、吸氧、導(dǎo)尿,不太方便幫他翻身,父親的后背出現(xiàn)了褥瘡,墊上了膠圈,每隔幾個小時膠圈上纏的紗布便被血水浸透。每次換紗布,對我都是一場折磨。
父親住院時,大哥正在天津看病。接到電話,從天津趕了回來。那幾天他每天在自己家喝酒,喝醉了便瘋了似的鬧騰。他認(rèn)為這些年他對父母的付出比弟妹多,這讓他心里很不平衡。他還對我二哥很不滿,因為二哥的兒子在日本讀書,經(jīng)濟壓力大,曾說過不想按照舊習(xí)俗來操辦父親的后事。另外,他還認(rèn)為這些年我媽偏向小妹妹,對他很不公平。
大哥當(dāng)過二十多年的廠長,平常經(jīng)常自譽是個厚道人。他的一反常態(tài)讓很多人不理解,但我想,這或許是他渲泄內(nèi)心脆弱與痛苦的一種方式,畢竟他身為長子,面臨父親的現(xiàn)狀,他的壓力比弟妹要大得多。為此,我和大哥之間有過一次談話。我說,這些年我們一直以為媽媽是我們這個家的絕對中心,可現(xiàn)在我卻明白了,原來爸爸才是我們這個家的根基,現(xiàn)在看來,雖然爸爸這口氣還在,但他的靈魂已經(jīng)走了,震不住這個家了,所以我們家才會出現(xiàn)這些是非紛擾。是不是別人家這時候也會生出這類家務(wù)事兒呢?大哥想了想,說,嗯——
第五天晚上。妹妹和大哥的朋友守著父親。大哥在家燉了雞,讓我和二哥過去吃飯。那天晚上,我們喝了些酒,說了不少話。大哥二哥說起小時候的很多事,由于我比他們小十多歲,有些事情我并不知道。他們說我在《一只羊其實怎樣》中寫過的我家那只特立獨行的羊,其實還有很多桀驁不馴的壯舉,而我只不過寫出了很少的一部分。大哥說,小時候他還喂過一只安哥拉兔,長到十四斤。二哥說,父親在解放前為了不被抓去當(dāng)偽軍,只身從天津逃出來,步行幾百里走夜道回老家,在捷地附近遇到了狼,父親蹲在一堆碎磚上,手握磚頭,無論那只狼從哪個方向撲上來他都能有效防御,那晚父親一直與狼對峙到天亮。
我則想起,我上學(xué)用的第一個鉛筆盒,是父親給我用木頭做的,很精致,盒蓋可以抽拉。父親還為大哥的女兒做過一個木馬,馬腿上裝著四個小鐵鈷轆,可以拉著跑。而二哥講的父親的那段只身斗狼的經(jīng)歷,我還是第一次聽說,這讓我想到,這些年一直以為父親是一個平常、平凡到平庸的人,原來他也有著自己的生命傳奇。想想也是,父親曾經(jīng)在那么貧窮的歲月里長大,竟然能長成一米八七的大個兒,這本身就是個奇跡。他一生經(jīng)歷過戰(zhàn)亂、饑餓、憂患,用誠實的勞動養(yǎng)大了四個孩子,自己活到八十歲高齡,這無論如何不是件簡單的事情。他靈巧的雙手,他的知足、沉默、謹(jǐn)慎、安于天命,誰說不是一種生活的智慧呢?
那天晚上,我們一直說到后半夜。直到二哥在沙發(fā)上不住的打盹,五十六歲的大哥摟著五十三歲的二哥說,老二,去睡一會兒吧。
那時我已經(jīng)幾天沒怎么睡覺了,天快明時,我在大哥家做了個夢,夢中,我像往常一樣回去看望父母,卻找不到家了,眼前只有一片殘磚斷瓦……醒來,我怔怔地想這個夢,一定是父親要走了。父親沒了便意味著家沒有了。
早晨,我們來到醫(yī)院。妹妹說,父親昨晚發(fā)高燒了,打了退燒針,一會兒輸液時,還得再加些退燒的藥。妹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從小一直對父母很依賴,這些年也是她和父母一起生活的時間最長。從住院的那天起,她就一直盼望著父親能醒過來。這一晚,妹妹很仔細(xì)地把父親的臉和手擦洗得格外干凈。父親臉上的皺紋很少,他雖然勞作一生,但皮膚天生細(xì)膩有光澤,這一點我們兄妹都得益于他的遺傳。
我看著父親。此刻父親恍若一條被風(fēng)浪推到岸上的大魚,張著嘴,吃力地呼吸著,鼾聲的力度已明顯減弱了。他上顎的皮膚由于長時間被肺里呼出的熱氣熏蒸,已經(jīng)開始腐爛、脫落。我想,父親的最后時刻來了。
我握著父親的手。我說,爸爸,你現(xiàn)在一定很難受很難受吧,爸爸,我們都盼著你能好起來,回家,喂鳥,劈柴,和我媽做伴過日子……我說,爸爸,你要是真的不行了,也別有太多的牽掛,放心地走吧。我們會照顧好媽媽,會好好地過日子。我說,爸爸,你一輩子為人清白,勤勞,忠誠,你在睡夢中離開這個世界,是終得善果,是你的福報。我說,爸爸,你走的時候,會有神靈指引你,去西天極樂世界,過安詳喜樂的生活,你跟著他的光明向前走,不要回頭……
當(dāng)我說完了這些,我看到父親的眼角涌出來了一滴眼淚,緩緩地,順著臉頰淌了下來。
幾分鐘后,父親停止了呼吸,安靜地離去。
楊瑞霞,作家,現(xiàn)居石家莊。主要著作有長篇小說《枯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