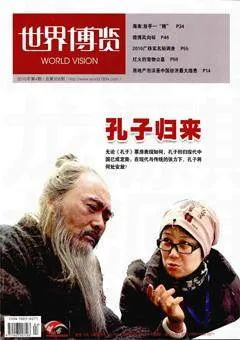張見:迷藏的玄機
在張見的畫面中,至少出現過三種氣質傾向的女性,經過她們之時,仿佛能夠隱約感到張見迷藏的玄機。
趁著有溫州同行的當兒,才有機會和張見真正坐下來,閑談些與藝術相關的話題。讀書期間,接觸并不多,對于他本人的了解,還是畫風更為熟悉。初見他那張《襲人的秘密》之時,我不可抗拒地,被他這種高妙的凝練、深邃的融通之氣給吸進去了,并確知,它的與眾不同——即使我很分明地知道,我所體會到的,可能僅僅是張畫面外延的一部分而已。
“創作《襲人的秘密》之時,忽然意識到中國傳統文化元素之于畫面中的可行性,這讓我異常興奮。我好奇于將已然得心應手的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經典圖式與中國傳統元素作一個跨越時空的對接與融合。”張見如是說。
張見私藏經典,不只是對他所涉及的國畫領域,西方油畫中的經典文本同樣對他有著不可遏制的吸引。雖然采取的語言方式是工筆,但他試圖,在工筆畫這一極具中國傳統文化氣息的形式中找到不同尋常的東西。顯然張見的色彩觀是西化了的,他的畫面出現了原本不屬于傳統國畫中樣板似的色彩關系,而透過這層陌生化色彩以及與之相協調的畫面,卻給他的畫面帶來一種新鮮的可能性:從色階跳躍舒緩的灰色調到明艷的桃紅、粉藍等,完全可以作為一種有意味的象征,呈現并成立于工筆畫當中。
其私藏經典的方式之一在于:構圖方式源自對于歐洲文藝復興早期經典圖式的崇拜。那些畫面元素,如幽雅安靜的女人、爬山虎、棕櫚、電線桿,它們被經典化地組合在一起,呈現給人一種陌生而特殊的印象:不似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宗教感的無上靈光,巴爾蒂斯傳遞的俗世美好,也不似顧愷之《洛神賦圖》亦真亦幻的神話意味,或者趙佶《瑞鶴圖》意象層出的超現實……他似乎都與它們有關聯,又都不完全重疊或貼合。他經由元素的排列組合、色調比例的選擇、線條的繁密或簡淡,去營造一個既有歷史質感、神話氣息,又有時代余味、現世生活感的理想主義。
其后,他轉入之于道具元素的深入思考。在他的作品當中,與自然、人文相關的元素都被附加了意義,從而再一次印證表意的價值,出現了張見極富個性化、個人化的寓言畫面。那些類似于道具的元素——比如頭盔、煙斗、蛇——被安插在畫面所昭示的環境當中,充當營造氛圍的黏合劑。畫面提供了更多思考和想象的可能性,進而神游到蒙特菲洛、瑪格利特所在的年代,回到這些原本有些久遠的訴說當中,回到與蛇相關的性的原罪假想。這些道具,同樣也轉化為他講述畫面的又一層難以一望而知的解釋,似乎有這樣一種講述可能:瞬逝時間的不可重復性、自然的極端永恒性以及人與自然之間多情而暖昧的依存關系……最重要的是,在這一切風物被調動之前“觀念先行”的理念,理念聚合了這些紛紜的元素并賦予意義。
私藏經典的方式還在于,他將經典化的中國傳統文化元素寓于蘊含西方哲學觀念的畫面當中。《襲人的秘密》的出現,再次印證了中西方經典文本可以以一種合理的方式并存于畫面。經由具有典型性的太湖石、手持大紅汗巾子且衣衫不整的古代仕女,你幾乎已然猜測出這個女人的身份。透過襲人的面龐、纖手,可以遙想古代經典仕女畫的圖式景象,窺探到張見之于美感的極致化取合,那絕不是簡單照搬或者肆意顛覆,而是取其精粹,融生出張見式的抒寫方式、風格面貌。極為有趣的是,襲人所在的環境并非是我們慣常猜測的閨閣或者院落,不再是有局限的風景,而是一望無際的荒原、云陣——著實讓人困惑——而那隱約立于其中、象征著現代社會的電線桿讓這一切遠離了原始、野蠻,泄露了文明的玄機。在一派現代文明的背景之下,面對半掩衣衫的襲人,遙想她身為大紅汗巾子變體的相予,變故叢生的命運,借此你甚至可以生發“古今一也”的詠嘆……超時空的并置,有種歷史文獻彼此交疊的預感。眾人立于畫前,所謂歷史、寓言、傳奇、神話,仿佛都在轉身回首的一望中,隱現。
特里薩·德·勞雷蒂斯認為:“女人始終是基本的變現主題,不管是直接作為欲望的對象還是借以表達欲望,這種與力量和創造性密切相連的欲望是推動人類文化和歷史發展的動力。”在現代藝術中,女性形象成為一種反思現實生活的符號代碼和各種藝術觀念的載體,某種程度上,恰如其分地傳達了各個時期藝術家之于世界的獨特感觸和情感幻想。透過張見這些充滿女性質素的畫面,像是穿越一片融化了雪的土地。那些對張見有益的經典文本印象,都被深深滲透,然后消失無蹤——他把所有這些帶有啟發性的暗示,收入囊中,然后生發出全新的與眾不同的氣息。畫面中反復出現的元素,帷幔、棕櫚、荒原、云朵、蛇、半裸的有著優雅身段、幽然魅態的女子,具有松散、清淡、優柔、黏稠的閱讀感,勾兌著人間煙火氣息、道不盡的風情——這讓人想到,面對一灘泥濘的沼澤,人的內心會對其有所防備,不至于陷落;而面對一潭迷離的春水,我們卻容易忽略它的深淺,就在不知覺的觸及當中,被浸潤、被滲透、被吞噬……這并不是荒謬的邏輯,而是神秘的力量和其背后隱藏著的靈魂所賦予每個觀者的心理暗示。稀薄而多情的質地,持遠的理想,凝結于間的空氣感,讓人在畫面的一呼一吸中體察到迷情的實誠與虛妄。
人類有史以來,情色和藝術——從古埃及時代一直到當代,始終保持著一定距離的親密關系,對情色的表達幾乎出現在社會存在的每一時期,尤以龐貝藝術為甚;經營情色成為理所當然的藝術方式。后現代主義一反現代主義回避色情的高尚姿態,煽情而大膽,且蓄意破除禁忌,借助以“性”影射的方式,向通俗的道德標準和藝術觀念挑戰。而面對情色——這一充滿魅惑的果實,張見以澄懷的方式窺探。澄懷與窺探,這兩種貌似矛盾的姿態同時被張見捕捉:畫面中的女性被靜置窗前,剪影般,一切無關于外面的世界。紗幔掩映著女人的身體,經由細膩的光感與風物所組合的節奏,如同沙漏垂直而下流淌,讓人聯想到張見筆下匆匆而過的光陰——那也一定是有質感的,可見的,可敘述的。時光濾去繁縟,女人綻放出迷離幽淡的春情,再沒有誰比她更了解事情的真相,也同樣沒有誰可以比她更多地占據張見的內心。
一切都是幕景,一切都是道具,一切都是現實世界中似有似無的夢境。藝術家不是那個按照呈現面目去看待和理解的人,事物在他們眼中更為豐滿、單純。一個真正的藝術家生命中總是常駐朝氣、春意、情念。張見所持有的思維傾向,憑借畫面營造的夢境以及散透出的個人化氣息來釋放視覺、聯想和詩意的強力。他之于畫面的想象,迂回于傳統崇拜、精神追想、情感迷藏三者之間的細節——那具有非絕對性、帶有模糊化特質的,也可能是虛設的細節當中——細想來,那幾乎是潛游的姿態。其動勢,絕不是跳躍的、鏗鏘的、激勵的,而是靜緩的、典雅的、沉湎的……
在張見的畫面中,至少出現過三種氣質傾向的女性。一種是高貴典雅、端莊溫韻、具有神女氣質的凡女,以略微單純的色調身處近景,遠方是開闊的天地:荒原與云陣。他堅守最為傳統的創作方式,忠實于筆與絹——此種最具代表性的中國傳統藝術創作媒材,呈現中西經典文化時空錯置的交疊趣味,顯現于《置于風景前的肖像》系列;另一種,是一眼望去具有情色誘惑的印象,錯落而有致的構圖傳達出一種不確定的美。在這里,張見將具有中國傳統文化意味的物件:桃花、絲綢、太湖石、迷離的女體,以不同于古人的敘述方式,用饒有興味地“經營位置”,放大或縮小著元素的意義。此時,作品變成了一枚放大鏡,遞給眾人用來端詳。不由想到尼采的言論:思想,詩歌,繪畫,樂曲,乃至建筑和雕塑,不是屬于獨自藝術,就是屬于面對證人的藝術。《桃色》系列傾向于這一類型。再者,是本屬于神話故事中的妖女。《Medusa的預言》中與蛇相繞的美杜莎——是一個糾結著極致美感與深重邪惡的女性,
“不合時宜”地出現于張見的畫面,成為被選中的女人。她被置于虛設的平凡當中,卻又隱藏著與現實之景相悖的暗喻。若被置于另一種語境下,或許會產生關于未知世界神隱層面的猜想,而張見偏偏把她放置在一個交錯的時空,她仿佛成為一則與現世相關、卻不得道破的讖語……我們經過她們之時,仿佛能夠隱約感到,張見迷藏的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