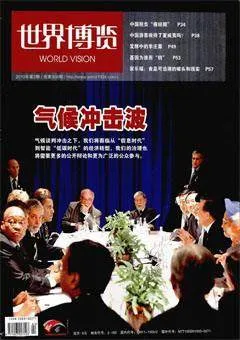波匈事件的中國版
1956年的中國,雖然出現退社、罷工、罷課、請愿與游行,但在處理-類似波匈事件的群眾騷亂中,中共表現出了政策上的靈活性。行光
1956年6月上旬,波蘭波茲南市來蓋爾斯工廠(斯大林機車車輛廠)的工人要求退還過去三年不應征收的稅款,還提出改革工資制度等要求,拉開了影響深遠的波匈事件的序幕。在蘇聯的軍事威脅和武力干涉之下,到了1956年11月,東歐的十月危機過去了,華沙和布達佩斯電逐漸平靜下來。
雖然隔著千山萬水,但波匈事件對中國社會的震動絲毫不亞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除執政黨外,整個國家也在積極思考。對波匈事件作出強烈反響的主要是基層黨政干部、知識分子(包括大學生)、民主黨派和私營工商業者, 一般工人、農民和青年學生,雖然對東歐事變沒有表現出興趣,甚至也不了解,但是對切身利益的關注使得他們中許多人采取了與波匈事件非常類似的舉動——退社、罷工、罷課、請愿和游行。這給執政的中共出了一個不小的難題。
知識分子反思社會主義制度
《內部參考》是供中共高級干部閱讀的刊物,1949年創刊;1964年停刊。從其1956年的文章中可以看到知識分子列波匈事件普遍感到意外——在社會主義國家竟然也會發生群眾暴動和示威游行?匈牙利的暴動如果是反動的,為什么有許多群眾參加?如果是合理的、正義的,為什么政府又要鎮壓,蘇聯軍隊電出來了?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代表剛去波蘭是否妥當?波蘭和匈牙利的民主化是否做得有些偏激?他們提出要求獨立、主權是什么意思,難道蘇聯妨害了他們的主權和獨立?
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是,為什么被視為具有無比優越性的社會主義國家發生了如此嚴重的事件?很多人的看法已經深入到社會主義國家的政策乃至制度層面。上海一些職工、干部、工商界人士就認為,波、匈共產黨犯了嚴重的教條主義和脫離群眾的錯誤,不關心群眾生活,結果“官逼民反”。還有人認為是黨內不團結,同中國的高饒事件差不多。更有人挖苦說:“天天夸社會主義,夸了半天鬧成這樣。”
人們從一系列國際事件聯想到了中國。如民主建國會山西省委副主任委員胥以恒認為,波蘭、匈牙利事件的發生,證明黨和政府工作上有缺點,這應該成為中國的前車之鑒。與胥以恒的含蓄相比,北京大學氣象系四年級學生胡伯威的批評則尖銳得多,也最具代表性。10月27日,胡伯威致信《人民日報》,指責中國報紙對所發生的國際事件封鎖消息,他說: “報紙應該尊重自己的讀者,將事物真面目不加修改和粉飾地反映出給讀者。”“一個能夠把自己的思想建筑在對事物的真實情況的了解上的人,才名副其實地是思想有自由的人”,而在中國, “只有報紙來提供這種自由”。他嚴厲地指責《人民日報》關于波茲南暴動以及波匈事件的報道“粉飾現狀”,報喜不報憂, “令人作嘔”。信中表達了一個善于思考的中國大學生對民主和自由的看法: “我堅決相信民主自由的充分發揚,人權和人的尊嚴得到真正的(不是口頭上的)重視,黨的宣傳工作忠實地遵從這些原則,才能把人民群眾真正放到主人翁的地位,這才對社會主義有極大的好處,人民群眾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才會變得聰明,成熟,有對社會和國家的責任感,熱愛之情,才能以雪亮的眼睛來防止和消滅種種可能發生的弊病,消滅騎在群眾頭上的官僚主義和腐朽傾向。” 胡伯威的來信已經超出當時執政黨意識形態所能容忍的程度,但還有更為極端的言論。比如,在北京鋼鐵學院的食堂等幾個地方,就出現了粉筆寫的標語: “反對目前社會制度”,“我們要民主自由”,“中國人民處于悲慘的情況中,青年們行動起來吧”, “支持匈波人民的斗爭”。
事實上,知識界和工商界對中共現行政策的不滿情緒,在此之前已經有所表露,東歐的動蕩不過更加強化和刺激了這種情緒。還在1956年初,自中共中央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后,各部門收到的有關知識分子問題的來信就大量增加。據不完全統計,至5月底,中共中央及所屬機關共收到來信5200件,普遍反映對知識分子政策不滿。
工商界很多人則對中共給資本家代理人和小資本家定為資本家成分的政策有意見。無錫市資本家代理人普遍說,資本家已經固定五厘利息,企業基本上由國家管理,我們在國家領導下工作,靠勞動,拿工薪,再戴資產階級的帽子,實在冤枉,紛紛要求獻出股份、摘掉帽子。南京很多小資本家半年定息只有5元錢,最少的僅一角七分,卻為此戴上了資本家的帽子。南京市工商聯副秘書長康永仁反映: “摘除這些人的資產階級帽子,對調動他們的積極性是有好處的。”
農民退社、工人罷工
波匈事件前后中國社會的不安定局面主要表現為農民退社、工人罷工和學生罷課。這些情形在1956年下半年繼續發展,甚至日趨嚴重。
12月初中共廣東省委報告:數月來,特別是全省大部分農業社轉為高級社,并進入秋收和準備年終分配以來,各地不斷發生社員鬧退社的嚴重情況。據不完全統計,退社農民已達7萬余戶,已經垮掉的社有102個,正在鬧退社的還有12.7萬余戶。
據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與遼寧、安徽、浙江等8個省電話聯系,秋收前后在一部分農業合作社中,退社戶一般占社員總戶數的1%,多者達5%。正在要求退社的農戶比例更大,如浙江省的寧波專區,想退社的占20%左右。
據遼寧省手工業管理局9月29日統計,已正式被批準退社的社員有524人。在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中,全市90%多的獨立手工業者都參加了合作社,但高潮過后就出現了社員要求退社的跡象。這種情況在目前供不應求的縫紉、制鞋兩個行業中最嚴重。
《內部參考》還報道了大量工人罷工請愿的情況。如內蒙古森林工業管理局所屬的單位,從6月到9月已經發生了6起工人罷工請愿的事件,參加者少則數十人,多則300人。10月29日福州市發生了60多起筑路民工集體向市人民委員會請愿的事情。波匈事件發生以后,情況更加嚴重。到12月上旬,上海輕紡工業已有53個合營工廠1834人因工資和福利問題先后發生罷工、怠工、請愿和其他鬧事事件。
學生罷課、請愿的情況也時有發生。1956年9月15日在成都的第二機械工業部所屬兩個技術工人學校,400多學生開始罷課,要求轉學和分配工作。參加者很快增加到800多人,并集體到到四川省委和市勞動局請愿,還毆打干涉他們罷課的同學,隨意破壞公共財物,甚至與前來維持秩序的警察發生沖突。此外,還有300多人在成都游行示威,向中級法院請愿、控告。至10月底,學校已陷入嚴重混亂狀態。
渡匈事件后,中國社會的動亂局面確有擴大趨勢。1957年3月官方文件指出:“在最近半年內,工人罷工、學生罷課、群眾性的游行請愿和其他類似事件,比以前有了顯著的增加。全國各地,大大小小,大約共有一萬多工人罷工,一萬多學生罷課。”
盡管從目前看到的史料,還不能說中國發生的這些事件是直接受到國際風波的影響,但就各地鬧事的緣由而論,與波蘭和匈牙利出現的危機頗有相同或相似的特點,即都反映了人民大眾對執政者的強烈不滿情緒,而這種情緒長期受到壓抑,一朝爆發,便成烈火之勢。 農民和手工業者退社,主要是因為合作社管理上的問題比較嚴重,經濟收入不如入社之前。至于工人和學生的罷工、罷課、請愿、游行,基本上也都是因為工作條件、生活待遇問題沒有解決好,或者是出于對基層管理干部的官僚主義作風不滿和反抗。
縱觀各方面的材料,所有事端的起因都是個別的和局部的“瑣事”,就每個具體事件看,規模并不大,程度也不算嚴重,與波茲南和匈牙利發生的事件無法相比,所以當時被毛澤東稱為“少數人鬧事”。但是,這些事件涉及不同的地區和人群,卻有著大體相同的起因。綜合起來看,問題的存在是帶有普遍性和全局性的。中國社會底層的各種困惑、不滿、騷動,與波匈事件的震撼和反響交織在一起,在1956年下半年構成了一種雖不過分緊張,但又令人不安的局面。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確實有些擔憂了。
中共的讓步和安撫措施
1956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指示,要求各農業合作社在當年秋收分配中,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員增加收入;對包工包產不合理、勞動報酬定額不夠準確的問題加以清理,在實行超產獎勵、減產處罰的制度時,采取多獎少罰的原則;對人社生產資料作價不合理的問題,也要好好清理一番,把社員應該交納的股份基金計算清楚,欠交的應該盡力補交,多余的應該分期償還;對農業社干部的報酬,應該根據本社的具體情況和合作社章程規定,對于不合理的部分加以適當的調整。
11月30日、12月24日,中共中央分別批轉河北省委、廣東省委的報告,在批示中告誡各地黨委, “急急忙忙”讓富裕中農人社“本來是不策略的”,因此讓一部分要求退社的富裕中農退社“不但無害,而且有益”;對堅持退社的手工業者和其他行業從業人員,可以允許他們退出,不必勉強把他們留在社內。批示還注意到合作社內困難戶的問題,要求從公益金中給予適當補助,必要時可暫時給以土地報酬。
1956年下半年,城市經濟生活出現一個新現象:一些原私營工商業戶開起了“地下工廠”、“地下商店”,個體手工業生產也日趨活躍。9月份上海市手工業個體戶為1661戶,從業人員5000多人;lO月份就發展到2885戶,從業人員8100多人。
12月7日,毛澤東與民主建國會和工商聯負責人談話,說到“地下工廠”時,毛指出:目前中國的自由市場,“基本性質仍是資本主義的”。但自由市場和地下工廠能夠發展起來,這說明“社會有需要”。應該“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毛澤東以制衣業為例,主張私營工廠與合作社競爭,并把這叫做“新經濟政策”。 “只要社會需要,地下工廠還可以增加。可以開私營大廠,訂個協議,十年、二十年不沒收。華僑投資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沒收。可以開投資公司,還本付息,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 緩解社會緊張,平息各地“鬧事”,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解決國民生活問題。1955年起,由于過分偏重國家基本建設,日用品生產受到擠壓,加上各地爭搶高速度,導致物價上漲,商品供應緊張。8、9月間,全國范圍內在提高工資基礎上的工資改革陸續結束,增加工資后的社會購買力,很迅速地集中投入到消費品市場。再加上全行業公私合營后,資方的上半年定息也在這一時期發放,更增加了對消費品市場的沖擊。呢絨、絨線、針織品、家具等供不應求,部分高級消費品如自行車、無線電、手表、鉆戒等,也暢銷起來。工業消費品市場,十分活躍和緊張。副食品的供應也很緊張,特別是豬肉來源較緊,減少了供應量,居民發生排隊搶購的現象。
面對壓力,中共中央不得不調整國家建設與人民生活的關系,在安排計劃時強調注意人民生活。12月18日,代總理的陳云主持召開國務院全體會議,提出了“在照顧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民生條件下來搞建設”的觀點。主張消減1957年基本建設投資,陳云意味深長地指出,這樣做“可以避免犯東歐國家的錯誤”。
做好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工作,自然也是安定社會的一個重要方面。上半年提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后,中共中央統戰部即在內部系統開始了一次檢查工作。從民主黨派、知識界、工商界的反映看,不僅對中共各級統戰部門有意見,而且對各單位內部許多具體問題的處理意見更多。于是,中共中央在12月26日作出指示,要求進一步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和民族政策執行情況的檢查,重點是政府機關、學校、企業和部隊,主要檢查這些單位中的中共黨員同黨外人士的合作共事關系。中共承認,統一戰線工作和民族工作“存在許多缺點和錯誤”。
1957年1月18日至27日中共召開了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毛澤東很有信心地說,中共的農村政策和城市政策都是正確的,“所以,像匈牙利事件那樣的全國性大亂子鬧不起來。無非是少數人這里鬧一下”。在1月27日的講話中,毛澤東重點談了“鬧事”問題。他說, “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少數人鬧事,是個新問題,很值得研究”。
毛澤東用階級斗爭的觀點進行分析,認為鬧事就是對立面的斗爭:地主、資本家鬧事是因為他們心懷階級仇恨,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議論紛紛是因為他們都講唯心論,大學生鬧事是因為他們大多數都出身于剝削階級家庭。至于在工人和農民中間發生的少數人鬧事的原因,一方面是“領導上存在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在政治或經濟的政策上犯了錯誤”,是“工作方法不對頭”;一方面“是反革命和壞分子的存在”。由于對立面的斗爭是永遠存在的,“少數人鬧事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
對待“鬧事”的態度,毛澤東主張既不提倡,也不害怕,要有充分的準備和積極的態度,這是一種“領導藝術”。他以匈牙利為鑒說: “你不許罷工,不許請愿,不許講壞話,橫直是壓,壓到一個時候就要便成拉科西。黨內、黨外都是這樣。各種議論,怪事,矛盾,以揭露為好。要揭露矛盾,解決矛盾。”毛澤東最后提出:“怎樣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是一門學問,值得好好研究。
毛澤東的這番講話,已經蘊含了他后來發動反右派運動的思想基礎。
(本文根據沈志華教授的文章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