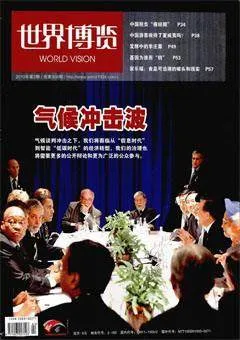那塊“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
“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標牌存不存在也許并不重要,因為那段遭受殖民統治的歷史是不能抹殺的。
周作人在1903年9月11日的日記中這樣寫道:“上午乘車至高昌廟,晤封燮臣,同至十六浦。途中經公園,地甚敞,青蔥滿目。白人游息其中者無不有自得之意,惟中國人不得人。門懸金字牌一,大書‘犬與華人不準人’七字,哀我華人與犬為伍。園之四周皆鐵柵,環而窺者甚多,無甚一不平者。奈何竟血冷至此!”這差不多是今天人人皆知的“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標牌的最早記載。但是經過現代學者的研究,這個深深影響了中國人民族情緒的牌子,是否曾經存在過已被打上了問號。
拒絕華人入內的公園
周作人當年途經的公園,今天叫做黃浦公園,當年的上海人把它叫做公園、娛樂場或者外灘公園,1868年建成并對外開放,不久之后就成了是非之地……
最開始的抱怨來自外國人。1868年公園建成之后就禁止華人進入,但“身份尊貴”、“衣冠楚楚的紳士”除外,當時,外國人的華人仆人,尤其是阿媽,如果在外國人的陪同下也可以進入公園。而且當時的上海公共租界雇員,比如華人警察也可以進入。進入公園的華人一多,歐洲人就開始抱怨,于是1881年租界當局改變了政策,禁止所有華人進入。而這一政策激怒了居住在租界里的華人領袖。他們要求殖民當局區別對待承認他們的權利。
1881年4月6日,上海虹口醫院醫師惲凱英和怡和洋行買辦唐茂枝等聯名致函工部局總辦,他們用英文寫道:我們都是租界的居民,而且是納稅人,想請問你有什么條文規定中國人不可以進入公共花園?我們沒有見到官方有關這方面的文件。昨天,我們中有位先生冒昧地想進入花園,不料被門警阻擋了。
4月20日,工部局秘書索爾本復信說:花園的范圍不大,不可能讓所有的中國人都進來游賞。門瞽曾得到過指示,只讓文雅的衣冠整齊的中國人進入花園。如果被拒絕,那一定是門警誤會了,工部局表示歉意。但4月25日,工部局又復信說:工部局并不認為中國人有進入花園的權利。我們是根據英國駐滬領事館領事溫斯達致上海道臺的信來管理公園的, “這塊地方是給在上海的外國社區的居民作為娛樂場所或公園之用”。
但工部局先前的表態畢竟已經對于上等華人入園問題采取了默認態度。不久,作為一種變通的辦法,唐茂枝等人就提出了有限制地向上等華人開放公園的建議:所有善意的真誠的來花園游玩的中國人,必須出示證件。證件由工部局發給。有名望的中外人士的介紹信,或是社區居民團體委員會的介紹信,都可以作為入園的證件。
但是1885年的公園明示游覽規則,仍然禁止華人入內。規則共六條:“一,腳踏車及犬不準入內;二,小孩之坐車應在旁邊小路上推行;三,禁止采花捉鳥巢以及損害花革樹木,凡小孩之父母及傭婦等理應格外小心,以免此等情事;四,不準入奏樂之處;五,除西人之傭仆外,華人一概不準入內;六,小孩無西人同伴則不準入內花園。”這項收入《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章程》的六項規定,直到1928年,四十多年間在字句上或有差異,各條順序或有變動,但基本內容沒變。
上層華人仍然抗爭不斷,《申報》等報紙從中推波助瀾,在1885年的《申報》上有文章說:公家花園之創,與夫平時管理修葺,一切等費皆出自西人乎,仰出自華人乎?以工部局所捐之款計之,華人之捐多于西人者幾何?則是此園而例以西法,華人斷不至被阻。且彼日本之人其捐尤少于西人,高麗之人則競一無所捐,而何以顛倒若斯乎!
在民間人士的推動下,1889年3月11日,上海道臺龔照緩在給英駐滬總領事的英文信中寫道:那個地方是在我們中國的土地上,花園基金的主要募集對象也是中國人,而我們中國人卻不能越雷池一步。我們認為這是極不公平的。這對我們來說,是一種侮辱;對我們中國來說,是有損國家尊嚴的。
但是即使是有限發行許可證的制度到了1890年再次受到限制,因為申請通行證的華人太多。而且工部局還說,有幾個例子說明中國人在游園券上搗鬼,如更改日期,過期的入場券再使用等。1890年12月,位于蘇州河南面、里擺渡橋東面的新公園(亦稱華人公園)建成開放,專供中國人使用,張園、愚園等私人花園也對游客開放,華人便很少索證游覽外灘公園了。
1894年的公園規則規定:除了各種俱樂部的仆人或者俱樂部成員以外,華人不得人園。到了1903年,游園規定第一條是腳踏車及犬不準入內;第五條規定除西人之傭仆外,華人一概不準入內;1913的修改條例第一條改為:公園只允許外國人進入,第二條是大與腳踏車不得入內。到1928年公園向所有人開放,在工部局的官方告示中沒有任何“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規定。到底有沒有周作人所說的標牌呢?
殖民侵略的標志
“華人與狗不得入內”這塊標牌已經成為了上海殖民統治的標志,漢學家畢可思在文章寫道:當西方人聽到或讀到“舊上海”時,第一個躍入腦海的印象就是,“華人與狗不得入內”這個宣稱的標志。這是因為,幾十年來,小說家、記者、通俗史學家以及學界人士、游記作者都使他們的讀者了解到這個簡明字句布告的存在。
這個符號第一次出現在英語文本中是在20世紀最初十幾年中,并很快成為西方著作關于中國的一個老生常談的對象。最早的有案可稽的文獻是1914年記者普特南·威爾所寫的小說,在小說中威爾寫道:“布告張貼在公家花園那里。市政當局的一些蠢貨在布告板上涂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我認為這太粗暴了。如果我是他們的話,我會殺了那些外國魔鬼作為報復。”第一次出現于非虛構類作品則是1917年魯塔銳特的《中國的發展》。出生在上海的傳教士之子約翰愛培在關于上海童年的回憶錄中認為,這個著名的布告成了一個“標志,以至于任何關于上海的書都不能不提到它”。
美國朱利葉斯董事會托管基金會的董事長愛德·恩波利,在登載在1930年11月《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中寫道:“一件粗暴無禮對待一個文明國家人民,即中國人民的事件,……最重要的例子——一塊豎在上海迷人的公園里的告示牌,用正楷字樣公布‘狗與華人不得入內。”
在中國對這個牌子的議論涉及到民族的覺醒、國家的獨立等多重問題。郭沫若在1923年8月23日夜間寫的《月蝕》一文中,說;“沒有法子走到黃浦公園去罷,穿件洋服去假充東洋人去罷!可憐的亡國奴都還夠不上,印度人都可以進出自由,只有我們華人是狗!”又寫道:“……穿和服也可以,穿印度服也可以,只有中國衣服是不行的。上海幾處的公園都禁止狗與華人人內,其實狗倒可以進去,人是不行,人要變狗的時候便可以進去了。”
1923年11月16日蔡和森在《向導報》發表題為“被外國帝國主義宰制八十年的上海”一文中寫道:租界以內最初是不準華人居住的,而是“華人與犬不得入內”的標牌,至今懸掛在外國公園的門上。
1924年11月25日,孫中山發表《中國內亂之原因》的演說:“上海黃浦灘和四川路那兩個公園,我們中國人至今還是不能進去,從前在那些公園的門口,并掛一塊牌說:狗同中國人不許人。現在雖然取消了那塊牌,還是沒有取消那個禁例。”
我們可以看到蔡和森說的牌子是“華人與犬不得入內”,而孫中山說標牌是“狗同中國人不許人”。而且他們提到的公園也不確切。而方志敏在1935年就義前所寫的《可愛的中國》提到他看到的牌子上寫著“華人與狗不準進園”,他說“有幾個窮朋友,邀我去游法國公園散散悶。一走到公園門口就看到一塊刺目的牌子,牌子上寫著‘華人與狗不準進園’幾個字。這幾個字射入我的眼中時,全身突然一陣燒熱,臉上都燒紅了。這是我感覺著從來沒有受過的恥辱!在中國的上海地方讓他們造公園來,反而禁止華人人園,反而將華人與狗并列。這樣無理的侮辱華人,豈是所謂‘文明國’的人們所應做出來的嗎?……我后來聽說因為許多愛國文學家著文的攻擊,那塊侮辱華人的牌子已經取去了。但以畜生看待華人的觀念,是至今沒有改變的。”
早年留學英倫,通曉多國語言,曾任國民黨的外交專門委員會委員的湯良禮,后來附逆汪偽政權,但他的著作在海內外很有影響。在他1927年出版的英文著作里,他提到一個外國人馬隆的照片作為證據,聲稱這個牌子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才被摘掉的。
有關這個牌子的故事還是一直流傳,新中國成立后,隨著教科書深深烙印進每個中國人的心里。這個標牌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有力象征,最能激發中國人的義憤。
在1973年的香港電影《精武門》里,印度警察指著那個“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不讓李小龍飾演的陳真進入公園,而同時穿和服的日本人甚至帶狗的歐美人卻堂而皇之地進入。日本男人還說如果陳真扮成狗的話就可以帶著他爬進去,怒火中燒的陳真把日本人打死了,還把掛在公園門口的“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告示牌踢得粉碎。據說電影首次在香港公映時,看到此處全場觀眾大聲歡呼。
標牌是怎么出現的
盡管報界批評不斷,工部局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禁止華人人園的規定。在1900年以前的文獻中,迄今未見到有人將公園規則第一、第五條相提并論的情況,也沒有見到從侮辱華人角度將華人與狗聯系在一起表示憤慨的情況。那么,為什么1900年以后關于牌示問題就出現了,將公園規則第一、第五條相提并論的情況就多了起來?可能的解釋只有兩種:其一,1900年以后,公園確實出現過僅寫“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字樣的牌示。陳岱孫、周而復、曹聚仁、蘇步青、桂祖良、宋振庭都說確實存在,并且親見。寫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非正式小型告示牌,或許只是實物或者照片沒有流傳下來,而實際上確實存在。
中國學者吳貴芳、薛理勇,英國學者畢可思,美國學者華志建,日本學者石川禎浩等看法則比較謹慎。上海社科院熊月之教授認為:在沒有發現確定性證據的現在,可以認為在正式向中國人開放之前,在外灘公園門口,有過限制中國人和狗入園的告示牌。但是,一般所想像的那種將兩者連在一起所謂“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告示牌,看起來好像并不存在。他認為20世紀初,有著強烈民族主義的人們從“公園六條”中品出侮辱華人的味道,并將之加以發揮。
熊月之教授認為1900年以前上海的華洋關系相對和諧,除了兩次小事件外,沒有太大的沖突,也還沒有明顯的民族主義意識,沒有上升為中外沖突。但進入1900年以后,上海的華洋沖突就逐漸升格為中外問題,民族主義色彩越來越濃厚。比如1909年《申報》上刊登了一張外灘公園的大幅照片并說,這里不準華人進入。在報紙的宣傳之下,公園成了民眾關注的焦點。
英國學者畢可思,美國學者華志建則認為,有關這個標牌的議論主要出現在20世紀10年代末20年代初,所以這個牌子的故事很可能是在20世紀初的幾年內開始流傳。至于這個牌子是怎么開始出現的,他們認為很可能正如溥儀的老師莊士敦所猜測的,是把公園規則的第一條“不準華人人內”與其他條目綜合起來說,概括成了“華人與狗不得入內”。
華人不得入內的公園守則早在1903年就存在,到1913年改成更中性些的“只準外國人進入”。畢可思認為這個都市傳說很可能是在1913年之前產生的。與知識分子為了激起愛國主義的情緒而“創造”了“華人與狗不得進入”這個標牌的觀點不同。畢可思認為那些沒文化的上海阿媽或者其他傭人在謠言的傳播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他認為,有一段時間,作為外國人的仆人,這些下人是可以進入公園的。這些人不認識英文,但是能從某一條中認出“華人”,另一條里認出“狗”這些英語單詞,他們經常把這些條文指給其他上海下層民眾看,也許“華人與狗不得入內”這個影響深遠的牌子就這樣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