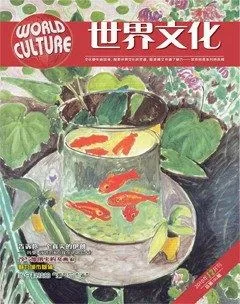告訴你一個真實的伊朗
我知道,當我選擇說出這十故事,
我就再也回不去了。
我的故鄉,沒斯沒里斯。
那覆蓋著皚皚白雪的阿爾伯茲山,
以及奶奶身上迷人的茉莉花香。
然而,我選擇告訴你們這個故事,
從古波斯文明的波斯波里斯,直到現代伊斯蘭下的神秘面紗。
我永遠記得奶奶的話:不要忘記你從哪里來。
這是我純真的革命童年,我青春的愛情流浪。
這是我的伊朗,我的家鄉。
這是我的,茉莉人生。
——瑪贊·莎塔碧
伊朗,當人們談起這個古老國家的時候,總不外乎兩種情愫:一種是對昔日波斯帝國神秘輝煌的緬懷,波斯波里斯石柱,《一千零一夜》,楔形文字,波斯神毯;而對于現代伊朗,大多數人通過國際媒體得到的印象,就是一片充斥著戰爭,飛彈,宗教狂熱主義,恐怖主義的土地。伊朗人也為此被貼上了諸如貧窮、極端、保守、邪惡的標簽,而很多人卻忽略了這個國家的國民作為“人”的個體存在。
在今天的法國巴黎,生活著一個長著中東面孔,說一口流利法語,言論比西方人更大膽直率的伊朗女,人_瑪贊·莎塔碧,一個在伊朗長大旅居法國的漫畫家,她的自傳體漫畫《我在伊朗長大》近年來暢銷全球。瑪贊·莎塔碧親歷了伊朗近幾十年的風云變遷,她用孩童的視角和優美柔和的筆觸,將一個伊朗女性的生命史娓娓道來,試圖用她的親身經歷告訴世界一個真實的伊朗。
瑪贊·莎塔碧1969年出生于伊朗拉什特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在德黑蘭長大,母親是波斯國王的曾孫女。從瑪贊童年時代開始,伊朗就進入了一個動蕩、危險的時刻:國王的暴政引發社會的激烈反抗,幼小的瑪贊目睹了當時在特殊政治形勢下越來越壓抑的公民自由,隨后是1979年伊斯蘭教革命,王朝被推翻,她目睹了戰爭的毀滅與摧殘,遭受了親人的離別。瑪贊的祖父是卡扎爾王朝的王子,為革命死在監獄,叔叔是民主斗士,最終被判絞刑,這一切給她幼小的心靈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幼年的瑪贊聽父親講述沙赫推翻卡扎爾王朝,聽叔叔講述共產主義革命結束沙赫統治,政治這個敏感的字眼很早就成為瑪贊生活的一部分,革命和戰爭,在她的童年生命里一直熙熙攘攘,也讓她從小就表現出一種對社會事物的驚人早熟的看法。在小瑪贊看來,所謂伊斯蘭教革命就是不能跳舞、不能聚會;就是8歲到80歲的女人都穿得一模一樣;就是半夜開舞會,被警察逼得跳樓身亡;就是老師帶頭撕掉課本上講到國王的頁碼,在課堂上撒謊說現在沒有政治犯。瑪贊在伊朗改革派家庭中成長,深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她讀法語公立學校,迷邁克爾·杰克遜,聽Rock&Roll和朋克,看李小龍功夫片,上街參加游行抗議。1980年兩伊戰爭爆發,這場戰爭持續了8年之久,她的不少親友、同學都死于這次漫長的戰爭。1984年,父母為了讓莎塔碧能夠脫離伊朗的戰亂環境,將她送到奧地利維也納繼續學業。
然而,當14歲的瑪贊來到奧地利,親臨以往那個只存在于海報、電影和磁帶中的西方世界時,她卻如葉公見真龍般震驚,她畢竟來自一個“當眾接吻都被當作性行為”的東方國家,她試圖否定自己,融入他們,她流利的法語可以讓她謊稱自己是法國人,因為在歐洲人眼里,伊朗簡直是個妖魔般的國度。青春期的瑪贊在一切自由的氛圍里,遇到了同性戀者、吸食大麻者、性自由者,為了讓自己看起來不那么格格不入,她也開始嘗試戀愛,性,大麻。然而,瑪贊并不能在歐洲找到歸屬,那些維也納的平安夜從來與她無關,她試圖在愛情中尋求溫暖,但是,她的第一個戀人,在與她相守后證實了自己是個同性戀,而讓瑪贊覺得和自己心意相通、融為一體的第二個戀人,最終被發現是個尋花問柳的混蛋,他另結新歡還用光了瑪贊的學費,倔強的瑪贊沒有告訴父母自己的處境,終因繳不起房租被房東罵為小偷、妓女,并被驅逐出門……她最終精神崩潰,在寒冬流落街頭,在公園長椅上度過她18歲生日,幾乎病死異國。革命和戰爭無法傷害她,愛情卻差點要了她的命。瑪贊哭著打電話給母親,說:“我要回來,但你什么問題都不能問。”母親說:“回來吧,我什么都不問。”
瑪贊于是回到伊朗,回國進入藝術學校接受大學教育,重新戴起面紗的她此時又表現出另一種格格不入,她仍然沒有改變自己仗義執言的個性,繼續針砭時弊,“在奧地利我是外國人,回到伊朗我卻依然像是個外國人。”她游蕩在伊朗和歐洲之間,伊斯蘭文化與西方文化在她身上的沖突是難以掩蓋的。在故鄉倉促覓得的愛情只是片刻的喘息,瑪贊經歷了一場短暫的婚姻。一年后,在那段讓愛情干涸的婚姻里,生活又迅速墜入庸俗和乏味,瑪贊又一次近乎絕望。每當在她面臨精神危機的時刻,總有來自家庭的偉大力量,父母和奶奶總給她無限的鼓舞和勇氣,在這個貴族家庭中,家教嚴厲又不失開明,既有傳統價值觀的堅持,又有超越于這個國家的開明價值觀。瑪贊在家人的支持下離婚。這時的瑪贊已意識到,盡管自己是個地地道道的伊朗人,卻無法在這個國家生活,她再次離開父母,離開家鄉,去法國尋找新的自由。母親告訴她:“孩子,我要你自由,去找你自己的生活,再不要回家。”當瑪贊又一次遠離故土來到法國,別人問她從哪里來,她平靜地脫口而出:“伊朗。”這時她已重新找回自己的身份印記,并可以坦然追求自由。
瑪贊移居法國斯特拉斯堡,她結識了法國漫畫家大衛·B,開始致力于圖畫小說、插畫和童書,成為一名插圖畫家和兒童書籍作家。2001年,她的自傳體漫畫《我在伊朗長大》出版,《我在伊朗長大》系列共四部,分別是《面紗》《安息日》《流落奧地利》和《回家》,全球銷售20余萬冊,橫掃眾多漫畫大獎,包括2001年法國安古蘭國際漫畫節最佳首版漫畫,2001年比利時布魯塞爾Lion大獎最佳首版漫畫,2002年法國安古蘭國際漫畫節最佳漫畫獎,2004年美國Harvey獎美國最佳外國出版物,2004年德國法蘭克福書展最佳漫畫獎。
2007年,漫畫被改編成同名電影,這部帶著濃郁中東風格用傳統方法繪制的黑自動畫片驚艷戛納電影節,作為唯一入圍的動畫片一舉奪得評委會大獎。在華美繽紛的電腦三維動畫風生水起的年代,這部黑白二維手工繪制的動畫片一反潮流,摒棄色彩,拒絕透視,用簡潔的線條和細密的筆觸,描繪了一個伊朗女孩兒的成長史,舉重若輕地展現了伊朗經歷的推翻巴列維王朝的人民起義、伊斯蘭教革命、兩伊戰爭幾個重大歷史轉折,將個體成長與一個古老國度的記憶用幽默戲謔的方式一一展現,投射的卻是不能承受之重的文明陣痛。
瑪贊的作品最難能可貴的,是在政治和文化沖撞的嚴肅主題下始終沒有丟掉純真幽默的童真視角,尤其是那獨特的畫風讓人耳目一新。黑白兩色勾勒出強烈的儀式感和冷峻感,保持了人物描述的單純和簡潔,然而畫面又充滿伊斯蘭特質,利用花卉、樹葉、人體輪廓和獨特的幾何圖形,構建起一種直線、角線或曲線交錯的畫風,讓影像在沉重憂郁中透出難得的幽默和溫情。戰爭、死亡、政治迫害、離別傷痛,都被一種舒緩綿長的曼妙深情消解。這份洗盡鉛華的簡樸,讓習慣了夢工場商業3D動畫的觀眾感受到獨特的清新馥郁。
《我在伊朗長大》是瑪贊·莎塔碧對她深愛而無奈的國度的一聲呼喊,也是對西方國家無端指責和誤解的一種回擊,更是對摯愛親人的一次深深擁抱。影片在戛納電影節上捧得評委會大獎而在本國卻飽受冷遇,伊朗電影機構宣稱這是一部“沒有真實反映伊斯蘭教革命偉大成就”的電影。其實從漫畫出版那天起,瑪贊就知道她再也回不去伊朗了。今天的瑪贊在法國巴黎定居,她喜歡這個不禁煙,不平則鳴,經常罷工、偶爾沒車可搭的城市。
而對于她離開多年的國度伊朗,她依然有種無法割舍的依戀:“法國就像是我的妻子,而伊朗則像是我的母親。我的母親,哪怕她是失常的或者是發瘋的,并不會改變她是我母親的事實。我當然可以選擇自己的妻子,但是我可能會選錯或者離婚……”錯置的生活境遇使她身份迷茫的同時,也獲得了一般人很難擁有的批判距離感和此地與彼方的雙重視角。“我認為,不應該根據少數幾個極端分子的惡劣行為而對整個國家做出評判。我也不希望人們忘記那些為了捍衛自由而在獄中失去生命、在兩伊戰爭中喪生、在各種暴政統治下遭受折磨,或被迫離開親人和祖國的伊朗人。”瑪贊努力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來告訴人們,伊朗不止是“1979年前的飛毯和1979年后的飛彈”,她希望讓世界看到這塊土地上真正的“人”。這些黑白線條勾勒出一部成長的連環畫,也見證了一段民族的記憶。
“人可以原諒,但絕不應該忘記”,瑪贊·莎塔碧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