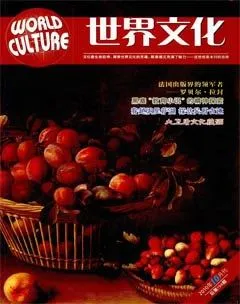現(xiàn)實主義的另類挖掘
《和巴什爾跳華爾茲》是以色列導(dǎo)演阿里·福爾曼2008年的作品。此作一經(jīng)上映便在紀(jì)錄片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除了影片所蘊含的深刻內(nèi)涵和人道主義精神,作為一部動畫紀(jì)錄片,其革命性的表現(xiàn)方式也成為了評論家們津津樂道的話題,它的大膽革新預(yù)示著紀(jì)錄片領(lǐng)域出現(xiàn)了一種新的理念、新的藝術(shù)追求。
動畫在表現(xiàn)形式、時空重塑、歷史還原等方面有著無可比擬的自由度,對擴展、開拓紀(jì)錄片的拍攝手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此,在本片之前已經(jīng)有一些紀(jì)錄片開始利用動畫的穿插來展現(xiàn)一些難以用真實影像表現(xiàn)的內(nèi)容,但像《和巴什爾跳華爾茲》這樣如此大膽的全動畫紀(jì)錄片可以說是未有先例,這也使它擁有一種別具一格的震撼力。
影片中,導(dǎo)演福爾曼試圖還原他對20多年前貝魯特難民營大屠殺的記憶。1982年,黎巴嫩新當(dāng)選總統(tǒng)、基督教長槍黨高級領(lǐng)導(dǎo)人巴什爾在貝魯特被炸死。長槍黨民兵為了替遇刺的領(lǐng)導(dǎo)人報仇,在以色列國防部長沙龍和以色列軍隊的默許下,對薩布拉和夏蒂拉的巴勒斯坦難民營中的平民進行了一場駭人聽聞的種族清洗,具體死亡數(shù)字至今難以計算……
一切起源于福爾曼的昔日戰(zhàn)友博阿茲·瑞恩的噩夢。
“它們佇立在那里,嗥叫著,26只惡狗,我知道它們表情的含義——它們是來殺戮的。”這是當(dāng)年,博阿茲在黎巴嫩村莊搜查被通緝的巴勒斯坦人時射殺的26只狗。“26只狗,每一只我都記得清清楚楚,每一只的長相,每一只中彈的地方和它們死時的眼神……26只。”當(dāng)年大屠殺的殘酷景象就像這26只惡狗,20多年來一直撕扯著這些士兵的心,戰(zhàn)友的噩夢也喚起了福爾曼腦海中關(guān)于戰(zhàn)爭的殘存畫面:“那一晚,是20年來的第一次,我的思緒回到了黎巴嫩的戰(zhàn)場上,不只黎巴嫩,還有貝魯特,不只是貝魯特……還有在薩布拉和夏蒂拉難民營的那場大屠殺……”
福爾曼的夢境也在影片中屢次穿梭:夜空中點點焰火緩緩滑落,將海岸邊的城市照耀得有如白晝,年輕的福爾曼和戰(zhàn)友赤身裸體地從金光點點的海水中沐浴而出,涉水上岸,套上軍裝,拿上武器,穿梭于這個廢墟城市的大街小巷,迷茫地面對著像潮水般迎面涌來的絕望嚎哭的女人們。這一具有迷幻色彩的夢境,表現(xiàn)的是福爾曼對于這段血腥歷史的模糊記憶,像他的戰(zhàn)友一樣,沉浸在夢境和臆想里是他們逃避這段慘痛經(jīng)歷的唯一手段。
借助動畫這種不受約束的表現(xiàn)形式。福爾曼得以不受紀(jì)錄片的手法所限,而大量表現(xiàn)富有隱喻性質(zhì)的夢境與幻覺。相應(yīng)的,影片請來了兩位心理學(xué)專家對這些夢境進行解構(gòu)和剖析,從精神分析角度挖掘出造成這些幻覺的深層次心理原因,從而拼接出外在的歷史真實。
為了重組對大屠殺的記憶,福爾曼重訪了九位同樣親歷過這場戰(zhàn)爭,目擊了大屠殺的人:
“你為什么而來?”
“我失去了記憶。”
那一場屠殺究竟有沒有發(fā)生過?
這是福爾曼自己和所有參加過這場屠殺的士兵面臨的同一個問題,“我不記得大屠殺時的任何事了……大屠殺,好像不在我的腦海里一樣”。正如影片中女心理醫(yī)生所提到的,人在親歷了一些可怕的事情之后會患選擇性失憶,人性本身會阻止我們走進心理的陰暗面,記憶只帶我們?nèi)ピ撊サ牡胤剑胗涀〉淖匀粫涀。幌胗涀〉模呐驴吹健⒙牭揭矔S即過濾,這是人的一種自我保護機制。戰(zhàn)爭給每一個士兵的心靈都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創(chuàng)傷,再度回憶起當(dāng)年發(fā)生的真相對他們來說無異于莫大的折磨。于是,他們選擇了對記憶進行掩埋、忘卻或臆造,只可惜種種嘗試注定是徒勞的,生命中有些軌跡終究無法磨滅。在福爾曼找尋記憶的旅途中,所有被訪問的人連同福爾曼自己都不得不去觸摸殘酷的記憶禁區(qū)那扇塵封的大門。
鮮血、死亡、子彈侵蝕著記憶的空白。電影在過去與現(xiàn)在、虛幻與現(xiàn)實間自由穿梭,在記憶的一次次回溯和澄清中,幻想的外衣像洋蔥般層層剝開,直到真相顯現(xiàn),褪了色的記憶開始變得鮮活,而大屠殺的情形也就在每個人回憶的碎片中和對自我心靈的拷問中逐漸拼湊完整。而這“不是幻覺也不是潛意識”。
在影片后半段,大屠殺完整的一幕重現(xiàn)了出來:血十字,折磨、拷打,屠殺,廢墟,堆積如山的人類殘骸……影片最后的50秒鐘,不再使用動畫,而是突兀地插入了當(dāng)年屠殺過后的真實的紀(jì)錄片史料,重現(xiàn)了屠殺后的難民營慘絕人寰的景象,一片狼藉的廢墟中到處是男女老幼腫脹、腐爛、發(fā)黑的尸體,哭泣的婦女們控訴著軍隊的惡行。當(dāng)導(dǎo)演絲毫不給觀眾心理準(zhǔn)備的時間,突然撕開動畫掩蓋的糖衣,失去了保護的觀眾一下子停止了呼吸。眼前那清晰、真實,無比嚴(yán)酷的景象提醒了我們之前所看到的一切并不是~場浩大的噩夢,甚至不是一部動畫,不是一部電影,而是活生生的一段歷史和一個個逝去的生命……就像導(dǎo)演本人的記憶,撥開層層夢境的迷霧,那一瞬間的清晰所形成的落差具有極強的殺傷力,這讓人心碎的50秒真實影像就像50年一樣漫長。
福爾曼說:“之所以要留下成千上萬人被殺、孩子被屠殺、婦女被屠殺、老人被屠殺的鏡頭,是因為我想讓這部電影達到一種均衡,那50秒真實鏡頭對我至關(guān)重要。”
影片至此,福爾曼帶我們超越了屠殺現(xiàn)場:你可以不知道巴什爾是誰,不知道黎巴嫩、以色列或巴勒斯坦,不知道貝魯特,不知道薩布拉和夏蒂拉難民營,但這一幕幕是如此熟悉,巴什爾的頭像變成了希特勒、膏藥旗……巴勒斯坦難民換成猶太人、中國人……病態(tài)的戰(zhàn)爭,從來沒有從我們的現(xiàn)實中離去。正像片中心理醫(yī)生分析的那樣:“你對大屠殺感興趣的根源是另外一場大屠殺,你對被屠殺的難民營感興趣實際上是因為‘其他’難民營。”我們從中看到了一個個人類歷史上曾經(jīng)發(fā)生過、正在發(fā)生的和將來會不斷重演的種族滅絕:納粹集中營,南京大屠殺……當(dāng)人性中潛藏的殺戮的欲望借民族、宗教、戰(zhàn)爭和復(fù)仇的名義得到徹底滿足時,葬送的不僅僅是成千上萬個無辜的生命,同時也摧殘著人類自身,并將人類的希望一并埋葬。
導(dǎo)演的夢境最終得到了解釋:海岸邊的城市就是貝魯特,城市上空落下的根本不是什么焰火,而是為了給長槍黨人“順利工作”制造便利的照明彈。
“他們不知道他們正在見證的是一場種族滅絕,”
“那你是站在哪邊的?”
“我同情他們。”
“那你做了什么?”
“我只是站在屋頂上,看著天空中落下的焰火。”
“什么焰火?”
“照明彈。”
“沒有照明彈的幫助,基督教長槍黨的人無法……順利工作”
對導(dǎo)演和當(dāng)時在場的任何一個人來說,有沒有親手發(fā)射照明彈已經(jīng)沒有意義了,這種袖手旁觀本身就已經(jīng)是罪惡。就站在那里,站在屠場附近,平靜地看著一切發(fā)生,看著小小的人影一個個地倒下,充當(dāng)劊子手的幫兇。面對不聞不問的長官,“就那么看著屠殺發(fā)生,和親自動手沒什么區(qū)別。”福爾曼們的失憶,是不敢相信自己和當(dāng)年的納粹分子干了同樣的事情,不敢相信猶太民族竟會帶著種族清洗的創(chuàng)傷去縱容另一場種族清洗,把巴勒斯坦難民營變成了和奧斯威辛集中營一樣的人間地獄。
福爾曼說巴什爾對于長槍黨人來說就像上世紀(jì)著名搖滾樂手大衛(wèi)·鮑依之于他自己一樣。影片的配樂,從古典音樂、爵士樂到上世紀(jì)80年代的老搖滾樂,以MTV般的黑色幽默的表現(xiàn)方式,給當(dāng)年的歷史蒙上一層荒誕,一絲詼諧,一點滑稽,每一個跳躍的音符都敲擊著當(dāng)年這些青年士兵在戰(zhàn)爭中無處安放的青春和支離破碎的夢。個體在戰(zhàn)爭中的渺小和無助所帶來的是深深的絕望,“普通士兵永遠都是政治領(lǐng)袖的棋子而已”。“黎巴嫩,早安:黎巴嫩,早安,痛苦的經(jīng)歷正在上演……將你撕成碎塊,在我的手中你流血致死……哦,我短暫,短暫的人生……”隨著士兵頸部的突然中彈,歌聲戛然而止。在另一幕中,一個士兵將手中的機槍當(dāng)作電吉他彈奏,勁爆的搖滾樂電吉他特殊的金屬聲配合以畫面中不間斷的轟炸、爆炸聲,響起了“我今天轟炸了賽伊達,在晨曦中迎著朝霞-…我差點坐著棺材回家,我今天轟炸了賽伊達”,“我今天炸了貝魯特,我天天都炸貝魯特……扣動扳機的時候,我們將陌生人送進地獄……當(dāng)然,我們在大路上會傷及無辜。如果我離死亡不遠了,我要說我天天都炸貝魯特”,歌曲所代表的涵義不言而喻。音樂中彌漫的恐懼、迷茫、激進和不安的情緒,反映出了年輕士兵,或者說,一個民族面對戰(zhàn)爭普遍表現(xiàn)出的恐懼、壓抑、焦躁和無助。
福爾曼當(dāng)年的戰(zhàn)友,年輕時的弗朗茲,不顧頭頂?shù)臉屃謴椨辏殖諱AG機槍從掩體坑道中一躍而出,肆無忌憚地向高處的敵方瘋狂地掃射,樓頂灑下的鋪天蓋地的子彈雨點般落在他的腳下,伴隨著和畫面形成強烈對比的鋼琴曲,他閃躲子彈的腳步仿佛錯落有致的舞步,他摟著MAG機槍,在巴什爾布滿彈孔的巨幅海報下“瘋狂地炫耀他那華爾茲般跳躍的槍聲和舞步”。
這便是本片“浪漫片名”的由來。“和巴什爾跳一曲華爾茲,是戰(zhàn)場上命懸一線的浪漫”,生命的消逝,只在轉(zhuǎn)瞬之間。
《和巴什爾跳華爾茲》是一部非典型性紀(jì)錄片,“它創(chuàng)造了一種嶄新的電影語言,給觀眾造成強烈的印象沖擊……糅合夢幻場景與歷史真實、運用音樂來充當(dāng)額外敘述的技巧尤為值得褒獎”,“動畫的形式,張狂的色彩,超現(xiàn)實主義的段落,令人震驚的拿來主義配樂,福爾曼把他的才華揮霍到了可能下一次就枯竭的程度。”在各大影展上,專業(yè)影評人都給予了福爾曼的這次個人嘗試以極高的評價,肯定了影片在使用動畫表現(xiàn)紀(jì)錄方式上的創(chuàng)新,稱他的創(chuàng)作為“現(xiàn)實主義的另類挖掘”。但在各種褒揚聲的背后也不乏對此類紀(jì)錄影片的真實性的質(zhì)疑。
略帶凝滯感的二維動畫畫面,殘酷的意識流表現(xiàn)手段,夢境、幻覺、超現(xiàn)實……《和巴什爾跳華爾茲》的確構(gòu)不成一部典型的紀(jì)錄片。此外,雖然影片的原始素材都來自真人采訪,但在影片中的九個被訪者中,有七名是真實存在的人物,而另外兩位,則是應(yīng)當(dāng)事人的要求,借用了別人的故事。
然而,這些并不影響影片敘述的真實性。《和巴什爾跳華爾茲》是一部內(nèi)傾性的紀(jì)錄片,就好像是用心眼在拍攝導(dǎo)演靈魂深處的救贖之路。導(dǎo)演采用這種拍攝方式并不意在對歷史進行準(zhǔn)確的還原。它所真實記錄的是當(dāng)年參與那場屠殺的士兵,戰(zhàn)地記者等相關(guān)人員的記憶以及自己從逃避到直面歷史、反思戰(zhàn)爭的心路歷程。整部影片可以用福爾曼的那個夢境概括:夢中的海水模擬了母體的保護,福爾曼們躺在大海里安詳?shù)亍巴浟诉^去”,但是歷史不容遺忘。為了贖罪、懺悔、祭奠,福爾曼和戰(zhàn)友,終究在經(jīng)歷陣痛后從母體中脫胎而出,上岸直面廢墟般的城市和絕望的婦女,從而沐浴重生,得到救贖。同時,在這超現(xiàn)實主義的夢境背后是曾經(jīng)發(fā)生在黎巴嫩的真實屠殺。影片在帶領(lǐng)著觀眾神游了一趟當(dāng)年的戰(zhàn)場和屠殺現(xiàn)場后,在結(jié)尾的50秒處返回赤裸裸的現(xiàn)實,就像片中女心理醫(yī)生所說,像戴著一副立體眼鏡看一部戰(zhàn)爭大片,然后,突然間,“立體眼鏡”壞了,真相撲面而來,瞬間給人留下難以磨滅的創(chuàng)傷,展現(xiàn)了動畫影像那凌厲、深刻、直達靈魂深處的現(xiàn)實力量,它所造成的沖擊和震撼絕不輸于真實影像。
《和巴什爾跳華爾茲》從外在視聽到內(nèi)在命題,都帶給了觀眾一次靈魂的洗滌。它從普通士兵真實的視角,“拷問了人性的曖昧,審視了民族的弱點”,重新定位戰(zhàn)爭、民族、歷史和生命。讓觀者在不禁動容的同時,也深切體會到了從一個個體到一個民族在人道災(zāi)難和集體悲劇中被撕裂的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