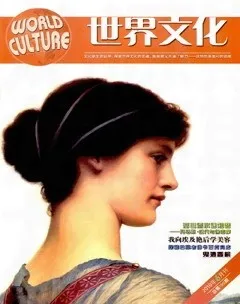高山流水遇知音
“單憑他的四五部長篇,他在文藝界的位置已足夠與莎士比亞、巴爾扎克并列。”以上文字為徐志摩追憶英國作家托馬斯·哈代所作。其情真意切,景仰崇拜之情躍然紙上。除了于文字間表達對托馬斯·哈代的敬仰之情,徐志摩更曾遠赴英國以一睹偶像風采。那么,托馬斯·哈代和徐志摩又有著怎樣的文學因緣?
(一)
托馬斯·哈代生于1840年,卒于1928年,是英國著名的小說家和詩人。哈代的創作跨越了兩個時代,承上啟下,既繼承了英國維多利亞時期批判現實主義的文學傳統,又開創了現代主義文學的先河。從其個人的寫作生涯看,哈代始于詩歌創作,中期以小說創作為主,最后又回歸詩人身份。1910年,哈代被授予殊勛勛章。1928年逝世之后,哈代被葬于倫敦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詩人角,其心臟則遵遺愿被葬于他終其一生熱愛和反復刻畫的故鄉。
作為反抗社會黑暗和追求光明的斗士,哈代在中國一直廣受文人學者以及讀者的喜愛。然而,追本溯源,第一個向中國讀者介紹哈代,第一個把哈代的詩歌翻譯成中文,第一個把Hardy翻譯成現代通用的“哈代”,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目睹過哈代風采的中國人,卻是徐志摩。1928年,徐志摩又在《新月》創刊號上發表《湯麥士·哈代》一文,高度評價了哈代的文學成就。徐志摩不僅翻譯了哈代的二十多首詩歌,而且曾多次撰文或賦詩對大師進行了深切的追憶。到底是怎樣的文學因緣,把這兩個乍一看在藝術氣質上千差萬別的人聯系起來的呢?
縱觀徐志摩短暫的一生,圍繞著他的是各種眼花繚亂的社會新聞和頭銜。“中國離婚第一人”,和林徽因的種種撲朔迷離的感情迷案,和陸小曼那轟動一時的婚戀以及一直為人津津樂道的恩恩怨怨……所有的這些,在某種程度上增加了徐志摩的知名度,但是也是對徐志摩的一種傷害。因為大家常常被這些帶有娛樂色彩的消息和傳聞所吸引而忽略或者低估了徐志摩的文化歷史地位,往往對他的作品和思想不能深刻理解。那么,在大多公眾眼中的這位“溫柔鄉的夢囈者”又是怎樣與“悲觀厭世”的宿命論者托馬斯·哈代結緣的呢?
(二)
對于真實的徐志摩,作為他的知己和兄長的胡適更有發言權。在胡適的眼中,“他的人生觀真是一種‘單純信仰’,這里面只有三個理想:一個是愛,一個是自由,一個是美。他夢想這三個理想的條件能夠會合在一個人生里,這是他的‘單純信仰’。他的一生的歷史,只是他追求這個單純信仰的實現的歷史”。愛、自由、美——這些看似柔軟的字眼,不見得比高深復雜的理論淺薄。對于這“三個理想”,徐志摩孜孜不倦地追求著,并渴望在全人類中得到完全的實現。在其中,“愛”可以說是徐志摩思想核心之核心。這種愛不局限于愛情和親情。它是一種博愛,5JA5QhelJAScLLBPApHmTg==對世界萬物抱有愛,對茫茫蒼生懷有悲憫。他的愛之思想接近于西方文藝復興以來源遠流長的人道主義精神。徐志摩認為,愛是拯救這個世界的一帖良藥。盡管這個思想有著濃郁的理想主義色彩,但是并不代表它不深刻。人類的發展和不斷進步,不正在于有著理想之光的指引嗎?
徐志摩游學四方,滿懷“向中國人介紹西方文明,尋求理想之光”的熱情。此時的他受浪漫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對人生和社會都充滿了希冀和熱忱。因其單純,故行為恣縱,因而被社會所非議。在理想主義者徐志摩的心中,他是在為社會樹立追求理想生活的先鋒榜樣,而在社會大眾的眼中他的很多努力不過成為了茶余飯后的談資。除了個人生活上所受到的非議,此時的徐志摩也經歷著另外一層痛苦。其時的中國正內憂外患,處于生死存亡之危險關頭。徐志摩寫給表兄蔣復璁的信充滿了憤慨:“太丑惡了,我們火熱的胸膛里有愛不能愛;太下流了,我們有敬仰的心不能敬仰:太黑暗了,我們要希望也無從希望。太陽給天狗吃了去。我們只能在無邊的黑暗中沉默著,永遠的沉默著”。個人受到的誤會和遭遇的不順利,再加上目睹了殘酷的社會現實,他那激情熱切的博愛只能轉化為呼號和同情。
悲憫之下,徐志摩開始尋求走出苦難的道路。這條“愛一遭遇現實之痛一悲憫一尋找出路”的思想歷程也是托馬斯·哈代所經歷的。相同的處境和思想歷程正是徐志摩對哈代那籠罩著濃濃的悲憫意味的作品產生共鳴的原因,是他們結下文學因緣的基礎。
托馬斯·哈代生于英國西南部一個小村落。盡管家里拮據,但是熱愛文學和音樂的父母十分重視對小哈代的教育。從小在濃郁文學藝術氛圍熏陶下成長的哈代,漸漸地培養起了對文學的熱愛和敏感。父母給哈代講述故鄉多塞特郡的風物民俗和神話傳說。在小哈代的心里,種下了對故鄉和故鄉人民深愛的種子。在其六十年的寫作生涯中,哈代創作了大量以故鄉為背景反映農民生活的作品。
哈代創作風格的轉變明顯反映在他的小說作品里面。他的一生,共創作十四部長篇小說,四部短篇小說集。前期的作品洋溢著夢幻般的田園歡歌,例如《綠樹蔭下》《一雙湛藍色的眼睛》。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哈代所熱愛的田園生活在工業化的侵蝕下面臨瓦解,而故鄉的村民也被迫背井離鄉。此情此景,加上日益嚴峻的社會現實和階級矛盾,迫使哈代從田園夢里醒來,投身于刻畫底層人民的悲慘命運。《苔絲》和《無名的裘德》正是其中最出色的作品。在這兩部作品里面,哈代以滿腔的悲憫之心記錄了善良上進的年青人是怎樣被人吃人的社會一點點扼殺的。在《苔絲》一書的題目下面,哈代赫然寫上“一個純潔的女孩”,以示對殘酷現實的悲憤。因為對世俗道德觀的挑戰和作者對書中主人公的深切同情,《苔絲》一問世便成為了宗教道德家們攻擊的對象。然而,讓他們更憤怒的是,緊跟其后的《無名的裘德》文筆更是犀利,因而受到的攻擊更加猛烈。不但報刊上對《無名的裘德》的抨擊鋪天蓋地,韋克菲爾德主教還聲稱他焚燒了自己手中的一本《無名的裘德》,并號召其他英國人也這么做。然而,正是這兩本小說,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哈代在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鄉村青年裘德盡管出身卑微,并且常被取笑不自量力,但他一直沒有放棄他要進入基督城讀大學的理想,并且為此而努力鉆研拉丁文和神學。然而,他的理想逐漸被殘酷的社會現實擊碎,只能以石匠身份徘徊于高等學府之外。“讀大學不是適合你身份的選擇”,大學的教授們跟他說。另一方面,裘德與表妹的真心相愛也為宗教和禮俗所不容,最終裘德孤獨死去。
《無名的裘德》的故事,徐志摩想必是清楚的。他在1925年拜訪哈代的時候,問,“你小說里常有建筑師,有沒有你自己的影子?”盡管哈代給了否定的答復,但是任何一個讀過《無名的裘德》一書的讀者會輕易地發現裘德與哈代是多么的相似。像青年哈代一樣,裘德從農村進入城市當石匠,以修葺教堂為生:像青年哈代一樣,裘德自學各種語言,研修哲學和神學,渴望進入大學學習,也同樣夢想過能成為一名牧師;像哈代一樣,裘德對受苦受難的世間萬物懷有深深的悲憫。任何一個讀過《無名的裘德》的讀者也定能感受到哈代在字里行間對裘德流露出的感同身受的愛護和同情,還有哈代對那摧毀人性的社會制度的憤怒質問。
而徐志摩,也是一個志摩版的裘德。裘德身上體現的軟弱,他也有;裘德的敏感,他一定能捕捉到;裘德對愛的追求和在感情上受的苦,他一定也能理解:裘德在追求理想的路上所受到的阻礙和非議,志摩更是有著切膚之痛吧。“志摩啊你真不幸!志摩啊你真可憐!早知世界是這樣的,你何必投娘胎出世來!”裘德不是也發出過這么一句無可奈何的嘆息嗎?!
(三)
哈代后期的作品總被評論家們指責過于悲觀,而哈代也被貼上了“宿命論者”的標簽。在哈代的這些作品里面,不管主人公怎樣努力,但是好像總有那么一個“不知善惡,喜怒無常的主宰”隱身幕后,把主人公推向毀滅的深淵。然而,哈代所說的這個“主宰”,不見得就是人們普遍所說的“命運”。也許哈代是用了一種隱晦的說法,把這個“不分善惡,喜怒無常的”主宰指向當時殘酷無情的社會制度。如果哈代真的認為造成主人公悲劇的只是命運,那么,為什么哈代的筆墨都用來刻畫來自社會底層的人們的悲劇?難道上流社會的人就不會受命運的安排嗎?如果確實存在著這樣只壓迫窮苦大眾的所謂“命運”,那么,這樣的“命運”就只能是殘酷的社會制度!
哈代的悲憫和憤怒,徐志摩能懂。他深刻領會到哈代的悲觀后面的愛和勇氣。哈代的悲觀,是因為他看到了人間的苦難。他的悲的另一面是憫。徐志摩指出,“我想他的悲觀主義主要是由于他對人類和動物各式各樣生活的深切的惻隱之心,以及那種近于變態的同情心而引起的”,“哈代是他那個時代的思想領袖之一,是一個了解人類潛在偉大之處的社會向善論者,又是一個由于人類進步緩慢幾乎陷于絕望的作家。”作為受西方自由平等和人道主義博愛思想影響較大的一位詩人,徐志摩捕捉到了哈代悲觀面具下的實質精神正是人道主義。很多年后,我國哈代研究專家張中載先生也認為,哈代的“悲”“不是悲觀主義者的嘆息,而是博愛主義者的吶喊和對愛的召喚”。徐志摩對哈代的悲觀的慧眼獨到應該是兩者結下文學因緣的一個關鍵。
徐志摩在看出哈代的悲觀的實質的同時,還悟出了哈代的悲觀中潛藏著對光明的希冀。他說,哈代是“愛真誠、愛慈悲”“高擎著理想”,但哈代“不是完全放棄希冀”,“就在他最煩悶最黑暗的時刻他也不放棄他為他的思想尋求一條出路的決心——為人類前途尋求一條出路的決心”。而哈代在1895年寫的詩句“除非徹底的認清了丑陋的所在,否則我們就不容易走入改善的正道”表明,他所尋找到的出路就是籍著對現存不合理制度的無情揭露,從而摧毀舊世界建立新世界。
哈代的這個出路給了徐志摩無窮啟迪。他從中獲得了“靈魂探險”的勇氣。他要通過靈魂的冒險,深刻剖析自己,為自己的靈魂找到一條出路。因此相繼寫下了《自剖》和《再剖》。“我相信真的理想主義者是受得住他往常保持著的理想煨成灰、碎成斷片、爛成泥,在這灰這斷片這泥的底里,他再來發現他更偉大更光明的理想”。這想法和哈代的思想是何其相似!
哈代的作品有著無窮的魅力。這種魅力常常是一接觸他的作品就能被感受到的。而哈代的悲憫,和他揭露世界苦難所表現出來的不留情面和血淋淋,也給讀者強烈的靈魂觸動,為哈代贏得知音無數。而在眾多的知音中,就有一位叫徐志摩的詩人。他和哈代一樣,有著一顆熱切真誠的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