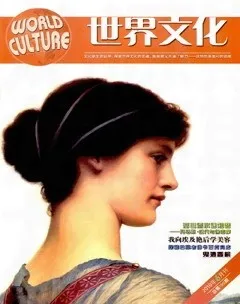《惡童日記》中的“病態”兒童
作家雅歌塔·克里斯多夫1935年出生于匈牙利的科澤格市。由于匈牙利發生暴動,她和家人被迫流亡,幾經輾轉遷居瑞士的納沙泰爾市。雖然她早年曾用匈牙利語創作并發表詩歌與戲劇作品,但是這些作品沒有得到太多反響。來到瑞士之后,背井離鄉的她曾在鐘表工廠務工,飽受流亡生活的苦痛。與丈夫離婚之后,她嫁給一位瑞士攝影家并開始學習法語,走上了法語創作的道路。她的首部小說《惡童日記》發表于1986年,引發轟動并獲得歐洲圖書獎。這部小說與后期的《二人證據》《第三謊言》一并構成著名的“惡童三部曲”,奠定了雅歌塔·克里斯多夫在當代文壇的地位。
其實,采用兒童視角來書寫文學作品,這一手法已經屢見不鮮。英國小說家狄更斯筆下的奧利弗-特威斯特,在倫敦遭遇了兒童犯罪等險惡社會現象,讓人記憶猶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保爾的《米格爾街》以少年為視角,記錄了特立尼達米格爾街區林林總總的苦難和無奈。英國當代作家伊安·麥克尤恩在這一方面也頗有建樹。他的《水泥花園》就呈現了當代英國社會中令人震驚的另類兒童。但是,有別于這些小說,《惡童日記》書寫的是二戰時期雙胞胎兄弟的故事。
戰爭的特殊語境讓小說披上了灰色的基調。因為戰爭,城市生活舉步維艱,雙胞胎兄弟因此被母親送往外婆家暫住。在大城市出生的雙胞胎無奈地接受現實,開始和未曾謀面的外婆一起生活。“外婆是我們母親的媽媽。”這樣一個句子,按照常理顯然多余,但是對于雙胞胎兄弟而言,這又是合情合理的,因為這就是他們認知世界的方式和邏輯。此外,這也進一步言明了他們和外婆的疏遠,也注定了他們之間的摩擦和沖突。
外婆邋遢、吝嗇、歹毒、貪婪,被外人戲稱了“老巫婆”,傳言稱她毒死了自己的丈夫。這一歹毒形象頗有點《格林童話》中邪惡巫婆的味道。她乖僻的性格導致母女關系極不融洽,也造就了這對雙胞胎的艱難窘境。在她眼里,雙胞胎兄弟就是“狗娘養的”。與這樣的外婆住在同一屋檐下,雙胞胎無法享受祖孫團聚的幸福,相反涉世未深的他們開始獨聞人生旅途。殘酷的現實逼迫他們自力更生,認識并適應世界。
外婆住在國境邊界地帶,物資相對較為豐富,但是她將一切物產都出售賺錢,只吃賣剩下的青菜水果。這種怪誕的行為源于她嗜財如命的性格。這樣的外婆自然會苛刻地對待兩個外孫,要求他們兩人干活,否則就不給他們飯吃,甚至會趕他們出去露天夜宿。不明就里的兩個孩子,忍饑挨餓,經過五天的觀察,立馬學會了操持家務農活,成為外婆的得力助手。他們勞作、修橋、捕魚,但是他們的勞動成果卻被外婆販賣。不僅如此,母親送來的衣物也都被外婆轉售。此外,貪婪的外婆毫無衛生觀念,從不注意個人衛生,更無暇為雙胞胎兄弟清理衛生。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原本潔凈的他們也變得骯臟邋遢,污穢的程度和外婆相差無幾。
除去外形上的污穢,這兩個孩子的精神世界也開始偏離常規。為了能夠更好地抵御外婆的虐待,他們決定要強壯起來,練習“互相打對方耳光”和“彼此互毆”。為了對抗外婆和陌生人的謾罵,他們練習相互辱罵,“字眼一句比一句更殘忍”。這一荒誕不經的邏輯,在這兩個雙胞胎之間又是那么的合乎情理。之所以這樣互相殘害,他們就是為了在那種特殊的環境中生存。為了適應戰爭生活,他們還開始“瞎子與聾子的練習”,訓練自己的視覺和聽覺,直到“不再需要拿頭巾遮住眼睛,也不需要拿草堵住耳朵”。為了忍受饑餓,他們“練習禁食”,兩天不吃東西。為了適應現實生活的冷酷殘忍,他們“練習殘酷”,開始殺生。這種病態的生存智慧滑稽可笑,但是又發人深省。
雖然這兩個孩子在外婆的摧殘之下痛苦地成長,但是他們并沒有完全灰心喪氣。盡管條件艱苦,他們兩個人克服困難,堅持閱讀學習與自我教育。利用他們自己帶來的大辭典和后來發現的《圣經》,他們給自己安排了“訂正錯字、作文、閱讀、心算、數學和背誦等課程”。難能可貴的求知精神讓他們保持了聰慧的氣質,也避免了他們的愚昧和沉淪。勞作與學習相結合,兩個“惡童”積極地應對這個世界的變幻。此外,他們的性格中依然保留了善良的一面。當鄰居的女兒“小兔子”受其他孩子欺辱時,他們出手相助;發現逃兵時,他們也毫不吝嗇地給予了幫助,提供食物,庇護他的行蹤;當“小兔子”母女在寒冬中煎熬時,他們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甚至“偷竊”和“勒索神父”,并對貪享奢侈的傳令兵大加譴責;甚至那刻薄兇惡的外婆受傷和生病之后,他們沒有袖手旁觀而是悉心照料。因此,可以說,戰爭讓他們變得殘酷,但是在這一層殘酷的外表之下,兒童的心靈還是天真善良的,對周遭的世界有著自己獨特的讀解,建構著自己的邏輯和善惡觀。正是他們難能可貴的善良感召了周邊的人,讓教堂的女仆、鞋店的老板和小鎮的居民對他們施予關懷。因此,雖然離別了母親,他們在鄉村苦中作樂,以自己獨特的生存法則存活下來。
與外婆的磕磕碰碰中,他們也逐漸習慣了這樣的生活方式,以至于不愿意離開外婆的屋子,不愿意和母親一起逃難。因為長期的疏離,母親在他們生活中的意義已經淡化,況且這種家庭環境也讓他們缺失了安全感,造成他們對親情的淡漠。傷心的母親不幸地遭遇炸彈襲擊,身亡離世。他們沒有太多悲傷,平靜地掩埋了尸體和炸彈造成的洞穴,輕描淡寫地說“一顆炸彈把院子炸出了一個大洞”。這樣異乎尋常的沉穩更讓人揪心,也間接地控訴了戰爭對家庭溫情的毀滅,扯斷了家庭成員間的情感紐帶。這一點在他們父子之間更為顯著和離譜。當他們和離別多年的父親一起穿越國境的時候,他們選擇了犧牲父親的策略。他們的父親用身體開路,引爆了深埋的地雷,掃清了障礙。雙胞胎中的一人就“踏過爸爸毫無生氣的身體”逃到另一個國家去,而另一個則返回外婆的屋子。
雖然沒有親歷戰場的血腥屠殺,但是雙胞胎兄弟在戰爭的后方也沒有幸免戰事的茶毒。他們健康成長的土壤已經被無情地鏟除。童年的記憶成了世事險惡,而要在那樣的環境中生存下來,他們無奈地蛻化成了“惡童”。然而,作家并沒有簡單地采取抽象人性論的觀點,將他們的行為簡單歸咎于“人性惡”:相反,她在具體的社會語境中探討兒童的成長和墮落。毫無疑問,小說敘事中直接與間接提及的戰爭成為主要因素,讓原本幸福的家庭四分五裂,讓親情冷漠,讓兒童視角下的社會充斥著種種病態。就連他們都鄙棄的惡婦外婆,與搶占葡萄園的軍隊相比,與強暴非禮“小兔子”的士兵相比,都顯得還有那么一絲人性的溫情。在這樣的環境之中,雙胞胎的“惡”就成了他們的武器和賴以生存的工具,只有這樣他們才能抵御外來的傷害。
這樣一來,他們的殘酷和病態也需要讀者辯證地審度。他們割斷了鄰居太太的喉嚨,用汽油燒毀了她們的房子。這樣的犯罪行為原本罪不可赦,但他們之所以這樣,是為了解除鄰居太太的煩惱,讓她和受到殘害而死亡的女兒一起得到解脫。這種邏輯,貌似荒唐,也不合乎法律規范,但是在戰爭的歲月里,它又不需要更多的解釋。因此,戰爭已經把毒害撒播出來,波及的范圍也不僅僅局限于交戰的陣地;后方的家園,同樣不能幸免戰火侵蝕。雙胞胎兄弟的戰時成長經驗就深刻痛斥了戰爭的滔天罪愆。
雅歌塔·克里斯多夫飽受戰亂的流亡之苫,把個人的經歷化作感人的文字。接受記者采訪時,她表示《惡童日記》就是以她自己和兄長為原型,融合了其他人的戰爭遭遇而鑄就的作品。通過雙胞胎兄弟的視角,她寫出了戰爭對人類的災難性的毀滅。戰后橫尸遍野的陣地或是瘡痍滿目的家園都已經是熟悉的災難形象,成為控訴戰爭的有力工具,但是小說《惡童日記》從“惡童”的視角出發,用他們的眼睛來觀察,用他們的語言來記錄。荒誕不羈的鄉村小鎮給我們帶來震撼,拷問世人的道德良知。雖然小說并沒有任何宏大的戰爭場面描寫,但是雅歌塔對小說的語言駕馭,讓一部沉重的作品通過兒童日記的題材來傳達,帶領讀者在閱讀的歡樂與辛酸中質問和反思。
在雅歌塔筆下,這對無名雙胞胎的形象,就和他們的名字一樣,從始至終都沒有清晰呈現。這也凸現了戰爭背景下個體的渺小和微不足道,更添一層憂傷的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