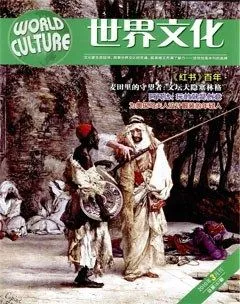“柳哥”
在多倫多,朋友們,特別是土木工程專業圈里的朋友們,都叫他“柳哥”。是不是太“民間”了點兒?
所以叫他“柳哥”當然有原因,一是與那些年輕的新移民相比,他年齡長了幾歲:二是他的為人處事。言談舉止,像個“哥”;三是外形上他實在不像個“知識分子”,叫“哥”更自然。
乍一見“柳哥”,倍覺熟悉和親切,像極了鄉下召集開會的莊戶人家的“頭兒”黝黑,精瘦,臉多皺,手粗糙,更惹眼的是那雙上世紀50年代流行的只有老頭兒才穿的圓口青幫布鞋。“柳哥”的口才極佳,是那種脂粉盡脫緣于鄉土狡黠詭譎可應付三教九流的口才。
果然,他真的是從村里走出來的。
“柳哥”叫柳中滿,遼寧人,具體說是遼西人。生在鄉間,長在鄉間,初中畢業后,回到鄉間當了兩年的生產隊長。1977年全國恢復高考那年,他沒敢報考大學,只報了中專,但卻因分數出色被大學搶了去,成了東北林業大學土木工程系學生,也是村里以及家里多個兄弟姐妹中唯一的大學生。小時候的好學生,大學也是,而且是學生會干部。畢業時,系主任對他說:你想上哪里工作?跟我說一聲。但他沒有說,因此也就沒有進大城市。時至今日,他還在想:如果當初進了大城市,也不知道現在我是個啥樣兒。
畢業后的“柳哥”一直在土木建筑工地進進出出,壘高樓、架橋梁、鋪公路、蓋廠房……積累了二十多年的技術和經驗,技術職稱和行政職務節節升,出國前,已經是正教授級的高級工程師,正縣級的領導干部,以多重身份、多種角色宏觀策劃,綜合實施,現場指揮過多項大型工程建設項目,管理、技術、政策爛熟于心到了只用三分之一的腦子就會有圓滿結果的程度。臨出國前,他正在“高速公路”建設項目上任項目經理。
這都是“柳哥”過去的事情了。
都是同胞 互相幫幫
結識“柳哥”,是因為人們在說加拿大中國專業人士協會有個土木工程分會,它吸引了很多“土木人”,幫助沒工作的找到工作,有了工作的提高水平,一些迫于無奈已經改行的重歸土木工程這一行。
“柳哥”移民后一番周折找到了同專業的差事,但那差事學學徒就能勝任,不是他這等人應該干的。有了工作的“柳哥”身邊聚了一群具有同樣專業背景的朋友,他想號召有工作的來幫幫沒工作的,“咱們都是同胞,互相幫幫。”“柳哥”常這樣說。
同是土木專業人士的馮建德找到“柳哥”說,咱們是不是成立個組織,把學土木專業的人組織起來,互相幫助幫助,要不你是學醫的,他是算賬的,這些人跑到一起能干什么?還是同專業的人士在一起能交流信息。
土木工程分會成立了,“柳哥”毛遂自薦當副會長,他說,會長要由注冊的專業工程師來做,而我不是,我來當副手,扶植會長,他把關,我張羅。
專業人士組成的專業分會出手不凡,一“開張”就賓客滿棚。在一個月舉行一次的活動中,講座,屢屢百多人參加;培訓,走廊也站著人,所有的課題都是土木專業人士的關切所在。“柳哥”自己也去講,講“怎樣找到第一份專業工作”,講“怎樣才能保住第一份工作”。所謂經歷、經驗、警示、告誡都出自他的生花妙口,大家捧腹也受益。他說:“每次講座、培訓結束后,大家不走哇,嘮啊嘮啊,那我們就提供個機會,讓他們嘮去唄。”為讓大伙盡情地嘮,他們組織了野外聚餐交流活動,一百多號人來了,拖家帶口,男男女女,頂著大雨,在野外公園嘮了半晌的嗑兒。
土木工程分會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共同尋找工作機會,相互傳遞信息資源,他說:“土木工程方面的公司經常有人走,老板不可能都發廣告,要是那樣,‘咔嚓’來了100份簡歷,看得過來嗎?小公司更沒專人看這東西。哪家走人了,說句話,我們的人可以頂上去嘛。”
專業人進入專業領域的敲門磚就是那張“簡歷”,“生”與“死”都維系在那張紙上,很多人懷揣“絕技”卻因那張紙寫的不夠“技巧”而不得其門而入。土木專業也是如此。“柳哥”說:“我們的會長不是注冊工程師嗎?他有資格推薦專業人士去建筑等公司工作,他簽字推薦的人一報一個準兒。為什么呢?因為他推薦你之前,一定要幫你把簡歷修改成用人公司需要的那樣,本土化,專業化,讓你的簡歷里的用詞金山詞霸里都找不到,在電腦上打出來下面都會畫出紅杠杠。這樣的簡歷,人家當然滿意。
“柳哥”專門組織了怎么寫簡歷講座,請會長主講。“柳哥”對效果很滿意,他說,會一散,哇,人們‘呼啦’一家伙全‘唿’上他了。以后很多人都找他看簡歷,改簡歷,都是在業余時間,這也不是個事兒啊,會長不愛支聲兒,我們得想個辦法。”“柳哥”開始替會長發“愁”了。
“有啥事兒。說。”
更多的人認識了柳哥,他經常接到求助、報喜、泄憤的電話,電話總是這樣開頭:“柳哥嗎?我是xxx……”柳哥也總是回答:“啊,你是xxx哇……”嘴上說著,腦子轉著:“xxx?我‘存’盤了嗎?‘存’哪兒了?”在“搜索”的當口,他總習慣地跟上一句:“有啥事兒,說。”這一“說”,“說”出一圈兒朋友。
呂鵬是個剛剛30歲的小伙子,移民后,在一家工廠做櫥柜臺面的labour工。他不甘心專業就這么丟了,想進社區學院重新學一遍“加拿大的土木技術”。鬼知道,天下的土木技術有何根本的不同?!蓋樓不都是先刨坑再打樁?!如果說不同,不是技術而是標準,標準是不用進學校學的。可小伙子這幢在“中國蓋的樓”不拆了重蓋,“賣”不上價兒呀!正當舉棋不定之時,他去聽了一次土木工程專業分會的講座,認識了“柳哥”。
都是“土木人”,都是東北人,都是遼寧人,說啥都親切,自相識以后,倆人經常湊到一起說說話。一天,“柳哥”的一個朋友打電話對他說,他要離開他工作的公司了,讓“柳哥”介紹一個人過去。“柳哥”說:“OK!沒問題!”扭過頭去,對坐在旁邊一籌莫展的呂鵬說:“你去!”機會就這么來了!什么叫大喜過望,那個時刻,就是,對他們倆來說,都是。
呂鵬去試工了,但不到一星期,老板對他說:工地反映你語言不行,我不能用你了。呂鵬對老板說,再做一星期,不行,我走人。那一周,小伙子拼了命了,把工作完成得漂漂亮亮,不懂的就問“柳哥”:“柳哥,路基的夯實度怎么做才能達到精確的數值?”“柳哥”在電話里說:“夯實標準和咱國內不一樣,是不?那你就……”“柳哥,現場混凝土檢驗有點問題。”“別著急,你先這樣……后那樣……”第三周,考試通過CSA證書,小伙子真爭氣,考了個前幾名,一切問題就此解決了,公司給小伙子配備了手機。
呂鵬非常感謝“柳哥”,他說,是“柳哥”幫他找到了機會,是“柳哥”幫他解決技術難題,是“柳哥”的鼓勵使他心里有了底。
有個叫劉博的“土木人”來加拿大半年了沒認識一個本行的朋友,轉來轉去地找,通過這個認識那個,通過那個認識這個地結識了“柳哥”。他對“柳哥”說:“我發了好多簡歷,都石沉大海,看來沒什么希望了。”“柳哥”要幫幫這個有點兒垂頭喪氣的小老弟。他馬上聯系馮建德幫劉博修改了簡歷。一周內,信息回來了,一天3個面談,最后聘用他的那家公司老板只問了兩個問題:做過什么?還做過什么?
現在劉博的工作位置高了,工資長了,他也成了土木工程專業分會的積極分子,幾乎參加所有的活動,還掛著個照相機,跑來跑去地照相,給“土木人”留個影,也站在臺上“講課”了——“如何找專業工作”。
“你就是語言不行啊……”老板很遺憾
“柳哥”說,很多人聽了我們的講座,經過我們的培訓找到了工作,有的做到了更高級的位置,也有的進了政府部門。我們會員中很多是博士、碩士,又年輕,英語又好,只要給他們機會,他們就如魚得水,會“蹦”得很高。我是那個“蹦”不高的人。
“柳哥”一肚子的“專業技術”讓那張嘴牢牢地封住了——他說,他英語不是很好:“其實,我天天都在學英語,只要開車就聽磁帶,沒事就在家晃著腦瓜兒背單詞,可這個門怎么就關上了,進不去了呢?”特別是剛到加拿大的那段時間。
回憶起當初找工的時候,他樂了,說,我準備得很充分了,可人家問的有的我還是沒聽懂,又不能總“pardonme”,我就“蒙”,當然“蒙”不過去了。我還接到過一個可能是約我面試的電話,人家問:“How are you doing?”當時我正在睡覺,我就說:“I amsleeping。”人家說:“謝謝,再見。”最后一次見工,他們把我放在一間小屋里等著。我從不信什么教,但那天我什么教都信了,在心里又是祈禱又是拜,只求兩條,一是不要問我太難的問題,二是給我一張伶俐的嘴說好英語,哪怕就一會兒也好。老板進來了,第一句話就是“你說說你自己。”我張口就講。老板說:“你英語不錯啊。”我心里想,敢情,我都背了100遍了。那天還真行,還和老板聊了會兒天兒。老板說去過蒙古,他找來一張地圖,我就在上面指指點點說,談興正濃,老板突然問:“你想要多少錢?”我說了一個小數兒。到家不一會兒。電話來了,讓我第二天去上班。
第二天,他們把我扔在工地上,沒有圖紙,嘴不能說,字不認識,儀器咱也整不明白,老板下午3點還要來驗我的工,那真是叫天叫地都不靈。我就戴著安全帽,穿著黃馬甲,一身工裝地躲在一角兒整那儀器。后來,我猛地省悟了,我不懂他們的那套,可我懂工程,懂工地呀,這塊“yes”那塊“no”不就得了?!我就以眼睛為儀器,巡視了一遍工地,老板來了,我匯報了,老板說:very good。
“柳哥”工作的是一家工程咨詢公司,他是工程檢測人員,每天“長”在工地上,檢查混凝土的塌落度、含氣量、溫度,路基填筑壓實質量等技術指標,自己的車就是自己的辦公室,沒事坐在車里,有事跑出去取樣兒,不管是刮風還是下雨。工地是多種多樣的,公路、橋梁、商業區、工業區、住宅小區;工地是流動的,幾年來圍著多倫多東西南北跑了不知多少遍。
跑工地對人生地不熟的“柳哥”來說太難了。老板一個電話,開車就得走,老板路名說得快,也不說明方位,他又不好多問,即使問了也聽不懂,所以只有先“OK”,再想辦法查地圖,有時還得提前一天去找。一次,他清晨六點多往他覺得是正確地址的工地趕,準時到了,但不對勁兒,那里是靜悄悄的一片住宅,工地在哪兒?他就豎起耳朵聽,工地是有聲音的,那聲音他熟悉的很。是過來的一輛truck把他引進了工地。進入工地還必須確認是不是你公司負責的工程,一上陣就開檢,白給人家忙活了的事兒不是沒有發生過。
幾年過來了,現在的“柳哥”完全被老板接受了,“把我放在工地上,他就放心了。幾年來,我從來沒把老板整到工地上去,也就是說,從沒給老板添過麻煩。”他的老板很滿意,但也很遺憾,總說這么半句話“你就是語言不行啊……”“柳哥”自己何嘗不曉得?
誠實,取信于人
跑工地,沒有人監督,上下班,特別是下班時間全由個人掌握。“柳哥”幾乎全部是干滿點,工地沒活兒了,看看表,還早,再跑一個工地,或者到實驗室去做做實驗。緣于此,老板很信任他,即使他偶爾不實事求是了,老板也相信他是實事求是的。他經常告誡那些“腦筋靈活”的年輕人,在信譽這個問題上耍不得半點聰明,即便不講做人,也要從保住工作考慮,否則早晚會吃虧的。
產生信譽,是一個過程,其中……“柳哥”曾受過一次工傷,扭傷了腰。保險公司來一個電話,問:傷在哪里?他說明了,支票就過來了。有人對他說,歇歇吧,反正有保險嘛。但他聽了一位老中醫的話:別動,躺著,請假一周,我能給你治好。一周后,他扎著護腰上班了。保險公司難以置信,老板和工頭也很驚訝,都跑到工地去看他。真傷假傷就此歇下去吃保險的不是沒有啊!
信譽是神圣的,也幫他承載后果。“柳哥”給公司損壞了一臺儀器,老板曾反復強調,這臺儀器不能離開你半步,因為它貴重,因為它放射伽馬射線。那天,儀器被工地的卡車壓壞了,“柳哥”也有責任,很不安,但老板對他說:“你沒有錯,如果有錯,大家都有錯誤。”老板能和自己共同擔待,“柳哥”很知足。
“柳哥”是公司分公司唯一的中國人,想學點兒什么,或不想孤獨,或者說被那些小鎮來的、口音很重、說話粗魯的工人接受,就必須和他們一起談冰球,一起聊女人,一起罷工,甚至一起罵街。“柳哥”經常端著杯咖啡湊到他們的堆兒里去,其實他不喜歡咖啡那玩意兒,他說:“喝完了,心里直撲通。”老板喜歡他,時不時地找上他一起上餐館。第一次,“柳哥”說他請客,人家說:不用,公司出錢。第二次是中國餐,“柳哥”理所當然地想做東,但還是被拒絕了。第三次,他不帶錢包了,可人家卻說,大家分攤,他狼狽了。至今他也沒搞懂這是啥規矩,但再也不敢不帶錢了。
和“柳哥”聊天的幾個小時,他不斷地重復著一個意思:我真的沒有成功,寫我什么呢?
但,還是寫了。誰也沒有規定必須寫成功的,再說,誰也說不清何謂成功。
“柳哥”的結束語是“我會修房子,我會剃頭,那時候一家伙一氣兒剃十幾個腦瓜兒,我還會做大醬,積酸菜,磨豆腐,啥時候請你吃我做的豆腐,比外面的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