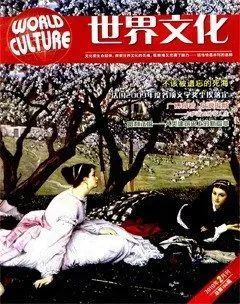荊棘地里的詩意
在西方電影界,有一個神秘而充滿傳奇色彩的科波拉家族,中流砥柱是拍過《教父》系列和《現(xiàn)代啟示錄》的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他的父親是為《教父》系列譜曲的卡邁恩·科波拉,他的女兒索菲亞·科波拉以《迷失東京》在好萊塢一鳴驚人,他的侄子是尼古拉斯·凱奇,原名尼古拉斯·科波拉,因為不堪家族重壓而改了姓,并以影片《離開拉斯維加斯》獲得第六十八屆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科波拉家族以意裔美國人的身份締造了好萊塢神話,成為電影史上一段魅力無窮且被不斷釋義和書寫的傳說。
而在東方電影界,同樣有一個家族聲名顯赫,他們所創(chuàng)作的影片形式與風格恰可以同科波拉家族的影像形成一種參照,他們就是伊朗的“馬哈馬爾巴夫之家”。與科波拉家族的雄厚經(jīng)濟實力和久遠家族歷史相比,馬哈馬爾巴夫之家更顯精神獨立,他們在資金不足和政治重壓下,創(chuàng)造的是在夾縫中求得生存的個人心靈世界。
馬哈馬爾巴夫之家的主力是與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齊名的穆森·馬哈馬爾巴夫,他年輕時曾因捍衛(wèi)伊斯蘭教義遭受拷打和監(jiān)禁,五年的牢獄生活讓他深感伊朗的根本問題在于文化,于是投身電影創(chuàng)作,拍攝了《流動的商販》、《意中人的婚姻》與《時光》等影片,是伊朗知名的電影人與社會活動家。穆森在1993年成立了“馬哈馬爾巴夫電影學校”,由于伊朗當局阻撓,學校只得招收家庭成員與親朋好友,但正是在這種手工作坊式的條件下,馬哈馬爾巴夫之家創(chuàng)造了電影史上的奇跡,到今天為止,共培養(yǎng)出一位攝影師、一位錄音師、一位美術(shù)設(shè)計師、三位導演與一位圖片攝影師兼剪輯師。
而其中最為耀眼的、取得成就最大的是被稱為“沙漠玫瑰”的薩米拉·馬哈馬爾巴夫,她是穆森的女兒,年僅17歲的時候就以處女作《蘋果》驚艷法國戛納電影節(jié),而她的第二部作品《黑板》更是獲得2000年戛納電影節(jié)評委會大獎,為本已久負盛名的伊朗電影增添了創(chuàng)作的活力和影像的深度。
其實電影史上不乏女性導演取得杰出成就,如法國的瑪格麗特·杜拉、印度的米拉·奈爾、新西蘭的簡·坎皮恩以及香港的許鞍華等都以女性細膩深刻的筆調(diào)描繪了一個個感性豐富的內(nèi)心世界,比起男性導演來,她們會更加關(guān)照生活的細節(jié)與生命的微妙誘人之處。而薩米拉的《黑板》卻是一出不折不扣的民族寓言,是關(guān)于伊朗政治拷問與民族前景的悲歌。20歲的薩米拉還是一個青春期的女人,但拍的片子在氣質(zhì)上卻是成熟女性的感悟,又帶著中東式的詩意,如果說在每個人的青春期里,都停留過顆大師般的敏感心靈,那唯獨薩米拉這顆,更多的帶著理性思考與審視。
影片在結(jié)構(gòu)上延承了以往伊朗電影《何處是我朋友的家》、《櫻桃的滋味》、《小鞋子》等影片的精致雋永,只不過主人公已不再是天真可愛的兒童,而是在戰(zhàn)亂頻繁的庫爾德地區(qū)背著黑板到處尋找學生的兩位教師:薩義德與瑞波爾。影片的超現(xiàn)實意味在這個敘事的設(shè)定中就已彰顯,在我們的概念中,只有學生自主進入學校學習的事實,而沒有老師去“求”學生跟著自己學習的偏執(zhí)。但恰恰這又是一部最具現(xiàn)實主義風格和內(nèi)容的電影,影片采用了各種紀實主義手法,如長鏡頭、跟攝、肩扛攝影以及同期聲的運用,都顯示了薩米拉場面調(diào)度的非凡功力。此外,影片中由陽光所造就的光影變化,濃稠的大霧以及高亢的《古蘭經(jīng)》吟誦聲交織成的審美意蘊,更是營造出一種亦真亦幻的景象。
“薩義德的婚姻”與“瑞波爾的學生”兩個段落可以被視為整部影片的敘事核心。兩位教師在岔路口分別,有了各自不同的經(jīng)歷,薩義德遇上想要跨過邊境回到伊拉克的庫爾德難民,HOivTs2I+IW2M86OPLnZjlR8uLmBWJnsv3ZvN+Q9XW4=而瑞波爾遇到的則是在邊境上走私貨物的“騾子”——一群佝僂著背、雙目無神的少年。
薩義德與難民群中唯一的有三個孩子的女人結(jié)了婚,結(jié)婚儀式滑稽而荒誕,以黑板為屏障,這邊是薩義德企盼的眼神與惴惴不安的慎重心情,那邊是女人無所謂的表情與引導她孩子撒尿的噓噓聲。主持婚姻的老者用拐杖敲敲黑板,禮畢,他們成了夫妻。沒有所謂的青梅竹馬或一見鐘情,更何談愛與理解?但薩義德卻馬上積極背負起作為丈夫和繼父的責任,無微不至地照顧女人和她的孩子。當然,他也要行使他作為丈夫的權(quán)利,當難民們停留休息,薩義德把他與女人用黑板隔絕在一方“私人天地”時,作為觀眾的我們按照好萊塢的思維方式心領(lǐng)神會微笑。卻不料,劇情陡轉(zhuǎn),鏡頭移至黑板另一側(cè),卻讓觀眾發(fā)現(xiàn)一幅令人啼笑皆非又心酸不已的畫面:有些癡傻的女人躲在角落里自顧自地啃著食物,而薩義德卻用粉筆在黑板上認真寫下“我愛你”,試圖用更文明和更深層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關(guān)系,薩義德說,跟著我讀:“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但女人始終只有沉默。當薩義德領(lǐng)著難民到達邊境,兩個都不愿背離祖國的人平靜地離了婚,黑板作為婚姻唯一的見證被當作嫁妝送給女人,然而,“半路夫妻”的灰色幽默卻在薩米拉的鏡頭下久長得令人感慨,一副黑板,承載的是一段萍水相逢的感情,是流水落花的無奈,也是薩義德深深的愛。
比起薩義德,波瑞爾作為教師的責任感更加堅定。他以頑固和耐心的態(tài)度緊緊追隨那群被稱作“騾子”的少年,當少年們?yōu)槎惚芩巡犊癖紩r,波瑞爾也背著黑板不要命地逃逸;當少年們停下來休息進餐時,他卻餓著肚子孜孜不倦地一遍又一遍游說。終于,有個少年同意波瑞爾來教他,這對于波瑞爾來說,無疑是巨大的肯定與鼓勵,他們在陡峭的崖間學習如何發(fā)音,在僻靜的小道練習寫字,縱然是騾子一般的生活,此時也充滿令人歡欣鼓舞的希望。可就在好學的少年在黑板上學會寫完自己的名字時,一聲尖銳短促的槍聲,擊倒了少年,波瑞爾的心血與無限動力,也被冷酷地屠殺,終結(jié)在這里。
或者薩米拉以交叉蒙太奇的方式講述這個故事,就是為了證明某種愛與文明的可能性。因為有愛,才會有包容和理解:因為有文明,才會有前進的希望。然而,處于宗教紛爭與頻繁戰(zhàn)亂的伊朗社會現(xiàn)實擊碎了愛與文明的夢想。因為不同國別與民族,所以薩義德與女人注定分離,因為缺少孕育知識的環(huán)境,所以瑞波爾試圖以文明的象征——黑板來拯救那些少年的想法,也成為空想。
薩米拉以不動聲色的客觀鏡頭和質(zhì)樸簡陋的影像表達,暗喻了整個伊朗民族進退維谷的尷尬處境,就像那群迷失在大霧中的庫爾德人,既難以找到何去何從的方向,又在方向中迷失方向,因為就算找到了方向,或許也并不是美好的開始。而更為值得贊賞的,是影片中流露的“真實的幻覺”,常常會令我們處于現(xiàn)實與超現(xiàn)實的雙重境地,這是一種人類普遍情感的外泄,是荊棘叢中生出的無限詩意,更是薩米拉在民族寓言上超越表層伊朗現(xiàn)實而上升至全人類命運的真切詢問:真主安拉,你在哪里?伊朗人的未來,又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