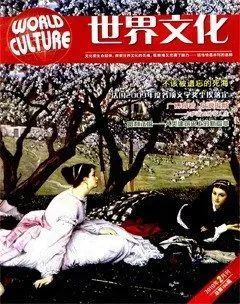當生活狠狠地拋來一個球
那是1987年,我才九歲。站在位于俄亥俄州哥倫布城,我家附近的一條小路上,我小心翼翼地把唾沫抹在我嶄新的壘外球員專用手套里,怕球打疼父親。離我20碼遠的地方,父親赤著手匍匐在礫石上,對我喊道“托米,把球扔過來!別擔心我疼,不會傷到我的!”
可我還是怕弄疼父親,就像打柿花球一樣,把球緩緩地打了出去。
“小毛頭,用力一點!”他叫著我的渾名。他知道這樣叫我會把我氣得臉紅脖子粗,一怒之下用力把球投向他,這倒會正中他的心意。“你這個沒出息的!”
我氣得緊緊捏著球直到手指發白,還帶著一絲惡意狠狠打量著對面的父親。我鼓足了勁,更多的是出自憤怒和羞愧,而不是靠肌肉力量和控制能力,用力把球投了出去。而我投球的目標,也不是父親已經擺好接球姿勢的雙手,而是他兩眼正中間。這球投得非常刁鉆,在球以高過他的頭六英尺,即將飛過的一霎那,父親用雙手接住了。之后,他若無其事地把球投還給我,平靜地說:“這次好一些了。現在投低一點吧。”
我出于一種報復心理學會了打棒球。我投身于運動中,而且摔壞了5根骨頭。而這是直到我19歲時,一次突發事件后做檢查,醫生對著我的×光片一臉苦相,我才知道的。當時,我仿佛又回到了哥倫布城的那條小路上,還是那個努力著要超過父親球技的小孩子。
做兒子的總是很難完全理解自己父親。我們背負著父親的期待,顛簸著前進,跌倒了又爬起來:總是在自我懷疑中郁悶,在阿諛奉承中掙扎。因為受到批評所帶來的刺痛,以及沒有得到表揚的失望,我們幻想著怎樣報復。總是想象著擁有一個更有眼力的父親。也曾經在白日夢里,勾勒出一些英雄主義的行為,比如迫使自己的父親跪在地上一~在當時的我們看來,這是讓他們能夠平等看待我們的唯一辦法。
其實父親并不像兒子眼中那么高深莫測。我的父親是一個礦工的兒子,和我一樣,在他的成長過程中,也不知道自己在父親眼中是什么地位。但是父親就差沒有改變自己的血型,來說明我不是他的兒子。他靠嘲笑愚弄他的兒子們,以使我們的外殼鍛煉得更加堅強,磨練我們的不足之處。他滿心希望,我們最終能夠通過向他的權威地位揮舞拳頭,以表示我們已經長大成人。
17歲的一天,我長大成人的時候終于到來。我坐在飯桌旁,用一些無禮的言語激怒了父親,他突然跳了起來,把我嚇了一跳,然后,他答應和我出去到房子外面解決。當他再次用“沒出息的”這個詞語奚落我,這次我是帶著同情看著他,而不是出于憤怒。他能夠應付我對他滿心怨憤,但是無法應付我的滿懷同情。
那之后,父親勉強接受了我長大成人這一事實。但一直到我高中畢業兩年后將要服兵役時,我和父親都還是很難把對方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與實際生活中的本來面目結合起來,找到一個平衡點。直到現在,有件事情還深深地印在我腦海里。那是1999年,一個秋目的下午,我們一道外出打獵,想借此緩和兩人的關系。
如果那天我們僅僅是熱衷于找尋獵物以供娛樂,那可真是要白白浪費一個下午了。當時,我將要動身,奔赴戰場。而那種表達親熱感情的詞語對于父親來說,就如同說阿拉伯文那樣困難;盡管如此,他還是在盡力讓自己說點什么。
我們在叢林中找到一片空地坐下,望著遠方。十月黃昏的天空,將最后一道光慢慢吸去。那種沉悶的氣氛簡直讓人無法忍受。在這種沉默持續了太久后,我們回到車上啟程返家。剛開始那一會兒,誰都沒有說話。途中,父親一邊掌著方向盤,一邊盯著汽車前方的緩沖器,終于說了出來,“托米,我想讓你知道,一直以來,我都為你自豪。如果有任何辦法能夠讓我代替你上戰場,我都會去做的。我會想你的。”
我一直沒有完全理解父親說這些話意味著什么,直到多年以后,一個朋友向我追述起在我上戰場期間,一件發生在酒館里的事情。“你父親當時正在玩賭錢,”那個朋友詳細說道,“然后一個愛搬弄是非的家伙一一是個大塊頭——正好講起了海灣戰爭。這家伙的兒子當時正在讀大學,他最后說:‘哎,人們總是要把那些更聰明的孩子留下來保住,今后用來建設國家。’他無法理解這句話對你父親有多大的傷害作用。我還沒來得及拉住你爸爸,他就已直穿過那張賭桌。他個頭雖不及那家伙的一半,卻用繩子把那個賭錢用的圓盤機綁在那家伙的喉嚨上,想要把他憋死。后來我們整整四個人,好不容易把你爸爸從那家伙身上拖開。”
“那年你走了以后,”他補充說道,“每當有一輛軍車回到街上而沒有你的出現,你爸爸身體中似乎又有一部分衰竭了。”
—直以來,父親向我掩藏了他對于我可能無法從戰場歸來的擔心。當我結婚以后結束了我的軍隊生涯,他也默默地掩飾了他的失望。直到最近我才明白,當他看見我身著制服時,為什么會那樣自豪。
今年年初,一個堂姐給了我一封信,那是50年前父親剛被招募進海軍時,寫給她父親的。信從德克薩斯州的海軍飛行基地寄出,滿滿兩頁信紙,洋溢著他要做一名海軍飛行員并將終身奉獻于此職業的熱誠希望。
“我們能夠隨時和飛行員一起翱翔天空,”他在信中吹牛,“我們在海灣游泳,將旋轉輪固定在水上飛機上,再把飛機固定在岸上的一個運輸機上。我們把它們拉上正常的軌道,沖走機身的鹽水,給發動機加油、檢修……”在后面的文字中,他詳細講述了將要一輩子獻身戎軍生涯的宏偉目標。
當年,他19歲,單身—人。他的父親當年迫于家庭原因,13就輟學到煤礦工作。在海軍生涯里,父親隱隱約約看見自己光明的前程,它閃耀著光芒,會遠遠勝過他的父親。
然而,在寄出這封信不久,經過飛行訓練后,他被海軍否決了,不能做飛行員。之后他申請加入潛水艇駕駛學校,而在嚴格的身體檢查中,卻發現他的心臟有細小的雜音。他不得不手里攥著僅有的一張軍隊發的票,坐上了回家的火車。
這封信幾乎向我解釋了一切。當父親離開軍隊回到俄亥俄州時,心里本來是沒有任何要返回的意向。命中注定,讓他整整三十年都在修理廢棄的卡車,還要艱難撫養六個孩子長大,這不是他一生的夢想。他那破滅的夢想讓他一生痛苦,而他采取一種扭曲的方法,用那種激烈的批評語言,想要激勵自己的后代不要重蹈覆轍,走他和他父親的老路。我疊好那封信,心里想,這也就是父親總愛罵“沒出息的”這些詞語的根源吧。
父親過世時,我不在家鄉。隔壁鄰居打來電話,通知我父親突然心臟病發作,非常嚴重,母親希望我立刻趕回家去。電話斷了好久后,我才反應過來電話那頭說了什么。
第二天一大早,在開車直奔俄亥俄州的路上,我想起了23年前小路上的那場球。我是那樣迫切地要在他的腦袋上打一個包,以解我心頭之恨。為什么兩個如此深愛著對方的人要采取如此迂回、孩子氣的方式來掩藏彼此的感情呢?我想,父親去世的時候,是否知道我有多么在乎他,在乎這一切。
又想到了父親說的,“沒出息的”,我不由得面帶微笑。我緊緊握住方向盤的手指關節已經發白。方向盤,帶我回家吧!就這一次了,帶我去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