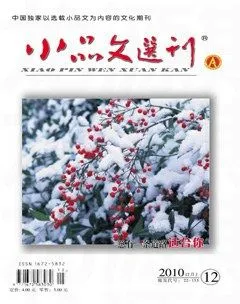蒼
現在,我想說說家鄉隨處可見的一種野生植物,它的名字叫——蒼耳。
在贛西,這是一種不論土地貧瘠,到處茁壯生長的植物。在我的印象里,只要是能長野草的地方,就一定有蒼耳。不過,在我們的口中,它不叫蒼耳,而叫“野紫瓜苗”,它的果實,我們叫作“虱婆”,與植物典籍中蒼耳的一個別名“虱麻頭”倒有幾分相近。
大概三四月間吧,蒼耳苗從土里冒出芽來了。這個時候,如果在菜地里發現了它,一定要馬上拔除,否則過不了多久,它就將開始肆無忌憚地生長了。
但是,蒼耳是那么多,田間地頭,到處都是,仿佛莊稼人勤勞除草的雙手總也清除不了它們一一事實上,我后來發現了,它們家族興旺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學會了避開農民種植稻蔬的土地,扎根到那些長滿雜草的荒地或者無人耕種的路邊空地。這樣一來,蒼耳成了無人管無人問的孩子,自然也就逃離了被刈除的命運,并且不斷繁衍。
它是那么壯實,與我們這些窮苦人家的孩子倒有幾分相似,再怎么貧瘠的土地也能扎下根來,結出果實。精心施肥的蔬菜還沒見怎么長呢,菜園邊上沒人理會的蒼耳卻在幾場雨后長得老高了。一開始,它呈卵狀三角形的葉子當然是鮮嫩光滑的,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葉子和莖稈都越來越粗糙了,葉子的兩面都顯出糙伏毛,葉柄也密被細毛。
然而這么一種毛糙的植物,卻帶著中藥的血統。蒼耳入藥當然已經有著很久遠的歷史,《別錄》、《藥性論》、《千金》等等書籍中都有關于它的記載條目。但作為藥材的蒼耳卻并不是因為這些醫書進入我們的記憶,而是因為鄰家某一個拉肚子或者生了疥癬的孩子。記憶中,鄉親們有了類似癥狀,常常便是在某個清晨或者結束勞作后的黃昏中跑到村頭荒地里扯一株蒼耳的莖葉,或者熬成藥湯,或者直接搗爛后涂敷。兩天下來,不花費一分錢,病癥便好了。那個時候,很多窮苦的村民們都曾受益于蒼耳。
等到九月份,蒼耳的植株已經有一米高了,一簇一簇的蒼耳果實(蒼耳的果實也叫蒼耳!)開始成熟。蒼耳是紡錘形或橢圓形的,表面有鉤刺,頂端有2枚粗刺。我曾經很認真地與小伙伴們討論過,這兩根粗刺究竟有什么特別的作用,但是最終也沒討論出一個結果來。隨著季節的更替,慢慢的,蒼耳由青轉綠,最后轉黃,變黑。這個過程中,成熟的刺果就很容易脫落了,人或者其他動物從蒼耳植株邊路過,褲子或皮毛上往往就會黏上不少蒼耳。植物書上說,這是植物藉以將種子散布他處的一種方法。這真是一個奇妙的事情,蒼耳以及其他很多植物自己不會行走,它們的種子卻能行走到很遠的地方。有時候我也想,要是哪一個褲腿上黏著蒼耳的農民跑到了百里之外的地方,然后不經意間將蒼耳抖落了下來。不知道這個孤獨的蒼耳孩子會不會想念百里之外的母親和兄弟?如果恰好這個地方也有其他蒼耳的話,又會不會欺負這個獨自流落異鄉孱弱而悲傷的蒼耳孩子?
蒼耳的孩子沒有回答我。而人類的孩子們對蒼耳卻是情有獨鐘。蒼耳成熟的季節里,孩子們紛紛跑到荒地里去采摘,然后團成一大團,帶到教室里去,偷偷扔到別人的衣服或者頭發上。衣服上的蒼耳很容易就拿掉,男孩子頭發短,黏上幾個蒼耳也容易摘除,但是留著長發的女生可受了罪。到后來,這種惡作劇式的游戲逐漸便演變成男生欺負女孩子的一種專利了。我記得讀小學時,班上的男同學們總是會在某一個時候出其不意地抓一把蒼耳扔到某個女生的頭發上,然后跑過去,抓住頭發猛揉幾下,讓亂成一團的頭發與蒼耳糾纏得更加復雜。遇襲的女同學拼命想將頭發從蒼耳的鉤刺中解救出來。但是,最后的結果往往是蒼耳從頭上摘掉了,但摘下的蒼耳上還纏著幾根糾結的斷發。這種游戲因為太過普遍,受害者的回擊又是那么無力,幾天下來,班上所有女同學便幾乎都領教了蒼耳纏咬秀發的厲害。只有學習委員除外。在小小年紀的同學們心目中,學習委員是班上最漂亮也最高傲的一個女生。她的成績總是在班上的前兩名,而且,她的潑辣讓每一個與她同桌的男生幾乎都哭過鼻子。所以,班上沒幾個男生敢跟她說話,更別說將蒼耳往她身上扔了。
有一次,課間的時候,我將游戲中玩剩下的一把蒼耳扔到窗外。結果,鬼使神差,蒼耳全部扔到了靠在窗前的學習委員頭上。她看一下我,卻并不說話。這一舉動給我壯了膽,我靠過去,將蒼耳用力揉進她扎好的頭發中間。然后,我看著蒼耳的鉤刺將她的秀發弄亂,并且相互糾纏,迅速跑開。
事情的結果沒有預料中那么嚴重。她并沒有大發雷霆,而且還似笑非笑看著我,臉突然紅了好一陣子,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小心翼翼地去整理秀發。到后來,剩下兩個蒼耳實在糾纏得太厲害,一拔就牽動頭皮,她便跑過來,拉住我的手:漆宇勤,你快來幫我摘掉啊。
必須交代的一個背景是,那個時候,男女學生同桌都要刻畫一條深深的“三八線”,懵懵懂懂又似乎情竇初開的年紀,與異性的任何接觸都會成為別人取笑的話題。哪里有人敢拉異性同學的手啊,更何況,她又是班上甚至是整個小學里最漂亮的女生!頓時,同學們便都開始起哄。哄笑中,我紅著臉幫她將蒼耳給摘了下來,看都不敢看她美麗的小臉。這時,另一個男生卻不合時宜地又扔了一個蒼耳到她頭上。幾乎是一瞬間,蒼耳被她捋了下來,只一轉身,就塞進了那個男生的嘴巴里,一邊還伴隨著清脆的兩個巴掌聲。那個男生被推到旁邊,幾乎是哭著說:怎么漆宇勤扔你蒼耳都不發脾氣,偏偏打我啊?她對著那個被嚇懵的同學挑釁地叫:我就只想讓漆宇勤扔我蒼耳,你們能怎么著?
沒人能怎么著。連哄笑都瞬間停止。
多年過去了,蒼耳已經遠離了讀中學的我們。但是,那一次,漂亮的學習委員說的這句話以及她在其他時間對我的友好,讓我溫暖了好多年。再后來,偶然間聽到同學說起,那個小學時連續當了五年的學習委員高中畢業后嫁給了一位市長的兒子。這則消息聽過也就聽過了,并沒有給我留下太多的印象,如同童年的那些蒼耳,并未給我太多深刻的回憶。只是,蒼耳榮了又枯枯了又容很多次之后,當我在同學聚會時再一次見到那個曾經的學習委員,我看見她依舊那么美麗,而身旁的那個男人,卻怎么也看不出半點出生領導干部家庭的優雅和素養。那一瞬間,我突然莫名地有些傷感。
這種莫名的傷感我自己都說不出緣由,只是突然之間,想起來,藥典中說的:“蒼耳,微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