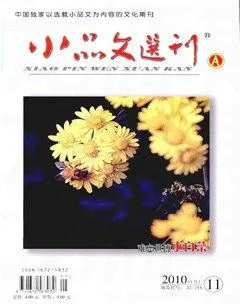心悅君兮君不知
總是記得那樣一個寒冬瘦雪的季節,你舉起酒杯,執手相邀,然后是秀發一甩,錦繡于內,然后我又走了。只有你燦爛明媚如禮花般的笑靨,零落于塵緣浮華之外,然后是深深地感動,長長地懷念。
“你真美呀,請為我停留一下”。這是《浮士德》里,歌德發出的靈魂驚呼,被我偶爾拾揀起,沾著心靈的泉水,我把這句話用一枚精美的書簽封存,在歲月的長長短短里,固執而偷偷地鐘情著你……
落日黃昏,晚霞染紅夕陽,我不能停止的是回憶;月升中天,孤星零掛夜空,我不能停止的還是回憶。在回憶里我可以自由自在地飛,像淚水和風一樣,一路狂奔著撞向雪山。
現在我可以做夢了嗎?
在夢里你是我的愛人。我相信這是繆斯女神的安排,是命運把一個寫詩的你贈給了我,一個平凡的男人,工作一般,生活一般,人也一般。沒有花前月下,海誓山盟,沒有卿卿我我,口唇生香。當愛情和柴米油鹽相遇時,浪漫就頓時灰飛煙滅。愛人,為了你的幸福,我寧愿放棄詩歌的誘惑,做一個養家糊口,收心斂性,有責任心的好男人。因為我知道,面包比詩歌更重要,當愛人忍受著饑寒交迫卻與我分享精神世界的快樂時,那是每個生出胡須的男人最大的恥辱。
在夢里你是我的情人。我們將在陌生的大地上建一座城堡,守著壁爐傾聽玫瑰綻放的聲音。在時光無形的掌中,以夢幻的眼神,你凝視著我,我凝視著你。如同《花樣年華》里梁朝偉與張曼玉的唯美主義,臨界狀態,沒有偷情,沒有火焰,永遠只說一句話:“我們跟他們不一樣”。從相識到相悅,只有濕漉漉的眼神,無奈的凝視。倩影搖曳,秋波流轉,纖指輕觸,引而不發。
在夢里你是我的紅顏知己。我和你只有傾訴與傾聽,讓我做你的歌者吧,居住在你的精神家園。在一個藍色午間,拉上窗簾,隔著一段距離,席地而坐,聽著德彪西的音樂,聽著淺淺的低語,天籟一般,直抵你的靈魂。你靜靜地傾聽,體貼如冬夜里的一杯暖茶,于是想起了浪漫,想起了一首歌:“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變老,一路上收藏點點滴滴的歡笑,留到以后坐著搖椅慢慢聊。”隨便地聊一聊,竟聊到了夜月低回,你我都有些困了,便手與手相握,傳遞著溫暖也傳遞著感動。送別的時候,你會很輕很柔地對我說:“早點睡吧,別想太多。”于是心底深處有了牽掛,淡而綿長,是微微的甜蜜的醉。
不是妻子,不是情人,紅顏知己就是紅顏知己。紅顏知己如靜靜的一株百合,在午夜時分,留下一屋子的純然香氣,一點一點入了男人的心,那個礁石一樣完整的男人,濤聲一樣破碎的男人,冷漠的眼角終于流下了蒼涼的淚水。
在夢里你是我的姐妹,我把你當做我手心里的一塊寶。水一樣靈秀的文字,絲一樣光潔的氣質,會讓我在所有人面前自豪地說:“她呀,她就是我親愛的姐妹,清純如上天無塵的花兒,可知,可明,可斷。”
現在我的夢做完了,你像鳥兒一樣飛走了。我的胸膛空空的,說不出的感傷,也說不出的平靜。
過去了故去了,哪個執手相邀的冬季像一架風塵仆仆的馬車,再也不回來了,你的聲音,你的笑臉只在夢里夢外閃現。而我還固執地等待,等待……還要等待多久,等待多久,我就成了你詩中的男人。在這個變幻莫測的世界,感情脆弱的像玻璃杯,心最容易破碎。
走進你的時候,止不住心旌搖蕩,風情萬千,仿佛聽見我在問:“你是為我預備的水嗎?你是為我預備的花嗎?”
離開你的時候,忍不住的嘆息,忍不住的念叨:“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
昨夜我又夢見了你,為我寫一首詩,字字珠磯,多像愛我的人流下的眼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