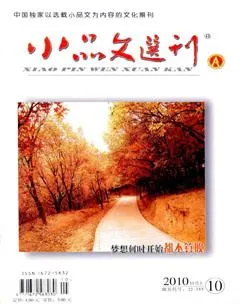春風(fēng)夜
她進了旅館的門,局促的前廳光線很暗,久未清洗的拼花瓷磚地面又黏又澀,腳踩上去有點沾鞋。空氣中彌漫著韭菜包子味兒,想必這就是旅館提供的早飯吧。曲尺形的前臺暫時看不見服務(wù)員,迎門墻壁上并排掛著三只表面模糊的石英鐘,分別顯示著紐約時間、東京時間和北京時間。一些客人從前廳走過,身上都帶著韭菜包子味兒。俞小荷向其中一人打聽102,那人指給她一條窄窄的走廊,敢情就是一樓。她穿過走廊,順利找到102房間敲起門來。聽見里邊有人唔唔噥噥地問“誰呀”?她憋著嗓子撇著京腔說“服務(wù)員”!門開了,打著哈欠的王大學(xué)見門口站著俞小荷,忍不住一拳打在她的肩膀窩上,接著一把將她拖進了屋。
房間里黑咕隆咚,一股又一股煙臭、腳臭和汗酸氣撲向俞小荷。從前她對這些氣味并不陌生,但是今天她覺得這房間的氣味真是嗆人。沒容她多想,王大學(xué)又是一拳將她打倒在床上。黑暗中俞小荷臉朝下地?fù)湓谝粓F熱乎乎的被子上,她聞見了王大學(xué)的味兒,身子一陣發(fā)軟。王大學(xué)從背后撲過來壓住她說,你小子學(xué)會蒙入了,還真當(dāng)你過3個鐘頭才到呢!說著就去摸索俞小荷的大衣扣子。這時忽聽黑暗中有入咯吱咯吱磨牙,驚得俞小荷叫道:誰?王大學(xué)說,別怕,是二孬,跟我搭伴開車的二孬,早睡死過去了。俞小荷猛地翻身坐起來壓低聲音說,你個流氓,屋里有人你還跟我這樣!王大學(xué)解釋說,二孬他表姑家離這兒不遠(yuǎn),這旅館就是他表姑給介紹的。剛才我給你打電話的時候二孬正要去他表姑家,我看他累得邁不開步,就讓他先在這兒睡一覺,反正你一時半會兒也到不了。要不我這就喊醒他叫他走?俞小荷截住他的話說,拉倒吧你,我是那種刻薄人么。說著摸到床頭桌上的臺燈,擰亮。她看清對面床上的確躺著二孬,試著叫了聲“二孬”。二孬不應(yīng)聲,卻又是一陣咯吱咯吱的磨牙聲,聽得俞小荷起了一身雞皮疙瘩。
王大學(xué)盯著俞小荷說,看是吧,睡得死人一樣。說著又去湊俞小荷。俞小荷閃開身子關(guān)了燈說,老夫老妻的你這是干什么呀,這會兒不行!王大學(xué)說老夫老妻了咱才不怕什么呢。俞小荷說你先到了怎么不先洗個澡啊。王大學(xué)哼了一聲說,我就知道你是住在北京城的別墅里眼高了。你們是24小時熱水,我們這春風(fēng)旅館就一個小時熱水,晚上8點到9點。俞小荷立刻覺出剛才的話有點傷了王大學(xué),趕緊軟了口氣說,什么你們、我們的呀,我請了一整天假,今天不走了,晚上住下,明天早上才回去。就這,聽明白了吧?王大學(xué)不出聲地笑了,接著嘴里一陣嘶嘶哈哈,兩只手扶住后腰。俞小荷知道他有腰椎間盤突出的毛病,跑車這一年多來經(jīng)常犯病。她從床上出溜下來,扶著王大學(xué)讓他平躺在床上,腰椎間盤突出最怕久坐。王大學(xué)在床上躺好,掀開被角對俞小荷說,你陪我躺會兒總行吧。俞小荷脫掉大衣搭在床尾,和衣靠住床頭坐好說,你躺你的,我陪你坐著。王大學(xué)拿被子蓋上她的兩條腿,他知道她的腿有關(guān)節(jié)炎。
晨光透過窗簾的縫隙絲絲縷縷擠進房間,兩個人安靜了下來,才覺出這屋子其實挺冷。98塊錢的客房,暖氣也停得早。王大學(xué)在被窩里摟住俞小荷穿著彈力保暖褲的腿,俞小荷低頭摸了一把男人臉上粗硬的胡子說,你還知道疼我這腿啊。王大學(xué)說我不疼你疼誰呀。這一趟十多天,我和二孬緊趕慢趕,兩個人輪換著開,一人開4個鐘頭,12個鐘頭才吃一頓飯——就怕吃飽了犯困。俞小荷說,給我講講這一趟你們都去了哪兒。王大學(xué)說從運城拉了蘋果送廣東;從廣東拉了椰子送呼和浩特;從呼和浩特拉鋼材到順義,明天從順義再拉上木頭到太原。凈開夜車了,好幾宿沒睡過囫圇覺。想早點兒看見你,剛才在順義連車都沒卸。俞小荷說那誰卸呀。王大學(xué)說有人卸,咱不掙那份卸車的錢了。
俞小荷說一會兒我請你喝酒,反正今天你也不開車。王大學(xué)說也給我講講你。俞小荷說你不是說我變了么。王大學(xué)說更肥了,你個肥婆!臉也白了。北京就是養(yǎng)人哪,說話的調(diào)調(diào)都綿軟了,從前你可是粗聲大嗓。俞小荷說,還有呢?王大學(xué)說,還有什么“曉得”啦“喉嚨”啦,“哇塞”啦,還有什么“得了您吶”“找補找補”,聽著不順當(dāng)。俞小荷放在男人臉上的那只手向上一掃,停在男人頭頂,抓住他一撮頭發(fā)使了點勁說,叫你不順當(dāng)!王大學(xué)哎喲著說,你想搞家庭暴力呀你……
俞小荷在王大學(xué)的頭發(fā)上松了手,她感慨粗心的男人竟還注意到她說話用詞的變化。被男人一說,她發(fā)現(xiàn)自己說話真和從前有所不同。趙女士是浙江人,趙女士的公公婆婆是北京人,劉姐是四川人,俞小荷身處這樣的環(huán)境,說話難免受些影響。她現(xiàn)在把嗓子叫喉嚨,把知道叫曉得,把扔掉叫摔掉,又從趙女士的兒女身上學(xué)得一些時尚感嘆句比如“哇塞”什么的。可著急時、大段說話時還得用老家話,那樣表達得清楚,也趕勁。那時她就顧不得向北京的趙家靠攏,她不用“生活”啊“日子”啊這些詞,她喜歡說“過光景”。趙女士對她說,過光景很好聽。俞小荷說話還有屬于她個人的一個習(xí)慣用詞:“就這”,常在一段話中間或末尾加上一句“就這”。好像在向你強調(diào)“這就是我要說的”,又似乎沒什么用意,只起著給說話節(jié)奏打拍子的作用。
現(xiàn)在俞小荷給王大學(xué)描述她的北京生活,還是老家話方便。她告訴他,眼下在農(nóng)村也少見像趙家這么多口人住在一起的。趙女士兩口子,他們雙方的父母,他們的一兒一女,一兒一女的下一代,還有趙女士一個沒結(jié)過婚的老哥哥和一個沒結(jié)過婚的老姐姐。王大學(xué)插嘴道這不是吃大戶嗎。俞小荷說趙女士家是大戶,開著好多家超市,北京、外地,都有。她男人一年有8個月在天上飛,是給外國銀行做事的。你說吃大戶,也算吃大戶吧。可一般大戶多半是不讓你吃,越是大戶,越是算計的狠。就這。趙女士好熱鬧,老人們都給接來,聽她說要養(yǎng)他們一輩子。就是做衛(wèi)生辛苦些,上下三層樓,十好幾間房。我每進一間屋子擦家具洗地板,都忍不住琢磨,往后閨女要是能落在北京,咱什么時候能給閨女混上一間房呢,哪怕就我和劉姐那樣的,10平方米吧……哎,你說我是不是做夢啊!哎!
俞小荷輕輕胡擼著王大學(xué)的頭發(fā)等他答話,但王大學(xué)不再言聲,他困得撐不住,睡著了。他的腦袋枕著俞小荷的大腿,壓得俞小荷又酸又麻。可她不敢動彈,生怕驚醒了他。她僵著身子靠在床上,聞著王大學(xué)頭發(fā)上的煙味兒和油泥味兒,靜聽著房間里兩個男人粗重的呼吸,靜聽著對面二孬偶爾的磨牙,她想能安穩(wěn)睡覺就好,跑車的人最缺的就是睡覺。再多的話要說,不是還有一個晚上么;還有整整一宿。她靠在床上,眼睛早已適應(yīng)了這房間的光線。她看見對面墻上有泛潮留下的形狀不一的洇痕,有的像人,有的像魚。現(xiàn)在她不覺得這墻寒磣。
天過中午,二孬讓尿憋醒,爬起來去撒尿,才打破了這間客房的安靜。他看見靠在對面床上的俞小荷,慌得連聲叫著嫂,嫂,看這事鬧的,我這就走!俞小荷說往哪兒走哇你,刷刷牙洗洗臉一會兒跟我去吃炸醬面啊。王大學(xué)也醒了,睜開眼就說自己“該死”。俞小荷下床把窗簾拉開,推開一扇窗,陽光和清新的空氣撲進來,叫人精神一振。她把兩張床整理好,等待他們輪流去衛(wèi)生間收拾停當(dāng),三個人一塊兒出了春風(fēng)旅館。他們都餓了,找了間面館吃炸醬面,喝老白干,俞小荷還特別點了兩葷兩素四個菜,聲明這頓飯是她埋單。
吃過飯,二孬去了表姑家,俞小荷要帶王大學(xué)去醫(yī)院。王大學(xué)說咱不回旅館啊?俞小荷說咱上同仁醫(yī)院做一次按摩,我看你這腰忒難受。王大學(xué)說花那錢干什么。俞小荷說我愿意花,趙女士家的老人凈上同仁做按摩。王大學(xué)叫起來說,他們家去的地方我更不去了,你就燒包吧!俞小荷沉下臉說你要不去我這就回趙家。王大學(xué)最怕俞小荷沉臉,只好跟她去了同仁醫(yī)院。到底是正規(guī)醫(yī)院,王大學(xué)享受了一個鐘頭的按摩,立刻覺出腰上輕松了許多。當(dāng)他知道一個鐘頭90塊錢,十分心疼。春風(fēng)旅館一宿才98塊。他明白這是俞小荷的心意,她讓他看到,她在北京能掙上錢,還認(rèn)識大醫(yī)院。這時俞小荷的手機響了,是女兒打來的。說她已經(jīng)下課了,問到哪里和爸媽見面。
他們和女兒見了面,一家三口就在同仁醫(yī)院附近一個涮羊肉的小飯館吃了晚飯。吃過飯,女兒說學(xué)校還有事,要先走。俞小荷說你爸好不容易過來一次北京,就不能多呆會兒。女兒說我是給你和爸騰時間呢,我呆的時間越多,你們說的話不就越少啊。說完真就走了。俞小荷笑著罵她像只巧嘴的八哥,但女兒的巧嘴畢竟又一次洋溢了王大學(xué)和俞小荷的情致。他們都覺出了時間的寶貴,他們應(yīng)該盡快回到旅館。
選自《文學(xu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