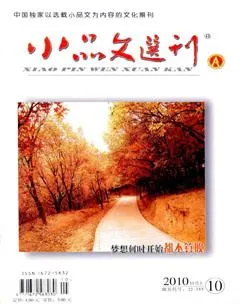孰愛
1949年7月,有一件事讓我忘不掉。事不大,卻挺鬧心。
13歲的我參軍不到三個月,被分到修建解放濟南革命烈士塔的一個半軍半政的單位。其中一部分人是設計師、工程師,全是解放以后留用的。在那個滿是墳頭的四里山上,一個殘留的日本神社就算是我們的“單位”了。屋里屋外英雄其實一個樣,戰爭的原因,這神社被炸得沒有一塊完整的墻,只好用席子一圍。
炎熱的夏天,蚊子、蟲子一起進攻,我沒有被單,沒有蚊帳,軍裝褂子是我的枕頭,我只好把那床褥子卷成筒,夏天我就是這么過來的。
睡不著的不止我一個,大家干脆湊在一起閑磕牙,我經常加入到這個“隊伍”中來,聽那些關于解放區、舊社會的新鮮事。
有一天晚上,熱得實在睡不著,神社的臺上圍著一堆人聽吳工程師講故事。他講得津津有味,我湊上去的時候,吳工正在大講羊奶多么有營養,在四里山上養上一只羊喝奶,就能保證你怎么怎么不缺什么什么營養……弄得大家一會兒想喝奶,一會兒想養羊……講著講著他像發現了什么似的向前看,眼睛發直,大家一起跟著向他看的方向瞄。
還沒看清是什么東西,他抓起屁股底下那條板凳向著前方“沖刺”,我們跟過去一看,原來是只小刺猬。吳工說:“它的聲音像孩子哭,我從小就知道。”
怎么哭?還沒來得及“推理”,“小孩”已經哭上了,哭得非常非常凄慘。
原來他拿凳子腿壓住了刺猬的后腿,坐在上面轉著碾,碾了左腿碾右腿……刺猬凄厲的慘叫聲,在這靜靜的四里山上,幾乎是整座山都在哭叫。
大家都聽不下去了,有人求情:“饒它一條命吧,快放了它吧!”
小刺猬在大家的求助下拖著兩條報廢的腿隱沒在草叢里。
那天大家都沒睡著。我一個小孩子再不懂事,這情這景我能忘了嗎?一輩子都忘不了啦!
第二天下午,我上山換崗,路過草叢,隱隱聽到昨晚“孩子”的哭聲,同時還伴有咕咕的聲音。我朝小路六七米的地方看去,心里咯噔了一下——那只受傷的小刺猬竟然拖著兩條爛腿上了山,有三個“孩子”嗷嗷待哺,圍在“媽媽”身邊,這“媽媽”一見我,驚嚇萬狀……
我哭了,抹著眼淚上了山。
接著,每天上下崗我都遠遠地看著它們。這兩條殘腿的小母親有窩也爬不進了,那三個小家伙能不能吃到奶也是不言而喻的事——它們的媽媽已經不能動了。
三天下來再去看它們母子,“媽媽”已經沒氣了。
我扛著槍,一口氣跑到山上。這對當時的我而言,不能不說是一件大事。
后來,我長大了,成人了,成材了,想法也不一樣了,我認為,天底下最偉大的一個題材,也是藝術創作中最值得頌揚的,就是一個字——愛。
選自《中國婦女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