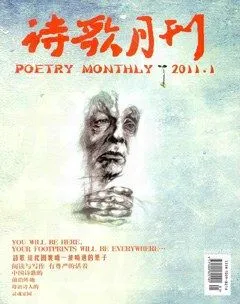劉小雨的詩(11首)
在高處
在云中山,我不止一次
俯視郁郁蔥蔥的松濤
那時候我堅信自己
坐在一艘石頭船上
我不蕩漾,是風
翻卷在森林上面
是太陽,在更高的地方
一如繼往地孤獨
沒有鳥,只有云做的翅膀
無限地潔白
飛在我羨慕的蔚藍中
我不是一塊山石
從小就不是
無法安放在任何一個裂縫
我不是一只狼
即使瀕臨絕跡
也不能替代它
仰天長叫
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將視線里的事物,像河水
花朵,炊煙,村舍,樹木
深愛的人
一起放在高處
在山頂上重新愛一回
秋風
整個秋天
如我的面孔
黃啊,無法褪去的黃
這是秋天的速度
用我的兩條腿表現的快
啊,一秒與一生
展示的瞬間
多么不同
又多么戀戀不舍
此時的秋風
輕輕擦痛了雙眸
只一晃
就露出了秋的針尖
我不讓出皮膚下的血脈
就得騰開小小的體積
可我從現在開始
不贊美,不詛咒
不流淚,不
失去我迷人的風度
很難
卻像風,站在秋天的胸脯
一次,一次
做俯沖的姿勢
僅僅證明
我們必須如此
與博爾赫斯有關的片段
我相信事物最后的莊重
——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
他講述布宜諾斯艾利斯這座城市的一些往事
廣場、酒吧、書店、街道上平靜的樹木
他緩慢的哮喘式的語調適合于分行表達
他說:月亮,瑪利亞,月亮——
月亮就代替了他的眼睛,俯瞰著阿根廷
輪廓分明的阿空加瓜山與巴拉那河
另一個博爾赫斯坐在一家電影院里
觀看《西區故事》,一部不錯的片子
他已看過幾次,黑暗中聽到音樂響起
沒有人意識到一個失明的老人在他們中間
究竟發現了什么。黑暗在減少
稀薄的回憶中,鏡中的面容多么危險
必須認清的事物有些模糊——
相比于安第斯山脈,他的曾祖父
勇武善戰,是——塵土與光榮
混合成的結局,光榮高于塵土
目光高于眼睛。他的晚年已看不見丑惡
過去的完美經常重現,別人將是他的墓碑
比大理石更堅硬和持久。他相信時間
是分開他和我們的籬笆,對于鳥
并不存在。對于鳥鳴更不存在
很多時候,他在一座迷宮中流連
古老的星辰,1955年的某些白天與黑夜
像玫瑰,吸引著他。1986年4月26日
在日內瓦,他再度認識婚姻的短暫
同年6月14日,他同肝癌一起離開
阿根廷,只回去一位詩人的名字
宋
時間對一個朝代的否定
僅僅是時間的問題
而宋也只是一個詞
我認識這個詞的過程
從柳永那個詞開始
一個“奉旨填詞”的才子
絕對與風流有關
我可以想象三千歌妓
走過宋朝的街道
不為他的倜儻
整個宋的戰爭
在我看來是鄰里間的斗毆
只有詞才是它的代言者
就像現在我又一次看見
它穿透了時間
不只是敘述
隔著半條前進西街,無數的金蝴蝶
展示行為藝術。我不只是欣賞
我在說出,一個秋天的本質
它們跳躍著,從高處的風中
一直往低處,仿佛流水的波浪
映出了夕陽的面孔
我十分擔心對面的泡桐樹
在秋天衰老的速度,比我的贊美快
十行詩的距離,我的一顆牙齒
早在一年前就落在我的右手心
但毫不影響我出口能夠成章
比如這個上午,太陽從紅旗商場的頂部
側轉臉龐,接近十一月的秋風
徐徐吹拂花壇,吹我內心的葉子
一片接著一片,我記錄下這些瞬間
不只是敘述:有關消失的起始和結局
不只是敘述:一個女人與一樹葉子的糾葛
我從上行線移至下行線,風,緊跟落葉
同我逆向而行,在我身后輕響了幾聲
蟬和禪
一直纏著我的兩個漢字
乍看像兄弟倆坐在紙上
一個呱噪,一個沉默
就象一屋子的酒徒
猜拳,放肆,吵鬧
突然間全部離去
剩下滿地的煙頭,瓶蓋
而我,就是隔壁那個丫頭
愛……
我很少說起愛
在公開場合,也很少
提及糧食二字
我靠它們活著
它們的分量
嘴巴和舌頭
越來越承擔不起
憂郁
我不承認憂郁。一共有三個我
出現在月亮下
不是你的,我的,他的
是土地上的,土地內的
以及最初不認識土地的混沌物
我承認憂郁。無論怎樣緩慢行走
衰老總是閃電一樣迅速
而且,我如何后退
都無法再次溫習混沌的感覺
月亮
今天我看見的月亮
同上個月區別不大
但它更像一只齒輪
細密的銀牙咬我
咬一顆心的兩瓣
如果它不接近我
把柔弱的心給它,多好
讓它變成我坐在窗前
我從天空一步步下來
咬它,多好
雨水
這來自高處的十五厘米雨水
不單是一種垂直的深度
而是幸福的尺度
我親眼目睹了它們
從我腳踝的上面
慢慢滲入一株植物的根部
單詞
一整天,寫一個單詞
MOTHER,在母親節的末尾
我大聲念,念到你白發變黑
念到你看著剛出世的劉小雨
忘掉了將來的一切
MOTHER,你在屋里安睡
聽不見,你正在塵世之外
夢見我祝福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