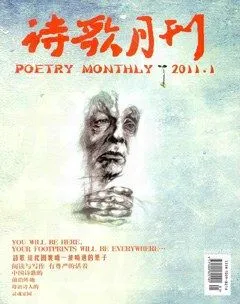雷抒雁:讀《詩》說“淫” (連載一)
聞一多先生說“《詩經(jīng)》是一部淫詩。”
這話說在上世紀(jì)四十年代,頗有些石破天驚。今天我們從2002年12月巴蜀書社第一次出版的聞先生的《詩經(jīng)研究》里還可以讀到這些話。(第25頁)
說“淫詩”,聞先生不是始作俑者。自《詩經(jīng)》問世,大約講授者、研解者,沒有人離開過這個“淫”字。
始見于孔子。即所謂“鄭聲淫,佞人殆”。
“淫”字,可解為“過度”,“沉溺”,但更多則是指“淫亂”。
漢儒因圣人說了詩三百,“思無邪”,便只以“正”字證詩。胡扯些《左傳》之類的淫邪故事,做了《詩經(jīng)》的背景,以為是“刺淫”,而非宣淫。
《左傳》里,多記有諸侯國君們生活靡爛的穢行。衛(wèi)宣公劫奪了兒子伋的妻子齊女姜氏為妾。那么,《靜女》《新臺》便是刺宣公淫其子婦的。《桑中》也是刺衛(wèi)公室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等等。漢儒解《詩》多依《左傳》,聞一多先生就干脆說“《左傳》是一部穢史”。認(rèn)為一部“《左傳》簡直充滿了戰(zhàn)爭和奸殺。”
直到宋儒,朱熹的《詩經(jīng)集傳》問世,否定了《詩序》派的牽強亂說,但卻又導(dǎo)入理學(xué)說教的怪圈。朱熹的眼里,一部《詩經(jīng)》充滿“淫奔”、“淫女”,淫思。詩人歐陽修的《詩本義》也依聲而起。
《靜女》、《新臺》、《君子偕老》、《桑中》、《蝃蝀》、《大車》、《將仲子》、《遵大路》、《女曰雞鳴》、《狡童》、《褰裳》、《東門之墠》、《風(fēng)雨》、《子衿》、《野有蔓草》、《溱洧》、《東方之日》等,一概都是男女“淫奔”之詩;若是失戀,便是“淫女見棄”。
宋儒較之孔子、漢儒將一“淫”字?jǐn)U大化,只要是男女相會,不管是相愛、相悅、相思,還是怨棄,一概冠之以“淫”。
一旦沾了“淫”字,就難免“邪”,難免被鄙棄。
《樂記》說:
“鄭聲好濫淫志,
宋音燕女溺志,
衛(wèi)音趨數(shù)煩志,
齊聲敖辟喬志。
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清儒解《詩經(jīng)》,雖已有解放,不拘于詩《序》、或宋儒說教,但一個“淫”字并未動搖。依然是圍繞“淫”字說詩。
以“淫”說詩,集大成者,乃聞一多先生也。
聞一多先生知識廣博,對于古字詞的訓(xùn)詁,超過前人;兼之又是優(yōu)秀詩人,這更是他勝于學(xué)究老先生們一籌的地方。
聞先生將《詩經(jīng)》里表現(xiàn)性欲的方式分為五種,即“(一)明言性交、(二)隱喻性交(三)暗示性交(四)聯(lián)想性交(五)象征性交”。(《詩經(jīng)研究》P2)
無疑,這種以隱喻、暗示、聯(lián)想、象征諸法解詩,自是得當(dāng),是懂得詩歌三昧的。較之古人只依“比、興”簡單析詩,要復(fù)雜、細(xì)致和深入得多。
無庸置言,《詩經(jīng)》里,尤其十五國風(fēng)中,寫男女情感的占有多數(shù),而且有的是情愛,有的是幽思,有的是怨懣,亦有的是性愛,甚至是較為露骨或粗鄙的性生活。這種表現(xiàn)性愛的詩歌,在古今民謠中比比皆是。所謂桑間濮上,曠野林下,多有男女私會。
但是,能否將情愛、性愛,一概都目之為“淫”呢?值得商榷。
聞一多先生訓(xùn)詁:“邂逅相遇”,“解逅”即“解覯”,性交也;“謔”,亦是性交。因為“虐”有“虎足爪人”之意,是“原始人最自然的性交狀態(tài)”。至于,“風(fēng)便是性欲的沖動”,“虹是性交的象征”,“饑”亦是性的渴求;而捕魚的“笱”,不過是“隱喻女陰”。等等。這就多少有些“泛性”了。
聞先生說,十五國風(fēng)中大多數(shù)詩是淫詩,即便是刺淫的詩,也得有淫,然后才可以刺啊!
聞一多先生也承認(rèn),《詩經(jīng)》時代,有男女春日相會的習(xí)俗,相悅者會相私。而且;他也承認(rèn),那時人們尚未脫原始的殼,不可用現(xiàn)代的目光去看。
可是恰恰在這一點上,幾千年來,我們研讀《詩經(jīng)》,總是擺脫不了現(xiàn)代人的道德觀念,甚至是封建的理念,去看待遠(yuǎn)古人們自由的愛情生活。一個“淫”字,如一根棍子,將那些美麗的愛情一概打殺。
聞先生深受“五四”精神的影響,說《詩經(jīng)》為“淫書”,是“因為《詩經(jīng)》為吃人禮教的圣經(jīng)”。“自從政府采詩而且作教本,就得加上騙”。那么,研究《詩經(jīng)》,“就是要把累積下來的誑話剝掉。”(《詩經(jīng)講義》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P2)
聞先生認(rèn)為談《詩經(jīng)》,“也就是談?wù)瘟恕!睆膹V義上講,國風(fēng)是民間的聲音,可以看出當(dāng)時的民風(fēng)民情以及上層政治對社會的影響,但說《詩經(jīng)》就是說政治,未免又過于籠統(tǒng)。
上個世紀(jì)五十年代,《詩經(jīng)》的研究興盛了一陣子,余冠英先生出版了《詩經(jīng)選譯》,陳子展出版了《國風(fēng)選譯》,影響甚大;他們用了許多新的觀點,特別是階級和階級斗爭的觀點。但是,說到“淫”字,依然未跳出古人的窠臼。
此中《桑中》一詩,陳子展先生認(rèn)為是“當(dāng)時,剛起來的新有產(chǎn)者和地主階級自夸‘一人而亂三貴族之女’,是暴發(fā)戶勝利者的氣焰”。(《國風(fēng)選譯》P96)淫者與被淫者的對象雖發(fā)生了一些理解上的變化,但仍劃在“淫詩”的圈子里。
就說《桑中》吧,只不過是一個男子關(guān)于愛情的幻想。“云誰之思,美孟姜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你猜我在想誰?想念美女孟姜、孟弋、孟庸。就當(dāng)這是三個人,想想又怎樣?后邊說那姑娘怎么在桑樹林等他,怎么在房子接待他,怎么送他過淇河,不過都是想象中事。就民歌而言,這種想象是很美好的。清人方王潤在《詩經(jīng)原始》中說:“三人、三地、三物,各章所詠不同,而所期所要所送之地則一,板中寓活”。(《詩經(jīng)原始》中華書局2006年2月2次印刷P161))很有見地。
但所有人都認(rèn)為這是一首最有名的“淫詩”,是“竊妻”的詩。稍稍分析一下,其中何來竊妻偷情一類的意思。完全都是解詩者強加上去的。
說到鄭風(fēng)《野有蔓草》,男女邂逅相遇,“有美一人,清揚婉兮”。相互愛慕,遂以相歡。這或為古俗。固然,如漢儒將這理解為為“思遇賢人”,實在牽強,但將這種兩相愛幕,相悅相交,便指為“淫”也太“道學(xué)”。陳子展先生也同意這首詩是歌詠“淫奔”的,而且還弄出了一個“合法的淫奔”與“非法的淫奔”,讓人哭笑不得。
人類原始的愛情,總是愛慕與性欲相伴隨。其表達(dá)方式,常常是性的獻(xiàn)身與占有。這種獻(xiàn)身與占有,雖然,在文明社會的人們看來,可能過于直露與粗鄙,讓人赤顏并忌妬;但它卻體現(xiàn)著一種狂放的自由,隨所欲說“是”;對強制說“不”,并予以拒絕與逃避。
愛情的自由,于是成為人類自身的第一權(quán)利。關(guān)于“自由”的意義也由此逐漸被引申并推及至人類對其它社會自由權(quán)利的渴望與追求。
文明社會道德體系的建立,是以約束為主旨。把愛與性區(qū)分開來,是人類生活的一次進(jìn)步。但限制愛的自由,壓抑性欲,則是對人類自由天性的束縛與剪滅。
閱讀《詩經(jīng)》,當(dāng)人們回望那些原始愛情的自由時,竟意識不到那種自由的美好與可貴,甚至懼怕那種自由的復(fù)活,會對現(xiàn)存社會與倫理秩序予以沖擊與破壞。當(dāng)那些道學(xué)家們責(zé)斥愛的自由為“淫亂”的時候,我們便不能不驚嘆封建倫理道德對人性的傷害有多深!愛情牧師們的誤導(dǎo)與說教,讓人們精神大分裂,一方面以難以壓抑的強烈欲望向往愛的自由;另一方面又以無可救藥的虛偽,指鹿為馬,表白著對于愛情自由的不齒。
重讀《詩經(jīng)》,特別是讀國風(fēng)里那些關(guān)于愛情的篇章,可以讓我們的精神重歸單純與清明;認(rèn)識唯愛才是人類自身發(fā)展的中樞與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