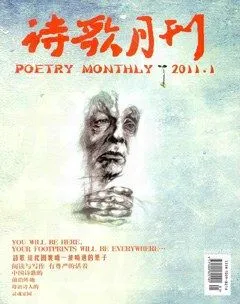給灰娃的信
灰娃詩人:
讀新版《灰娃的詩》,見到去年《國旗為誰而降》,注明寫于阜外心血管病醫院病房,感到十分親切,因為在那半年多以前,我也住進那家醫院病房,為接受“搭橋”手術,不過是在其第二門診部罷了。
我很同意屠岸先生為您的詩集寫的序言,可謂知人論世。他對您的詩在當代詩創作中所獨具的特色,分析得很具體,很中肯,用今天慣用的話說,很到位。
我在上世紀末從朋友處讀到您的《山鬼故家》,即為之驚“艷”,除了昌耀以外,久不見此個性化的詩了。語言和意象的獨創,使我感到惟此人有此詩思,有此詩境,有此詩句。有一種不可復制性,別人是摹仿不來的,硬要摹仿也只能是邯鄲學步。而且,由于您忠于自己的感覺——詩的感覺,您也不會復制自己,這是屠岸先生說到了的。您的那些詩,曾讓我重新思考所謂現實(寫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關系問題,是不是像有些理論家看得那么兩不相干,又像有些理論家設想的那樣可以從外部生硬地“結合”?
這一回我重讀您的詩,包括曾結集為《山鬼故家》那部分,還有新增加的部分。在我的心里忽然浮現“純詩”兩個字。“純詩”,這是有人論述過的,有人追求過的,也有人認為不可能存在的。關于它,有這樣那樣的定義,莫衷一是。我不想從定義出發來探討。我的這個反應,純粹是出于對灰娃的詩的直覺,和對母語中的“純”字的最樸素的理解。
從詩的生成來說,詩人作為主體是第一位重要的,也就是詩人的精神層面,靈魂層面。心地純凈,排除各種藉口的功利之念,才有可能為真正的詩人。王國維說,詩人是“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是天真,也是純真。灰娃對童年家鄉親人的回憶,對少年時期延安生活的懷念,是直覺的,是天真或稱純真的,是理性的思辨所不可替代的。這樣的心地,如海綿一樣吸納了各樣的表象,感受,形成心象,營造出一個不同于客觀世界的詩的世界。這個過程,是從生活“提純”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寫出的詩,稱之為“純詩”,不是恰如其分的嗎?
在這樣的純詩里,并不拒斥社會現實,但是對現實做了“詩化”的處理。在這樣的純詩里,自然不含世俗的渣滓。它是高于生活的更高的真實,只有在這樣的真實中,才會有訴諸道德的和審美的可能。這更高的真實,體現了詩人的心靈的真實,因此是獨特的,不可復制,不可摹仿的。
屠岸先生說灰娃無意為詩人,以及一連串的“無意”,即不是刻意為之。灰娃的詩中有大量的通感和象征,但可以想見,她絕不是學習了“現代詩技巧”一類講詩藝甚至是“做法”的書以后亦步亦趨的,甚至我想,她也未必讀過這些文字。“詩有別材,非關學也”,在這里又可以得到一個證明。對于走上寫詩的道路的人來說,不妨了解些有關詩的理論、源流、爭議,也不妨涉獵一些有關詩藝的探討,但歸根結柢要從心靈出發,要從自己的真正的感受出發,要生活在自己詩的感覺中,這不是人人能做到的。
灰娃的詩,可以看作是她“一個人的心靈史”,折射了一個時代,苦難的歲月,普通人的命運。一方面,是足以導致一個敏感的人精神分裂的矛盾和折磨,一方面是“為人類尊嚴拼死(地)抵抗”(灰娃語),這就是灰娃的詩。
這樣的折磨和矛盾遠遠沒有結束,這樣的抵抗也遠遠沒有結束。這就是灰娃的詩的泉涌不絕的根源,她仍然沒有放下詩筆。愿她健康長壽。
灰娃大姐:寫到這里,我不自覺地把第二人稱寫成了第三人稱,因為我希望這封信能夠在這些尊敬您,喜愛您的詩的讀者和知音面前一讀,以彌補我不能前來的遺憾。
客套的話就不說了。我的有關“純詩”的說法,也許不為文學理論家所同意,那我就換一個說法——灰娃是純粹的詩人,灰娃的詩是純粹的詩:對不對?
邵燕祥 2009年5月14日
(這是在一次關于灰娃的沙龍式研討會前夕寫給詩人的信,后據灰娃告知,在會上當作一份發言念給大家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