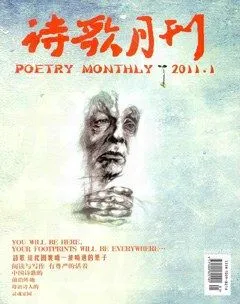春眠醒來尋夢跡
從大阪到京都不超過半小時。穿越內部通道縱橫相錯、熙來攘往人流湍急、似乎不打算讓誰停下來細看的阪急百貨店,進入要是描畫在地圖上就更像是集成電路板的京阪神鐵道網,找準JR東海道本線快車,只來得及觀察幾眼端坐著用手機發短信的少女、拱背埋首瞌睡的中年人、抓著把手吊住身子前傾著翻看漫畫書的小青年,京都就到了。
沿途最多的是房屋樓宇。建筑和建筑把都市和都市連成了一體。不過,走出車站,你立即就意識到這已經是另一座城市了。跟大阪或東京那種見縫插針絲絲入扣的緊張繁忙不一樣,京都街頭洋溢著不屬于當下日本的自在安閑——而這本應該屬于日本的。
記得唯美主義的谷崎潤一郎寫于七十多年前的《陰翳禮贊》,以挽留的筆調稱頌日本古色古香,光線昏暗,潔凈無瑕的那部份往昔,它們在大阪或東京這種當今最代表日本形象的超級都市里很難找到了,在京都卻還保存得相當完好。谷崎潤一郎覺得最有切膚之感,拿來例證可得精神之寧靜休息的日本式廁所,在京都也還容易找到。
京都那些依然籠罩在陰翳之光里的小店,陳列著各色細膩精巧的工藝品、日用品、糕點小吃、偶人玩具,讓你感到傳統還鮮活地在其日常里繼續生長;那些寺廟、庭院、寶塔、神龕,則把你引入美好的舊時代。并且,你更覺得,這地方正是從舊時代延展來到了今天,中間幾無突變和斷裂……聽同行的朋友說起,太平洋戰爭時,美軍特意沒有空襲轟炸京都和奈良這樣的古都。后來我又從一集有關古建筑的電視片里得知,是梁思成建議美軍不要去轟炸敵國這兩座古都的。歷史積淀而來的美,并不與人類為敵。
京都站和金閣
這是我第二次來到京都。幾天前我已經到京都游覽過一次。那天我是從東京乘JR東海道新干線到京都,途中兩個多小時,也像是在一座大城里穿行。春寒比以往走得稍遲,本該櫻花盛開的日子,卻只是偶爾見幾處早櫻點綴著空枝。富士山被霧氣遮擋,在新干線經過它時,只讓人遠遠地看到一點模糊的輪廓。
真正的驚喜是在抵達京都時到來的。JR京都站先就給了一個旅行者果然不虛此行的滿意,它宏闊的現代感成為觀光京都的奢華起點。這座由名建筑師原廣司設計的宛如山谷的超巨大建筑,設置了音樂廳、百貨公司、高級酒店和會議中心。車站的功能性空間只占去整棟建筑物的百分之五。1997年落成后,這座日本最大的車站成了京都的又一標志。它也是車站復合式經營獲利的典范。1991年,原廣司一提出設計方案,有關傳統與現代的激辯就隨之展開。有人說它太破壞京都古雅的意象了,而在我看來,它卻剛好是一個讓傳統煥發新意的提示。高60米的中央廣場式大廳、巨大的音響盒大樓,貫穿東西的約45米的空中通道、疊浪式上涌的傳送電梯,171級高階,上面以特定弧度傾斜的鋼架組成了鏤空的天花板。不妨把這種態勢看成是對京都古意的一種未來式關照——游覽京都正可以從這座車站的頂點開始,從那里下瞰京都全景,會覺得自己正欲從外星深入地球一角一座東方古都的往昔。
京都的另一個標志大概是那座金閣,它座落在京都西北角的鹿苑寺內。因為這座舍利殿“金閣”特別有名,鹿苑寺就又被稱作“金閣寺”。三層金閣有著不同的風格:第一層是平安時代寢殿建筑樣式的法水院,第二層是鐮倉時代武士建筑樣式的潮音洞,第三層則是中國禪宗佛教建筑樣式的究竟頂。第二和第三層在天然漆上再鑲貼純金金箔,泛著亞光,下臨水色比日本抹茶稍淡一些的鏡湖池,果然精美絕倫。那些金箔是1987年修繕時重新貼上去的。1994年的時候,金閣寺列入了世界文化遺產。
我對它久聞其名,是因為三島由紀夫的小說《金閣寺》。小說結束時提到金閣被焚的情景:“從這兒看不見金閣的姿影,只能看到繚繞的煙霧和沖天的火柱。樹叢中火星在飛騰,金閣上空仿佛撒下了滿天的金砂。”小說中的金閣被焚顯然是一種象征。在三島由紀夫筆下,金閣正是日本古典靜態美的典型。有意思的是金閣的頂上聳立著一只鳳凰,于是它的被焚,不是也添加了新生的意味嗎?因而它成了京都給我的又一個有關日本傳統文化之現在的提示。
金閣只可旁觀,不能進入其中。游人們多是以它為背景拍幾張留念照,然后就離去了。金閣實在太耀眼了,很容易讓人忽略鹿苑寺的其余美景。我反而更喜歡簡單地臥著一塊頑石的疏林空地,還有茶廊外那座樸素的夕佳亭。后來在三十三間堂和有名的東寺,我也更喜歡寺院里被冷落不顧的一二去處。
三十三間堂被視為日本國寶,因正殿內由間隔的三十三根立柱而得名。它的正式名稱為蓮華王寺,于1164年建成。在三十三間堂長約一百二十米的殿內,以中央一尊銅鑄的千手觀音坐像為中心,1001尊千姿百態的千手觀音立像沿兩側整齊密集地一字排開,氣勢奪人,是為三十三間堂的鎮寺杰作。東寺更早,始建于796年,是古代日本用來鎮護國家的寺院,正式名稱為教王護國寺。它的奇跡是那座高55米的五重塔,這是日本最大規模的古塔,由空海和尚所建,后來幕府德川家光又重建了它。
花見小路覓櫻
京都寺廟遍地,古跡太多,保存得又那么完好,那么鄭重其事,讓人不免嚴肅認真地一一細察,看得久了,便生倦意。外面大街上的氣氛要松快許多,陽光和煦,色調明媚。京都街景的一大特色是主要干道的人行道上都做了雨廊,分明是鼓勵人們多多步行。在京都逛街也的確是一種樂趣。很少看到那種旗艦甚至航母式的什么都賣的百貨超市,沿街全都是些小店,賣的是專門的貨色,許多意想不到又讓人愛不釋手的手工制品,游客們,尤其姑娘們進去就別想空著手出來。其實那些過于講究細節的小物件并不實用,但卻傳達出一番古意和對于生活之慢(因而也就不是庸懶就是優雅——難道庸懶并非優雅?)的緬懷。有幾條小街完全被雨篷遮蓋起來,成了專營這些貨色的步行市場街,是很多年輕人愛去的地方。
奇怪的是,日本那些衣著前衛打扮標新的年輕人,混跡在這種稍顯晦暗的街角,盤亙在那般總是陰翳的店堂,卻并不讓人覺得有什么不合適。或許一種日本傳統文明的教養依然會從他們的氣質深處隱隱透出?或許京都所代表的那種古意,在現代日本有著順理成章的接續延展?反正,鑲嵌在后現代風格樣式的建筑之間的一方牌位、一個神龕、一處舊廟是如此正當;一個剛剛還在燒香參拜的老頭一轉身走進邊上的電玩店里同樣虔誠地賭一把運氣也那么正常。至于一個老頭用手機相機拍攝一朵櫻花,那就太平常了。不過我第一次到京都的那天離櫻花盛開日還早了差不多一周,所以在街頭綠地見人訪櫻,也就不免駐足。櫻花向來是定期開遍日本的,卻也只在春天的某一周內盛開,然后立刻飄零,人們由是分外珍視櫻花時節,早早就開始期盼。
在京都,花見小路是人們尋覓櫻花消息的一個去處。那是一條最完整地保持了京都古老歷史風貌的南北向街道,非常有名,不過我當時卻并不知情,無意間走進了花見小路也還不知所在。但那種老街的氛圍吸引了我,至于竹籬紅墻的茶屋外面,抬頭偶見枝橫櫻花,則實在令人贊嘆——為什么別處不見,只是這地方獨開一樹呢?跟另一些老街不一樣,花見小路有著濃郁的花街柳巷情趣,鱗次櫛比的高級餐館料亭,店頭懸掛的小紅燈籠上標有“舞妓”字樣,示意店內有舞妓陪客服務。同行的朋友告訴我,運氣好的話能在街上見到舞妓,正說著,果然就見有外出去別的場所獻藝的舞妓挑簾出門,切腳小步急行而過。
花見小路上早開的櫻花驚動了幾個攝影師前來拍攝,其中有人雇了舞妓到櫻樹下擺樣子拍照。幾個歐洲游客見了趕緊揩油,強拉著兩個舞妓合影。舞妓倒是好性情,聽任指揮,哪怕這一服務是免費的。
我卻去注意一家開在路口的首飾店。店面狹小,但布置得漂亮。最有意思的是店內就設了一個作坊,原來所賣的首飾等等都是在這作坊里現場做出來的。這家首飾店的二樓視野很好,從上面能看到垂柳斜櫻下往還的行人,一條帶著弧度的溪流沿街伸向不遠處的鬧市,清淺的水中,竟然立著一頭鶴,正以為是個雕塑小品,它卻振一振翅,邁步隱向小橋陰影里去了……橋上,又一個老頭,端起相機在給他年輕的妻子還是女兒拍櫻花下的留念照?我更愿意那年輕女子是他的情婦,似乎這才更配花見小路。
花見小路也像金閣那樣太鮮明了,實則周遭另幾條老街才是舊京都的一般面貌。在平常風景里那些電線是最討人厭的,可是在那些老街上,團團亂麻似的電線卻一點也不礙眼,反讓這些老街變得更真實,并有了一種朝向現代和現在的美……
白沙村莊連歌
從東京到京都那次,一半是為了去看金閣,卻最中意于花見小路。幾天后我又從大阪來到京都,這次去的則是銀閣寺方向。那地方叫白沙村莊,在京都靠東位置,跟銀閣寺只一墻之隔,或許附屬于銀閣寺。大概半年前,一次將持續半天的連歌會就已經籌定,白沙村莊一座臨池的木結構樓臺,于是在這個白天迎來了一群臨時騷客。白沙村莊雖然不是寺院,卻是和尚們的產業,由僧人管理經營著,其中舉凡小丘疏林、曲水板橋、花草苔蘚、茅舍竹亭,樣樣別致,透著一種別樣的禪意。連歌的主持者高誠修三先生選定此地,自是想給這種傳統雅事一個相得益彰的環境,令其避開日本高速現代化的一面。
高城修三先生卻也不是那種脫節于時代的傳統固守者,這位芥川文學獎得主,有意要在當代日本發起一次新連歌運動,試圖讓這件中世紀的遺物再次用于日本人眼前的精神生活。他認為,連歌是“使人遭遇異質的事物、意外的構思和想象的裝置。連歌是‘場的文學’、‘共同的文學’。” 他希望 “連歌”這種對時人而言過于高雅甚至腐朽的游戲能夠新生。說起來,在手機、因特網發達的今天,似乎何人何時何地都可能成為連歌的“連眾”,所以,好像連歌在這個時代會有些新的可能性。
在白沙村莊的這次連歌,更多的則只能算一次返回,據以想象古代文士墨客那實已不會再現的風雅。上午10點,參與連歌的人們在樓下脫了鞋,從一道窄小結實、將以往歲月的黯淡深吸進木質的樓梯上到二樓,那兒,幾案已排開,杯盞放置得齊整,被水色映襯的連歌之屋的梁上懸著兩塊扁,一曰“老松白云源”,一曰“陽春白雪”。主持者座位背后靠墻的紅色小桌上,放著一個偶人。原來此次連歌,是得到一個制作偶人的世家贊助的。盡管有贊助,參與者每人還得繳納一萬日元。
整個連歌過程被安排成一套漫長的儀式:茶道、一次次端上來的更是給眼睛享用的精細菜點、酒、連歌完成后的書寫、合HCuIsrbYjqmpApIJUUp5yYkJg8o2Eec37SWB52+N8tk=影、移往咖啡館的閑談、見面和告別時沒完沒了的鞠躬……參與連歌的有近二十人,并不都互相認識,坐定后先就各自介紹自己,從中實已見出連歌作為一種社交活動的質地。除了主持者、宗匠和作家的高城修三先生,其余的多為大學教授、研究員、報社高級記者,也有世家子、畫家、詩人和專門的俳人。贊助者被稱為亭主也在座連歌;一位書法家負責記下主持者確認的句子;有個戴眼鏡的人站起來說他是京都大學的名譽教授,京都市長的競選人,即席發表了一通政見,拉起了選票。
連歌為和歌的一種,這次的連歌共計十二句,被稱為半歌仙連歌,每句如俳句由十七音組成。連歌有很多特別的規矩,我在座中靠著翻譯幫助,大約了解到高城修三先生宣布說十二句中涉及“戀、春、秋”的要在二句以上五句以下,并且第七句必須相關“月”而第十一句得要說到“花”。第一句也叫“表發句”,由俳人竹市悠紗念出,顯然是早就準備好的,譯成中文或即:“春眠醒來尋夢跡”。主持者解說評議一番,在座各位便開始苦思,偶爾有人惴惴念出一句,卻常遭主持者搖頭否決。那個京都市長的競選人有一次念出一句,更被高城修三先生痛批為“臭”!然而連歌在進行下去,有句子被采納,便全體釋然。下午忽然電閃雷鳴,一陣疾雨,也被有人一轉念寫下連成了又一句……這樣經歷了五、六個小時, 十二句總算集思廣益共同湊成了。
作出的連歌優劣如何在我看來實在不重要。感人的情形在于,一群人能從四處聚到一起,安安靜靜地坐下來,字斟句酌,為了一首詩,為了語言而沉浸投入。那樣一個漫長的詩的白天在日本這么個金錢社會里太過奢侈了。從中你還是能體會到一種過于優雅甚或頹靡的反叛:就讓那個新干線一樣疾急的世界失控般飛旋好了,我就在一邊慢悠悠鼓搗一首臭詩——人生難道就不該如此隨心所欲?當然,實際上,這又僅只是一場語言和詩的舞會,一個交際場合,一種交往方式。孔夫子說:“詩可以群”,我把《論語》中的這句話轉述給了高城修三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