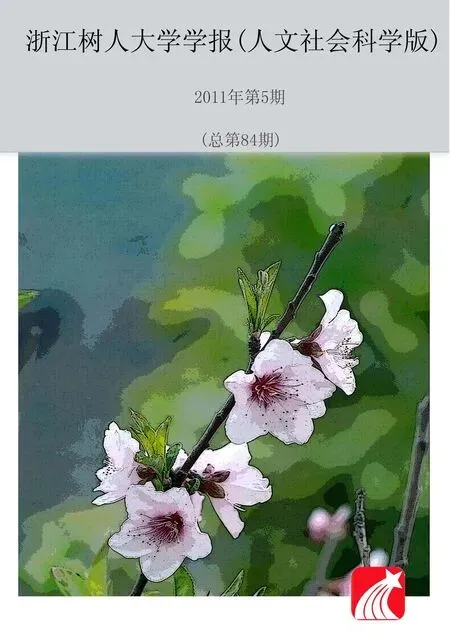《隨園詩話》中的詩歌用典觀
楊凌峰
(西南大學文學院,重慶北碚400715)
袁枚為清代中葉著名詩人,與蔣士銓、趙翼并稱“江左三大家”,其人也蔚為一代文宗。基于其詩歌創作的具體實踐,袁枚亦有詩歌理論的總結,在其《隨園詩話》中多有發明。《隨園詩話》一書匯聚了其數十年的心血,內容駁雜,體大思深,所論也非囿于一端。本文試就其詩歌用典觀念作一些探討。
詩歌用典觀念,顧名思義,即對詩歌創作中用典這一藝術手法的理解和主張。用典是中國古代詩歌創作中最為常見的手法之一,歷來不乏對其的討論。而作為一部具有廣泛影響的詩話著作,《隨園詩話》中對詩歌創作的具體方法屢有涉及,用典這一問題也不例外。
一、用典非以多為貴
袁枚比較了古之文人的鋪采摛文和今之文人的翻摘故紙。他認為:
古無類書,無志書,又無字匯,故《三都》《兩京》賦,言木則若干,言鳥則若干,必待搜輯群書,廣采風土,然后成文。果能才藻富艷,便傾動一時。洛陽所以紙貴者,直是家置一本,當類書、郡志讀耳;故成之亦須十年、五年。[1]7
袁權認為漢大賦的廣征博引、鋪采摛文,實際上具有類書、郡志的工具書作用,而不僅僅具有文學作品的審美性質了。這種狀況的出現,與當時這一些工具書尚未出現有關。然而,在“今類書、字匯,無所不備”[1]7之時,“使左思生于今日,必不作此種賦。即作之,不過翻摘故紙,一二日可成。可抄誦之者,亦無有也。”[1]7這種情況下,一味貪求廣引典故,既無文學作品的新意,甚至連類書的實用價值也沒有了。可見,袁枚對于一味講求用典的觀念是持反對態度的。因此,他以“博士賣驢,書券三紙,不見‘驢’字”[1]185譏之。
而就實際操作層面而言,用典既多,駕馭的難度也隨之增加了:
用事如用兵,愈多愈難。以漢高之雄略,而韓信只許其能用十萬。可見部勒驅使,談何容易。有梁溪少年作懷古詩,動輒二百韻。予笑曰:“子獨不見唐人《詠蜀葵》詩乎?”其人請誦之。曰:“能共牡丹爭幾許,被人嫌處只緣多。”[1]161
袁枚認為,大量用典使得駕馭驅使的難度增加,而這種駕馭能力各不相同,若一味求多,只能是弄巧成拙。因此他引用這一句唐詩一語雙關地規勸文中的“梁溪少年”。用典既多,而能力捉襟見肘,便容易在結構安排上出現問題。這樣一來,典故越多,越顯得胡亂堆砌、雜然拼湊,令人不知所云。同樣以用兵作喻,此時雖有百萬大軍,卻并無有力的統帥,徒然一群烏合之眾而已。書中舉了一例:
近見某太史《洛陽懷古》四首,將洛下故事,搜括無遺,竟有一首中,使事至七八者。編湊拖沓,茫然不知作者意在何處。[1]187-188
這位太史一味貪多,本欲炫其淵博,結果卻適得其反,可謂“博士賣驢”的真實版本。
袁枚又談及他在實際創作中的獨特做法:
余每作詠古、詠物詩,必將此題之書籍,無所不搜;及詩之成也,仍不用一典。嘗言:人有典而不用,猶之有權勢而不逞也。[1]20
“有典而不用”,在那些貪多炫博者看來,似乎有點不可思議。然而,這里面卻蘊含著袁枚的詩學理論。首先,對相關書籍“無所不搜”,卻“仍不用一典”,這樣方能去陳言,道人所未曾道。這與徒拾他人牙慧猶沾沾自喜相比,不啻霄壤。其次,不用太多繁復的典故,消解了讀者的接受難度,正是王靜安先生所云“不隔”的境界。而袁氏自云“人有典而不用,猶之有權勢而不逞”,既說明了這種面對接受者的親近感,也表現了作為一位詩人的充分自信。
二、避用生典
如前所言,大量使用典故,已經增加了讀者接受和理解詩歌的難度。如果使用生僻難解的典故,更使詩歌晦澀難懂。袁枚使用了一個生動的比喻來說明這個道理:
用僻典如請生客入座,必須問名探姓,令人生厭。宋喬子曠好用僻書,人稱“孤穴詩人”,當以為戒。[1]235
詩歌一經創作,必然要面對讀者,為讀者所接受。這個被接受的過程,正如袁枚所云“請客入座”。若客人皆是熟識,易于交往,自然賓主俱歡。而“好用僻書”,得出的作品必然艱深晦澀,形如陌生人相見,必然難以親近。那些好用僻典的作者,實際上是人為地設置了接受和理解作品的障礙,可謂胸無智珠。而在袁枚的詩歌創作中,正好與之相反:
余《過馬嵬吊楊妃》詩曰:“金鳥錦袍何處去?只留羅襪與人看。”用《新唐書·李石傳》中語,非僻書也,而讀者人人問出處。余厭而刪之,故此詩不存集中。[1]186
用僻典和大量使用典故一樣,是詩人以學問為詩,務求炫博的心理使然。這兩種做法有一個同樣的結果,即增加了理解的難度,使作品與接受者的距離被人為地拉大。正所謂“英雄欺人”是也。因此,袁枚力求避免這樣的錯誤,不僅反對使用“絕對生僻”的典故,甚至對那些因讀者未曾涉及而不能理解的“相對生僻”的故實也果斷摒棄。
三、典故的安排和錘煉
用典是中國古代詩歌中常用的藝術手法,運用得當,能為詩作增色不少。袁枚雖然反對大量運用典故,卻又并非絕對反對用典。書中云,有人這樣稱許袁枚的詩:
“專寫性情,不得已而適逢典故;不分門戶,乃無心而自合唐音。”雖有不及,不敢不勉。[1]235
字里行間我們可以感覺到,袁枚對能得到這一評價,還是比較得意的。而這里的“不得已而適逢典故”,正說明了他的詩歌中也并非讓典故絕跡。“主張詩中絕對不用典故是荒唐的,但是典故用得好,卻并不容易。”[2]而這正來自于對典故的安排和錘煉:
唐人近體詩,不用生典:稱公卿,不過皋、夔、蕭、曹,稱隱士、不過梅福、君平,敘風景、不過“夕陽”、“芳草”,用字面、不過“月露風云”,一經調度,便日月嶄新。猶之易牙治味,不過雞豬魚肉;華陀用藥,不過青粘漆葉:其勝人處,不求之海外異國也。[1]186
典故的好壞在于調度、錘煉,而非生僻與否、密集與否。一經妙手,必能點石成金,化腐朽為神奇。反之,難成佳構了,充其量只是典故的填砌。
酒肴百貨,都存行肆中。一旦請客,不謀之行肆,而謀之于廚人,何也?以味非廚人不能為也。今人作詩,好填書籍,而不假爐錘,別取真味;是以行肆之物,享大賓矣。[1]205
俗語云,“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然而有了“米”,也需“巧婦”之手的精心炊治。袁氏所云,正是此理。那么,用典時的錘煉,需臻于何境呢?袁枚云:
用典如水中著鹽,但知鹽味,不見鹽質。[1]235
以“水中著鹽”作喻,意為融會貫通,能讓讀者感受到用典帶來的詩意之妙,又能不著痕跡,沒有填砌、生澀之感。書中又列舉了詩作:
嚴海珊《詠桃花》云:“怪他去后花如許,記得來時路也無。”暗中用典,真乃絕世聰明。[1]73
詩中暗用陶淵明《桃花源記》中武陵漁人的典故,卻自然不著痕跡。所謂“暗中用典”,正是“水中著鹽”的高超境界。
四、用典要靈活,不可太泥
《三余編》言:“詩家使事,不可太泥。”白傅《長恨歌》:“峨嵋山下少人行。”明皇幸蜀,不過峨嵋。謝宣城詩:“澄江凈如練”,宣城去江百余里,縣治左右無江。相如《上林賦》:“八川分流。”長安無八川。嚴冬友曰:“西漢時,長安原有八川,謂涇、渭、灞、氵產、灃、滈、潦、潏也;至宋時則無矣。”[1]10
文學創作講求藝術的真實,允許一定的藝術加工。在運用典故的過程中,必然會根據藝術創作的需要對故實進行一定的熔裁和安排,這是文學與歷史的區別之一。若非要以考據家的眼光去推敲其真實性,就難免有膠柱鼓瑟之嫌了。
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袁枚對于用典的觀念是比較通達的。他看到了藝術創作的特殊性,反對那種以嚴格學問的挑剔眼光指摘藝術創作的做法,強調了對于典故進行藝術處理的合理性。
以上是對《隨園詩話》中的詩歌用典觀念的管窺。總之,袁枚并不反對詩歌中的用典,但是他不贊成大量典故的堆砌和晦澀生僻典故的使用。在典故的運用上,要認識到藝術創作的特殊性,注意調度、錘煉和靈活運用,而非簡單的獺祭魚式的堆疊。在這些觀念之中,正好滲透著袁枚一貫的詩學主張。
在清代文學史上,袁枚獨標“性靈說”,對清代詩壇產生了深遠影響,“使清詩從根本上擺脫了唐宋衣缽的束縛,真正走上了詩歌獨抒性靈之路”[3]。“性靈說”作為一個文學創作理論,是較為完備、系統的,“道出了詩歌創作的本質和規律”,其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為三個字——“真”、“新”、“趣”。[4]所謂“真”指詩歌須是真實情感的自然流露,“新”指追求藝術形象、角度、見解和表達方式的新鮮活潑,“趣”則是關注生活中活生生的情趣。這三點,可謂“性靈說”的核心所在。通過對《隨園詩話》中用典觀念的探究,我們可以看到,二者其實是暗合的。
大量使用典故和好用僻典,必然造成讀者的接受障礙,妨礙了真實情感的表達,如同猜謎一樣的解讀,必然使“真”字大打折扣。而為了用典而用典,不面向生活,不關注生動活潑的現實世界,卻只是一味翻揀故紙堆,必然離“趣”和“新”越來越遠。新鮮活潑、妙趣橫生的表達,除了對生活的關注,更少不了作者的才思。所以用典也須加以錘煉,靈活運用。正所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粹然無疵瑕,豈復須人為。”[5]
袁枚的詩歌用典觀念也是針對當時詩壇的一些風氣而發的。翁方綱的以考據為詩,袁枚深不以為然:“經學淵深,而詩多澀悶,所謂學人之詩,讀之令人不歡”[1]118。因此他反對用典時的考據眼光。浙派詩人作詩好用典,好句句加注,他便針鋒相對地反對大量用典、用僻書,以及典故的生硬填砌。正如書中卷七所云:“空諸一切,而后能以神氣孤行;一涉箋注,趣便索然。”[1]223
[1]袁枚.隨園詩話.[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2]吳蘊章.袁子才詩論——讀《隨園詩話》札記[J].徐州師范學院學報,1980(3):61.
[2]王英志.袁枚與《袁枚全集》[J].蘇州大學學報,1993(3):57.
[4]王成.袁枚“性靈說”論略[J].淮北煤師學院學報,1999(1):85.
[5]錢仲聯.劍南詩稿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44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