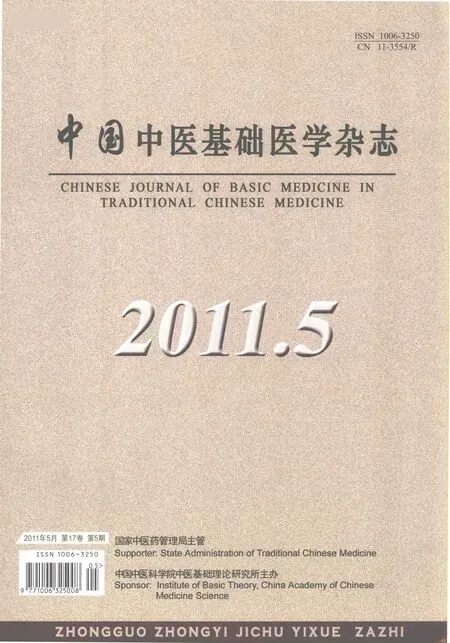初論中醫神氣生命觀
吳昌國
(南京中醫藥大學,江蘇 南 京 210046)
1 神、神明辨
1.1 神
神,是中醫學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但是目前人們對“神”概念的本質似乎還缺少深刻的認識。如《中醫基礎理論》教材對神大多這樣定義:神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的神是指整個人體生命活動的外在表現,狹義的神指心所主之神志[1]。這里至少有兩個問題:其一,“神”怎么會是“外在表現”?其內在過程又是什么呢?其二,廣義之神與狹義之神之間有何關系?
顯然,上述“神”的定義是來自日常語言的習慣,并未經過理性的界定,既不規范也不準確。正是由于對“神”之概念認識的不準確,導致對古籍原典中“精神”、“神明”等概念的混亂解說。要真正弄清這些問題,我們還必須回到經典中去探索。
《內經》正文出現“神”字約236個,其中除了少數用于表示人名(如神農)、穴名(如神門)、圣賢智慧(如生而神靈)、鬼神邪氣(如道無鬼神)等之外,其余“神”的含義無非“神志”、“神氣”兩種而已。在這兩種概念之間,“神氣”是更主要的一方面,而“神志”不過是“神氣”的特定表現而已。
縱觀《內經》全書可以發現,幾乎所有的“神”字(人名、穴名之類除外)都與“氣”有關,其背后都隱藏著“氣”。如果把這些“神”字替換為“氣”,不但語句照常通順,含義也無大的變化。如《素問·舉痛論》所說“驚則心無所倚,神無所歸”,這已經是明指為神志了,但此處的“神無所歸”與“氣無所歸”存在著自然的過渡,因而其結果乃是“氣亂”。
從《內經》大量涉及“神”字的經文看,神、氣、神氣這三個詞是互通的,文字的變化不過是因為語句的特殊需要而已。如為了對仗可以增減字數,為了韻律必須更換文字,甚至語境也可以決定用字的選擇。如《素問·四氣調神大論》云:“收斂神氣,使秋氣平,無外其志,使肺氣清”,是“神氣”互稱。《素問·玉版論要》所說“神轉不回,回則不轉”,此“神”即是氣無疑。《靈樞·九針十二原》所云:“粗守形,上守神;神乎神,客在門”,其中“神”字的選用完全是韻律的需要,其本義總離不開氣。
說到這里我們已經可以下這樣一個結論:《內經》所說神中有氣,氣中有神,或者說神即氣,氣即神。我把這兩者合起來,確定為一個明確的“神氣”概念。
“神氣”的概念確認,此氣是生命之氣,只有生命之氣才可以妙稱為“神”;此神是生命之神,其本源仍然是氣,因此神氣概念的重心落在氣上,神的作用乃是使氣展現為生命。《素問·移精變氣論》所說“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實際是指出元氣的存亡對于生命的重要性,而后世歷代醫家重視元氣,實本于此。
1.2 神明
古典文獻中的“神明”一詞,實際是“神”和“明”的合成,因此必須分別講清這二字的含義及兩者的關系,才能真正弄懂它的本義。但是在語言的歷史演變中,“神明”的含義逐漸地偏重于“神”的一面,并且被狹義化為客體的主宰神。“神明”的這種后生的演變又被現代人不恰當地應用到對經典概念的理解上,一個“心主神明”令中醫學術界爭論了近20年仍無結果,這里面概念上的誤會很多,姑且不論。我想說的是“神明”到底是何義?弄清這個問題爭論就沒有必要了。此前已有作者[2、3]注意到“神明”不等于“神”。張先鋒[3]雖然已經認識到“神藏于內,明顯于外,合稱神明”,但尚未發掘出“神”的真正含義及其與“明”的關系。
神,是深藏于事物內部、發自本源的一種存在,而非外觀形象。外觀形象只是神“化”出給人看的標象,而神的本象人是看不到的。《說文》對“神”的解釋是“天神引出萬物者也”,那是就宇宙整體而言的。同理,生命之神即引出生命形體者也。自然地,形與神的對立關系出現了,而實際上這和形與氣的對立關系沒有多大區別。形是什么?形即是“明”,“明”的本義是光明。《易·系辭》曰:“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在光明之下萬物現形,于是神與明成對,形與氣成對。其差別只在于形氣是客觀表述,神明是主觀認知,主觀認知的對象依然是客觀的形氣。《素問·天元紀大論》說:“陰陽不測謂之神”,“不測”二字明白無誤地反映出“神”的主觀色彩。換句話說,“神”不過是“氣”在人的主觀認識上的反映形式而已,但它絕不是人的意識本身。
那么,作為意識的“心神”是什么呢?它不是生命演化過程之“神明”,也不是生命本源之“神氣”,恰恰是由“神氣”所演化展現出來的“形”或“明”。
2 神氣與生命
神氣是中醫生命觀的核心,因此關于生命的起源、生命的本質、生命的運動等都必須依賴于神氣來體現。
2.1 神氣與生命起源
生命起源于宇宙,是宇宙大生命之神氣演化的結果。《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其在天為玄,在人為道,在地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體為筋,在臟為肝。”這就明確指出,宇宙生命通過氣化之“神”的作用,逐步演化出了人的臟腑形體。在《素問·天元紀大論》、《素問·五運行大論》中又多次重復了同樣的敘述。這里的神便只有在氣中才能找到它的本體,離開了氣,我們不知道神如何在天為風、如何化出五行、五臟。
由于氣化而分陰陽,于是陰陽交感運動是生命之神氣作用的主要過程。《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為什么說陰陽是“神明之府”?實際這里是點明了陰陽運動是化生生命的根本機制。一部《內經》本為闡述生命本質而作,雖善言天地陰陽,最終亦必歸結于生命而后止。因此這里的“神明”,既不是單純表述宇宙萬物運動的玄妙,也不是片面敘述人類精神產生的根據,而是精確地表達了“神氣生命觀”的基本原理。
由于生命起源于宇宙之神氣,古人便從這個本源上去觀察、衡量生命。在養生防病和治療疾病方面,追求對宇宙本源神氣的回歸,形成了中醫學特有的天人合一的整體觀。《內經》把能夠從宇宙本源神氣來進行養生或治病的圣人稱為“通神明”者。如《素問·生氣通天論》云:“故圣人傳精神,服天氣,而通神明。”《素問·氣交變大論》曰:“善言應者同天地之化,善言化言變者通神明之理。”
2.2 神氣與生命本質
區別生命與非生命的本質因素是什么?有作者[4]將“神”定義為生命之神,認為中醫學對生命的定義就是神,有機生命體與非生命物質最本質的區別就在于有沒有神。這種觀點已經接近《內經》的原意了。但是如果不把神落實到氣,仍嫌空泛。《內經》所謂“得神者昌,失神者亡”,表明的是神氣之得失決定著生命之存亡這個惟一的準則。除氣之外,還有精、血、津液等生命要素,它們也都必須具有“神”性,才是可貴的生命特質。也就是說,精、血、津液有神性則能化氣,所化之神氣便是生命之擔當者。
由精所化之神氣可稱為精氣,也可稱為精神。標之以“精”,是指明了此神氣的來源。有不少讀《內經》的人常把經文中的“精神”理解成心理之精神(心神),這是不對的。在神氣生命觀體系中,神即是氣,精神亦即精氣。《素問·上古天真論》寫道:“精神內守,病安從來”,“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數”。此兩句之“精神”作心神解表面上亦通,但這不是經文原意。如果把這里的“精神”理解成“精氣”不是更具有深度、更符合中醫學原理嗎?因為精氣才是生命之本,而心神不是。再看《素問·生氣通天論》一段就更明白了:“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經文似乎是為了防止我們誤解,特意把前半句的“精神”變為后半句的“精氣”。
由血所化之氣,亦可以“神”名之,這在《內經》中不乏論述。《素問·八正神明論》說:“故養神者,必知形之肥瘦,榮衛血氣之盛衰。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這里的養神不是俗語“養精神”,而是養血氣,因為血氣是生命之本。如果這一段經文含義尚有兩可之疑,那么《靈樞·小針解》一段原文,我們便無法把“神”強解為心神了。經文說:“上守神者,守人之血氣有余不足,可補瀉也。神客者,正邪共會也。神者,正氣也。客者,邪氣也。在門者,邪循正氣之所出入也。”此外尚有《靈樞·九針十二原》:“所言節者,神氣之所游行出入也,非皮肉筋骨也。”《靈樞·營衛生會》:“營衛者,精氣也;血者,神氣也。”《靈樞·平人絕谷》:“五臟安定,血脈和利,精神乃居。故神者,水谷之精氣也。”
2.3 神氣與生命運動
從根本上說,生命的運動即是氣的運動。氣的運動變化產生了萬物,亦產生了生命。氣的運動變化稱為“氣化”,氣化不但產生了生命,也是維持生命存在的條件。人們雖然知道氣是運動變化的,但對這種運動變化的具體過程卻不可能完全了解。人們對于無法完全把握的氣的運動變化,賦予了“神”的色彩。《素問·天元紀大論》指出:“故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陰陽不測謂之神。”對于“神”,人們一方面贊美它,因為它化育出萬物和生命;另一方面也敬畏它,因為人們無法走近或看清它。
氣化運動產生出了萬物和生命,因此成為決定萬物和生命的樞機,這便是氣機。“氣機”的概念表達了氣的運動對于生命萬物的主宰和決定作用,確立了氣對于生命萬物的根本性地位。教科書所說“氣的運動稱為氣機”是不準確的。由于生命之氣亦稱神氣,故而氣機亦稱神機。《素問·六微旨大論》說:“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此處“神機”與“氣立”對舉,神機即是氣機明矣。由此而引申出“病機”的概念,病機其實也是氣機之一種,是疾病情形下的氣機而已。《素問·至真要大論》一再強調“謹候氣宜,無失病機”;“審察病機,無失氣宜”,或正說或反說都明確告訴人們,病機即在“氣宜”之中。
盡管我們對神氣運動變化的具體過程不能直接觀察,但是神氣運動的總規律還是可以掌握的。只因如此我們才能“審察病機”。神氣運動的總規律是什么?無非升降出入。《素問·六微旨大論》云:“升降出入,無器不有。”而升與降、出與入,分別構成相反相成的循環往復運動。這種類似圓周的運動,可以看作是神機內在運動的圖式。《素問·玉機真臟論》說:“神轉不回,回則不轉,乃失其機。”神如何而轉,不過是氣的循環圓周運動的另一種表達而已。但是此處把“轉”與“機”聯系在一起,其寓意是深遠的。
3 心藏神論
對心藏神的理解歧義頗多。最大的歧義在于把心藏神等同于心主神明,即將神明單純解釋為神,這是不恰當的,上文已述。但《內經》并無“心主神明”一說,這一概念到清代才開始出現。《素問·靈蘭秘典論》說:“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這里的“出”字是不應忽略的。朱向東[5、6]等人已經大膽地否定了“心主神明”之說,并明確指出神非心所固有,神只是外舍于心而已。這里的“舍”其實就是“藏”,這就與“心藏神”一致起來了。周東浩[6]則根據《素問·靈蘭秘典論》“故主明則下安,主不明則十二官危”的論述,更明確地認識到“十二官外別有所主,主即是神,神才是一切生命活動的主宰”。但這里的“神”必須與氣合論才有意義。朱向東[5]認為,心神包括元神和識神。元神實際上就是生命活動的根本氣機,稱“神機”、“玄機”,它是先天的。識神即人的精神意識,它是元神在后天產生的花朵,對元神有反饋作用。此處“元神”正是本文所闡述的生命之神氣,而“識神”只是其作用方式,是神明從心而“出”的樣式。
[1]印會河.中醫基礎理論[M].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4.30.
[2]曲麗芳.關于中醫藏象術語英譯的幾點商榷[J].中國針灸.2008,28(1):68.
[3]張先鋒.論心不主神只藏神——與《中醫基礎理論》“心主神明”之說商榷[J].湖北中醫學院學報,2006,8(4):39.
[4]區永欣,張小虎.從神明的心腦之爭思考中醫理論的現狀和前途[J].廣州中醫藥大學學報,2004,21(5):332.
[5]朱向東,田文景,李蘭珍.“心主神明”與“腦主神明”的再認識[J].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志,2003,9(6):415.
[6]周東浩,周明愛.“心主神明”之我見[J].中國醫藥學報,2001,16(4):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