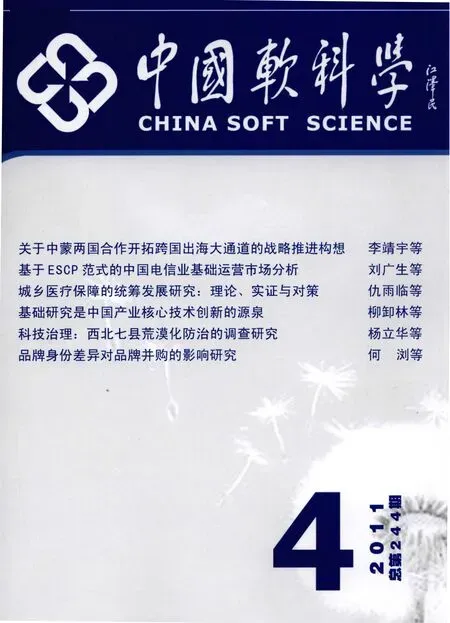環境公益訴訟的制度生成研究
——以近年幾起環境公益訴訟案為例展開
李義松,蘇勝利
(河海大學 法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8)
環境公益訴訟的制度生成研究
——以近年幾起環境公益訴訟案為例展開
李義松,蘇勝利
(河海大學 法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8)
環境公益訴訟是補救環境管理中政府失靈的良方,但當前中國的環境公益訴訟研究存在嚴重缺陷。環境公益訴訟的研究,應該借鑒“生成性思維”以及“法的生成”理論,環境公益訴訟的制度生成研究由此產生。制度生成視角下推進環境公益訴訟應該堅持保守的態度,選擇漸進的思路。在司法中,應著重在發揮私益訴訟的公益保護功能,并結合能動司法理念和嘗試性司法實踐有序推進環境公益訴訟;在立法中,應選擇適當的環境公益訴訟立法模式,并以類型化方法確定環境公益訴訟的原告資格。
環境公益訴訟;生成性思維;制度生成;司法推進;立法推進
環境法律的制定與運行,是解決環境問題最為重要的方式。從 1989年《環境保護法 (試行)》出臺至今的三十多年間,我國環保事業在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時,環境保護形勢依然十分嚴峻,即“雖然局部環境質量有所改善,但環境污染的趨勢總體上尚未得到根本扭轉”①這是我國官方近幾年來對當前環境形勢的總體評價,參見周生賢:《打好決勝戰,謀劃新發展,積極探索中國環境保護新道路——周生賢在 2010年全國環境保護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這意味著,我國現行的環境法律未能有效遏制環境惡化。在對環境法律制度的反思性研究中,學者們逐漸將視點聚焦在環境管理中的“政府失靈”②按照王曦教授對“政府失靈”的分析,“政府失靈”,一種是“積極”的政府行為即為了追求經濟發展而作出的規劃和審批;另一種是政府的消極或不作為,即在建設和管理污染處理設施上和執法上的懈怠,都導致一個相同的后果,就是資源環境狀況的惡化。參見王曦:《論新時期完善我國環境法制的戰略突破口》,載《上海交通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 2期,第 5-11頁。上,而環境訴訟被認為是補救“政府失靈”的良方,他們試圖通過更大程度發揮環境訴訟在環保中的作用來遏制環境惡化。
一般來講,訴訟是當事人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而請求法院提供司法救濟的制度,目的在于私益之維護,這類訴訟被稱為“私益訴訟”。然而在環境訴訟中,與私益訴訟不同,以維護環境公益為目的而提起的訴訟具有重要的地位。理論上,我們將這種以救濟“對環境的損害”或者說“生態損害”的訴訟稱之為“環境公益訴訟”,又稱“環境公民訴訟”③在美國,環境公益訴訟表現為“公民訴訟”或“環境公民訴訟”。臺灣地區的環境公益訴訟移植自美國,也稱為“環境公民訴訟“。本文中,不刻意區分兩種表述方式。。環境公益訴訟不僅可以發揮法院在環境公益補救中的積極作用,還可以鼓勵社會公眾對政府環境行政的監督,促進公眾參與環境保護。同時,它也被認為是環境執法的重要組成部分[1]。遺憾的是,我國尚沒有針對環境公益訴訟的立法,造成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法律依據缺失。但與此同時,我國近些年的環境司法實踐中,已經出現若干環境公益訴訟的案例,具有代表性的如 2003年樂陵市人民檢察院訴樂陵市金鑫化工廠案、2005年北大師生訴中石油公司松花江污染案、2007年貴陽市“兩湖一庫”管理局訴天峰化工公司紅楓湖污染案、2008年海珠區檢察院訴洗水廠水污染案、2009年中華環保聯合會訴江陰港集裝箱有限公司污染案、2010年番禺區檢察院訴博朗五金廠水域污染糾紛案等等。環境公益訴訟的司法實踐在法律依據缺失的情況下紛紛展開,這一現象具有深刻的理論啟示與研究價值。在環境公益訴訟的研究中,可透過這些看似違背法治理念的現象,窺探我國環境公益訴訟建設的可行路徑。本文擬從“生成性思維”角度,結合這些極具代表性的典型案例,探討環境公益訴訟這一制度的生成路徑。
一、制度生成:環境公益訴訟研究的新視角
(一)當下的環境公益訴訟研究
從世界范圍來看,環境公益訴訟尚處于逐漸形成階段。盡管許多國家和地區出現了環境公益訴訟的立法或者判例,但立法并不成熟,司法實踐也不穩定,不同利益群體的具體主張并不一致。在美國,法院通過在判例中限制原告資格等方式使環境公益訴訟的命運經歷了巨大波動④其中影響較大的案例包括塞拉俱樂部訴莫頓案、魯堅案、地球之友訴萊德勞環境服務公司案,參見[美 ]艾米利·A·貝格:《新千年之際:結束了過去十年 <清潔水法 >對公民環境訴訟資格的過分限制》,載呂忠梅、[美 ]王立德主編:《環境公益訴訟—中美之比較》,法律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82-210頁。。盡管如此,美國的環境公民訴訟依然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并對其他國家的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建立產生重要影響。印度和我國臺灣地區的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受美國影響較大。在印度,為了應對環境立法的滯后、不協調以及環境行政執法的疲軟[2],最高法院發揮司法能動性,通過憲法解釋的方式形成司法判例,創立了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在我國臺灣地區,1999年頒布的“空氣污染防制法”規定了臺灣地區第一個公民訴訟條款,此后許多環境法律紛紛增設公民訴訟條款。不過,臺灣的環境公益訴訟尚處于經驗積累階段,存在許多問題[3]。
盡管我國司法實踐中也出現了環境公益訴訟案例和地方規范性文件,但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尚未在法律中正式確立。學界關于環境公益訴訟的討論,整體上看,已經從環境公益訴訟的必要性與可行性論證,過渡到環境公益訴訟原告資格選擇的討論中,關于美國、歐洲、印度、巴西、南非以及我國臺灣地區環境公民訴訟或環境公益訴訟域外經驗的研究逐漸變得熱門。也有學者試圖將環境公益訴訟的研究引向深入,辨析其概念、性質、功能等。
在筆者看來,我國當下關于環境公益訴訟的研究有兩個特征:第一,相關研究主要在追問環境公益訴訟“是什么”,屬本體論的研究;第二,相關研究結論大致相同,重復率較高,理論爭點并不多①事實上,也存在一些爭議點,比如關于檢察機關與環保機關誰更適合作為環境公益訴訟原告的問題,以及不同主體作為環境公益訴訟的稱謂上等。相關研究可參見呂忠梅:《環境公益訴訟辨析》,載《法商研究》2008年第 6期,第 131-137頁;王小鋼:《為什么環保局不宜做環境公益訴訟原告?》,載《環境保護》2010年第 1期,第 54-55頁;別濤:《中國環境公益訴訟的立法建議》,載《中國地質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 11期,第 4-8頁。。這兩個特征表面上看關系不大,但實際上存在著因果聯系。正是由于學者們一直局限在“是什么”的討論中,缺少對生活世界的體認與把握,導致研究結論的大同小異,其結局是對環境公益訴訟的推進助益甚微②當然,我們不能否認本體性研究的重要性,對于“是什么”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這僅僅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另外,在這種討論中,一個前提預設是只要將“是什么”這一本體性問題研究清楚了,就可以建議立法機關通過立法方式創制環境公益訴訟的法律依據。然后,司法實踐中依據這些規定審判案件,促使環境公益訴訟發揮預期效果。這種思路是值得質疑的,其背后的理念是立法者的理性至上、無所不能,而司法機關只是嚴格適用法律。眾所周知,該種法律理念在經受了廣泛而深入的批判后,已經被現代主流法律思想所超越。若要有效推進我國的環境公益訴訟,必須破除這種“本質主義思維”的影響,在“生成性思維”的指導下展開環境公益訴訟的研究。
(二)“生成性思維”及其對環境公益訴訟研究的啟示
法學研究方法對法律制度研究具有決定性影響,研究方法的創新是法學研究和法律制度創新的第一步。環境公益訴訟的研究現狀之所以令人不滿意,很大程度上也是研究方法陳舊所導致的,因而環境公益訴訟研究呼喚研究方法的創新。筆者以為,“生成性思維”對環境公益訴訟的研究具有重要啟發。
“生成性思維”被認為是現代哲學的基本精神和思維方式。在近代哲學到現代哲學的發展過程中,“本質主義思維”逐漸被“生成性思維”所取代。近代哲學的世界觀是科學主義的世界觀,這種世界觀是以牛頓力學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學哲學化的結果。在這種世界觀下,世界被視為某種外在于人的、與人無關的、可計算的、本質既定的存在,而人只是這個客觀世界的旁觀者。這勢必導致對生活于其中的周圍世界、對人的當下存在狀況和對人的個性的漠不關心。這種世界觀背后是“本質主義思維”,即主張主客二分,在人的世界之外又設置了另外一個世界,從那個獨立自存的實體世界來描繪自己的生存,把那個世界作為生活的理想和生命的價值意義之源,用那個世界作為判明真假信念的標準。達爾文進化論影響下的現代哲學家們反對上述近代科學主義的世界觀及其思維方式,主張人與世界的統一,強調向生活世界的回歸,并走向“生成性思維”。生成性思維具有重過程而非本質、重關系而非實體、重創造而反預定、重個性與差異而反對中心與同一、重具體而反抽象主義等特征[4]。
與上述哲學觀轉向相伴隨,法律思想也隨之發生轉向。法學家開始關注“法的生成”問題,并與“法的創造”③“法的創造”,也可用狹義的“法的創制”、“法的制定”替換,指代那種認為法律僅僅是立法者意志的產物的唯理主義觀點,是與“法的發現”、“法的生成”相對應的概念。相區別。后者是古典自然法學派、分析法學派的代表性觀點或者預設,前者是歷史主義法學派、社會學法學派、經驗主義法學派等現代法學流派所主張的。比如歷史主義法學派代表人物薩維尼認為法是民族精神的體現,法學家只能通過研究發現這些法,而不能創造或者發明法律。自由主義代表人物哈耶克認為社會秩序本質上是一種“自生自發的秩序”,這種秩序中為人們所遵守的規則就是法律,它不是被制定出來的,不是立法的產物,而是在法官的審判活動中生成的。馬克思也一再指出,立法者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發明”法律,而僅僅是在“表述”法律。我國學者認為“法的生成”是法從無到有的發生過程,這個過程中,法還處于潛在狀態;法的生成過程中,法作為一種事物是社會自生的,不是外加的;法的生成過程帶有很大的自發性、自然性。法的生成的根據是社會對法的需要,法的生成機制表現為社會權力機關對糾紛的審理[5]。
上述“生成性思維”以及受此影響而形成的“法的生成理論”對于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建設具有重要的啟示。在大陸法系國家,環境公益訴訟的運行應該有法律依據,關于環境公益訴訟的法律規范集合成為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從“生成性思維”以及“法的生成”角度看,“環境公益訴訟的制度生成”應作為一個獨立的課題。這個制度的生成過程中包含有幾步,第一步是環境秩序出現糾紛,維護環境公益成為一種社會需要;第二步,這種需要會在環境糾紛解決過程 (包括審判活動)中有所體現,特別在審判活動中,能動性的法官通過特定的方式化解這些環境公益糾紛;第三步,這種化解糾紛的方式固定化為社會秩序中解決環境糾紛的那部分規則,這些規則被立法者發現并表述為環境公益訴訟法律規則,集合成為環境公益訴訟法律制度;第四步,這些環境公益訴訟法律制度通過在司法活動中的反復適用,被制度實施者重新加以詮釋而穩定化①這個過程被稱為“再制度化”,參見葛洪義:《論法的生成》,載《法律科學》2003年第 5期,第 65-71頁。。
在上述過程中,以下幾個問題值得注意:第一,環境公益訴訟的立法,只是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生成過程中的一個環節。因而,環境公益訴訟的研究不能僅僅盯住立法環節,僅僅提出立法建議是欠妥當的。第二,應重視并鼓勵環境公益訴訟立法之前進行的司法實踐,特別是那些試驗性的環境公益訴訟案例,并對這些案例進行微觀的分析。第三,環境公益訴訟生成過程具有階段性特征,不可能通過一次環境公益訴訟立法就解決所有問題,相反,環境公益訴訟的立法進程應該步步為營、有序推進。第四,環境公益訴訟立法受多種因素影響,如我國現有法律法規、社會利益關系、政府的法治策略、法律的實施狀況、司法機關的司法狀態、公民的法律意識等等。具體制度設計中,應結合各種因素,進行綜合決策,然后選定恰當的制度生成方法,保證新制度能夠在現有社會土壤與制度基礎上生根發芽,健康成長,最終發揮其應有功能。
環境公益訴訟的制度生成研究包含著豐富的內容,形成了環境公益訴訟研究的新視角。
二、制度生成視角下推進環境公益訴訟的基本態度
法的生成是一個漸進、漫長的過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生成同樣如此。選定推進我國環境公益訴訟的基本態度,是透視環境公益訴訟司法、促進環境公益訴訟立法的前提。從當下中國的情勢看,環境公益訴訟的推進無疑應該堅持漸進、保守的態度,而不能過分強調環境公益訴訟對傳統訴訟以及傳統權力結構的顛覆性。這一結論可以從以下幾方面獲得證成:
第一,在世界范圍內,環境公益訴訟的立法與司法實踐尚處于嘗試階段。公益訴訟被認為是現代型訴訟[6],其產生與發展也是近幾十年的事情。環境公益訴訟作為公益訴訟的一種形態,隨著公益訴訟的發展而發展。美國是環境公益訴訟較為發達的國家,但其發展過程并不穩定,還在遭受各種質疑和挑戰。美國的環境公益訴訟具體表現為公民訴訟,“在聯邦法律層面,《1970年清潔空氣法》是最早規定環境公民訴訟條款的法律,此后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美國聯邦環境法律的立法浪潮中,絕大多數的聯邦環境法律都包含了公民訴訟條款”[7]。但至今為止,美國尚沒有在環境基本法中確立統一的環境公民訴訟條款。并且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之后的環境公民訴訟司法實踐中,關于原告資格的問題,不同時期最高法院的態度也不盡一致。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在塞拉俱樂部訴莫頓案等幾個典型案例中,原告資格相對寬松;而 1990年以來,最高法院開始較為嚴格地限制環境公民訴訟的原告資格,其以魯堅訴野生生物保護者案為代表;但是,在 2000年的地球之友訴雷德勞環境服務公司案中,原告資格出現了新的轉機,最高法院認為原告環境團體享有提起公民訴訟的資格,這表征了原告資格趨向于寬松[8]。在歐洲很多國家,環境公益訴訟也并不廣泛,基本上處于嘗試性階段,尚未大范圍展開。
因而,在世界范圍內,環境公益訴訟還是一個新問題,相關立法與司法實踐并不十分成熟,許多理論與實踐問題尚處于探索之中。在這種背景下,我國的環境公益訴訟也應該在逐漸嘗試中積累經驗,然后在已有經驗的基礎上逐步推進。
第二,環境公益訴訟面臨著極為復雜的利益關系。環境問題利益相關者眾多,在環境保護措施中,綜合考慮各利益主體的利益需要并進行利益衡量是非常必要的,因而環境法律制度的創設過程中必須運用利益分析方法。在環境公益訴訟中的利益關系頗為復雜,涉及環境公益與經濟公益的協調、環境公益與環境私益的協調、環境公益與經濟私益的協調等方面。利益相關者包括政府、政府環境管理部門、污染企業、社會公眾、司法機關等。每個利益主體都有自己的利益取向,都對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產生與發展保持著高度的敏感性。因而,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生成必然要經歷這些利益主體的充分利益博弈,環境公益訴訟的具體規定也是在這些利益主體充分博弈基礎上妥協形成的。制度生成過程中的利益博弈,是十分必要的,應當讓各利益主體的利益需求有充分的表達,最終形成妥協以達成共識。未經利益博弈的法律制度,在法律實施過程中將面臨更多的難題。環境公益訴訟的利益關系復雜,妥協的達成也并非輕而易舉,決定了利益博弈需要長期的時間,因而環境公益訴訟的推進也必然是漸進的。
第三,我國環境法治發展的總體態勢決定了環境公益訴訟的保守性態度。近些年,各學科都進行了三十年發展的反思,環境法學界同樣對環境法治的發展進行了反思。汪勁教授認為,“公權力運行過程中的體制和機制因素是影響和制約環境立法、行政與司法的關鍵因素”[9]。在環境司法領域中,司法獨立已經成為制約環境法治發展的瓶頸。這些問題都說明,環境法治是整體法治的一部分,沒有一個良好的法治環境,環境法即使有優良的法律技術,也不可能獲得令人滿意的效果。從一定意義上講,可以用“法治缺失”來解釋環境法治發展的困境。這意味著,環境法治的發展應該與整體法治的發展相協調,應該以法治環境的改善為中心。環境法律制度與環境司法實踐創新的限度在于不違背法治的基本原則,環境法的理論研究應該尊重現有的法制框架,這是一種相對保守的態度。
環境法治發展的總體態勢,決定了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推進必須采用保守性態度。對于傳統民事訴訟、行政訴訟保持應有的尊重,不輕言“批判、重構”,因為目前法治發展最大的問題不在于公益訴訟,而在于普通訴訟尚不令人滿意,普通訴訟的有序發展應該為第一要務。
基于這一保守性態度,筆者將從司法與立法兩個角度分析環境公益訴訟的制度生成問題。
三、環境公益訴訟的司法推進
在法的生成問題研究中,學者們不約而同地將觀點聚焦于法官的司法審判活動。哈耶克道出法官在法的生成中的作用,“法官的工作乃是在社會對自生自發秩序賴以形成的各種情勢下不斷進行調適的過程中展開的,換言之,法官的工作是這個過程的一部分。法官參與這個進化選擇過程的方式,就是堅決采納那些更有可能與人們的預期相吻合而不相沖突的規則。法官正是通過這種方式變成了這個秩序的一部分。”[10]
而蘇力則對法官活動有更為直觀的表述,揭示了法官活動的微觀層面,“法官以及有關的司法人員,每天都直接面對大量、多變的現實,直接面對活生生的人和事,因此他 (她)更容易發現立法的不當之處、空隙和盲點;由于法定的職能,他(她)又必須作出具體的決定。因而,無論我們在理論上如何論述或規定,實際上生活中的法官都必然要作出一些判斷,調整有關法律,來爭取他(她)認為比較好的結果 (假定法官沒有私心)。在法律沒有規定的地方,一個理想的法官可能根據習慣的做法以及有關的政策性規定或原則以及多年的司法經驗作出實踐理性的決斷,補充那些空白。”[11]這恰恰是對當下環境公益訴訟司法實踐的客觀描述。比如在中華環保聯合會訴江陰港集裝箱有限公司污染案中,無錫中院在調解書中認為“中華環保聯合會作為非盈利的社團組織,依據國家批準的主要職能,為維護生態環境和周邊居民的生活環境有權提起民事公益訴訟”。這種解釋繞開了《民事訴訟法》關于原告資格的規定,而依據社團組織的法定功能肯定了其原告資格。這種論證既沒有明顯違反現有法律規定,又達到了法官的目標,是極為靈活機敏的。在番禺區檢察院訴博朗五金廠案中,法院認為“原告廣州市番禺區人民檢察院作為維護國家、社會公共利益的職能機關是可以向法院提起訴訟的”,采用“模糊戰術”補充了法律的空白。這些實踐經驗都值得仔細分析、體味。
因而,現階段,司法活動中的環境公益訴訟實踐,不僅有利于盡快維護環境公益,還能為環境公益訴訟立法提供經驗基礎。筆者以為,環境公益訴訟的司法推進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種。
(一)發揮環境私益訴訟的公益保護功能
環境私益訴訟包括普通的環境民事訴訟和環境行政訴訟,這些訴訟目的在于為自然人或者法人因環境問題而引起的人身、財產損害提供司法救濟,主要任務是為了維護個體環境私益。然而,環境利益具有公益與私益的交織性特點,侵害環境私益的行為,大多同時也侵害環境公益。特別是在大氣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損害環境私益的情況下,首先是對環境本身構成了損害,然后被污染的環境又造成人們的人身、財產損害。若因此而提起環境私益訴訟,法院則可以對環境公益和環境私益一并保護,從而發揮環境私益訴訟的公益保護功能。正如楊凱法官在對馬長松提起的三起環境關聯訴訟案例的分析中所指出的那樣,法院的“最終處理出現了‘種豆得瓜’的戲劇性結果,在追求環境私益的同時實現了部分環境公益,實際上就是對我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建構開端的最好啟示”[12]。
在我國,通過環境行政私益訴訟以及部分環境民事私益訴訟,都可以起到維護環境公益的作用。通過這種方式維護環境公益,大有可為,關鍵在于法院對環境保護的積極主動性發揮得如何。
第一,在環境行政訴訟中,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與環境公益緊密相連,通過對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護環境公益。比如,施建輝、顧大松訴南京市規劃局案符合行政訴訟的原告資格要求,可以通過此類行政訴訟的審理,起到維護公益的功能。遺憾的是,法院以不歸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管轄為由不予受理。再如,2000年 12月 30日,山東省青島市 300名市民以青島市規劃局批準的在音樂廣場北側建立住宅區破壞了廣場的景觀、侵害了自己的優美環境享受權為由將青島市規劃局告上法庭,法院受理了此案。
第二,在環境侵權民事訴訟中,可以與“損害賠償之訴”一并提起“排除妨害之訴”①該種訴訟形式是侵權責任法上“停止侵害之訴”與“消除危險之訴”的集合。參見王小鋼:《排除危害類公益訴訟理論、制度和實踐》,載《當代法學》2006年第 6期。,它是一種排除妨害型訴訟,是指依法請求已經從事或正在從事污染的侵權行為人停止其侵權行為的訴訟,或者是由于環境侵權行為給他人的人身、財產構成威脅時,受害方依法請求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危險的訴訟。該類訴訟屬于環境侵權民事訴訟,而非環境公益訴訟,但卻可以起到排除危害的目的,從而使環境公益得到有效的維護。因而,此類訴訟具有維護環境公益的潛質。對于公民提起的此類訴訟,司法中應該予以鼓勵。
(二)運用能動司法理念推進環境公益訴訟
2009年,針對新時期人民法院工作面臨的形勢和任務,最高人民法院王勝俊院長在寧夏、河北、江蘇等地調研時肯定了許多法院適當延伸、擴大審判服務領域的做法,明確提出了“能動司法”的理念。自此,“能動司法”成為我國法學理論界一個熱門詞匯,學者紛紛撰文表達自己的觀點。著名法學家、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江必新認為,“能動性是現代司法的基本特征和運作規律。同時,我國社會主義的性質和所處的特殊的歷史階段都決定人民法院的司法應當是能動司法,這也是時代發展對司法的新要求,更是人民對司法的新期待 ”[13]。
許多國家環境公益訴訟的產生與發展,得益于法官在司法審判中司法能動性的發揮。特別是印度的環境公益訴訟制度,便是在法官秉持司法能動理念之下逐步推進的。能動司法與環境公益訴訟之間具有天然的聯系。新近在我國興起的能動司法理念,是推進環境公益訴訟發展的有利契機。運用能動司法理念推進環境公益訴訟,主要通過法律解釋的途徑完成。具體來講,可以通過法律解釋的方式,為環境公益訴訟中法院的受理職能、提起訴訟的原告資格等尋找法律依據。
比如,在我國的一些環境公益訴訟司法實踐中,將檢察機關作為公益代表人,將檢察權與公訴權解釋為包含“公益訴權”,進而賦予了檢察機關環境公益訴訟主體的資格。又如,在貴州省發生的貴州市“兩湖一庫”管理局訴貴州天峰化工有限公司環境污染案,是一起典型的環境公益訴訟。法院認為原告是國家環境資源管理部門,是公益性的事業單位,法院認為其能夠代表環境公益,作為原告提起訴訟。除此之外,上文提到中華環保聯合會訴江陰港集裝箱有限公司案采用了同樣的論證方法,為環境保護社團組織解釋出原告資格。
(三)鼓勵嘗試性環境公益訴訟司法實踐
當前,環境公益訴訟的司法實踐案件正在不斷發生,這些案例主要由檢察機關作為原告,也有國家環境資源管理部門和環保社團。這些案件都是嘗試性的環境公益訴訟司法實踐,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對我國環境公益訴訟的理論與實踐產生了重要影響。同時,也有一些司法機關出臺地方性的規范性文件,比如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07年發布的《關于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環境保護審判庭、清鎮市人民法院環境保護法庭案件受理范圍的規定》、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于 2008年發布的《關于辦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的試行規定》、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與昆明市檢察院于2010年聯合制定的《關于辦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 (試行)》以及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與昆明市檢察院、昆明市公安局于 2010年聯合制定的《關于辦理環境保護刑事案件實行集中管轄的意見 (試行)》。這些規范性文件的出臺,在一定程度上為環境公益訴訟的開展掃清了障礙。
在我國,通過這些環境公益訴訟的“試驗訴訟”進行一段時間的探索,是一種比較保守、穩妥的做法。這一思路符合我國長期以來的“法律經驗主義”。“法律經驗主義”,是著名法學家江平教授提出的,指我國許多的制度的形成,都是“先摸索,有了實踐,當實踐充分了以后,把它上升為法律,成為制度”[14]。這受制于我國具體情況的特殊性。因而,嘗試性的環境公益訴訟司法實踐應當受到肯定和鼓勵。另外,建議最高人民法院可以發布相關典型判例,以指導此類環境公益訴訟的審理,通過指導判例的形式推動環境公益訴訟的發展。
四、環境公益訴訟的立法推進
通過司法途徑推進環境公益訴訟,僅僅是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生成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我國主要沿用大陸法系的法治理念,從長遠看,形成較為穩定的環境公益訴訟制度,也應重視立法環節中的問題。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生成的立法環節,是司法環節的繼續和確定化。基于筆者的考察,本文就環境公益訴訟的立法模式與原告資格選擇兩個最為核心的問題闡述看法。
(一)環境公益訴訟的立法模式
環境公益訴訟的立法模式,是環境公益訴訟立法過程中首先要面對的問題。立法模式的選擇取決于環境公益訴訟的特征:一方面,環境公益訴訟是公益訴訟的組成部分;另一方面,環境公益訴訟是環境公益的迫切需要,相對于其他公益具有特殊性。鑒于此,筆者以為,環境公益訴訟的立法模式既不能排除整體上的公益訴訟立法,還要有自己的特殊考慮。
第一,從公益訴訟整體看,可以將公益訴訟條款寫入《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環境公益訴訟自然可基于公益訴訟條款提起。盡管在訴訟法學界,相關問題研究較多[15],但前景并不樂觀。一方面,國外的此類立法實踐尚不成熟,無可借鑒;另一方面,公益訴訟包含面比較廣,類型眾多,所應采用的程序、條件也比較復雜,若在《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中寫入公益條款,是一項浩大的工程。因而,筆者認為,此種方案應該作為遠期方案。不過,最高人民法院在對法律進行有效力的“司法解釋”中,可以率先引入公益訴訟的條款,這也是一種嘗試性活動。
第二,從環境公益訴訟的特殊性來看,環境問題已經成為當下十分危急的問題,環境公益訴訟的建立也甚為緊要。環境公益訴訟的立法推進可以借鑒美國的環境公民訴訟立法思路在環境保護單行法中率先規定。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至今,美國環境公民訴訟的法律依據是寫在16部環境法律中的。這種方式較為保守,也較為穩妥。在環境問題日趨嚴重的今天,可操作性也較強。
污染防治法中有許多單行法,應逐漸在這些單行法中寫入公益訴訟條款。從而,在特定類別的環境污染案中展開環境公益訴訟,比如,在《水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等單行法中都寫入環境公益訴訟條款。另外,我國《環境保護法》正在迎來一次大的修改,擬將此作為我國的“環境基本法”,在環境基本法中寫入環境公益訴訟條款,也是不少學者的觀點[16]。筆者認為,這種思路既避免了公益訴訟寫入訴訟基本法的難點,又能盡可能包含不同種類的環境公益訴訟類別,是一條穩妥、中庸的途徑,因而也是一條可行選擇。
(二)我國環境公益訴訟立法中原告資格選擇
環境公益訴訟的原告資格選擇,是立法中最為核心、討論最為激烈的問題。在理論建構中,檢察機關、國家環境資源管理部門、環保社團、公民個人,均可以作為原告資格。但是,若結合中國的現實條件,那么,以上幾類主體便成了我國立法中原告資格的“候選”。筆者以為,目前來看,環境公益訴訟的原告資格應視不同類型而分別規定,即排除妨害型環境公益訴訟和生態損害賠償型環境公益訴訟兩種類型。這是根據環境公益訴訟的不同目的、功能而進行的分類。
第一,排除妨害型環境公益訴訟中,檢察機關、環保社團、社區組織可以作為原告。
排除妨害型環境公益訴訟,是指有關主體以預防或者停止對生態環境的損害為目的,而對污染者或者相關行政主體提起的公益訴訟。該類訴訟目的不在于要求行為人賠償生態損害造成的損失,而在于預防或停止對生態環境的損害,要求污染者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或者要求有關行政機關為或不為一定的行政行為。因而,它可以是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也可以是環境行政公益訴訟。
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應將功能拓展到對環境法律實施過程的監督,有權代表國家維護環境公益,行使環境公益訴權,提起環境民事訴訟或者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并且,在我國已經出現的排除妨害型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中,多是由檢察機關提起。如 2003年樂陵市人民檢察院訴樂陵市金鑫化工廠案、2008年海珠區檢察院訴洗水廠水污染案、2010年番禺區檢察院訴博朗五金廠水域污染糾紛案等,都以排除妨害為主要追求。檢察機關提起的環境公益訴訟案是當前環境公益訴訟嘗試性案例的主要部分,已較為成熟,應進一步在立法中予以確認。
環保社團應是依法成立的法人,它具有代表環境公益的資格和能力。環保社團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無論是在英美法系國家,還是在大陸法系國家,都是通例,在司法實踐中,產生了較為積極的影響,并且效果良好。前述中華環保聯合會訴江陰港集裝箱有限公司案作為我國第一例環保社團提起的環境公益訴訟案浮出水面,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受理該案,最后以調解方式結案。該案起到了維護居民生活環境與生態環境的效果,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等機關的高度評價。此案的成功審理,表明環保社團作為環境公益訴訟的原告具有可行性。另外,允許環保社團提起環境公益訴訟,也是對我國社會權力的認可與支持,對于培育我國環保社會力量具有重要推動作用。筆者認為,環保社團,既可以作為排除妨害型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原告,也可以作為排除妨害型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原告。
社區組織包括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物業管理委員會 (業主委員會)等基層自治組織。社區組織作為環境公益訴訟的原告資格,具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社區組織的環境公益訴訟原告資格是以公民個人的環境公益訴訟原告資格為基礎。按照理想狀態,公民個人應當能夠作為原告提起環境公益訴訟,但是,在我國,立法機關、司法機關等擔心賦予公民個人環境公益訴訟原告資格可能會導致濫訴,浪費本來就非常緊張的司法資源。以社區組織作為公民個人的替代,賦予其原告資格,既能避免濫訴的發生,也可以在相當程度上保證公民的環境公益訴權,符合我國的立法與司法現實。另一方面,環境保護的社區治理機制可以作為對政府環境監管機制的補充,還可以激發公眾保護環境的積極性,應當逐漸發揮社區在環境保護中的積極作用。賦予社區組織以環境公益訴訟原告資格,有助于發揮社區環保職能,是一種非常適當且明智的選擇。因而,筆者以為,應當允許社區組織提起排除妨害型環境民事公益訴訟與環境行政公益訴訟。
第二,生態損害賠償型環境公益訴訟中,國家環境資源管理部門、檢察機關可以作為原告。
生態損害賠償型環境公益訴訟,是指在污染者已經因其行為對生態環境造成損害的情況下,由有關機關向法院提起的,要求污染者對其污染行為造成的生態損害承擔一定恢復費用的公益訴訟。該類訴訟的目的在于要求污染者承擔生態損害的賠償責任,因而只能是環境公益民事訴訟,而不可能是環境行政公益訴訟。若該類訴訟勝訴,被告將給付一定數量的生態恢復費用,該費用應當用于恢復、修補生態環境中。
生態損害賠償型環境公益訴訟在我國的海洋環境保護領域已經有了法律依據。我國《海洋環境保護法》第九十條第二款規定:“對破壞海洋生態、海洋水產資源、海洋保護區,給國家造成重大損失的,由依照本法規定行使海洋環境監督管理權的部門代表國家對責任者提出損害賠償要求”。這意味著,在海洋生態環境造成特定損害的情況下,海洋環境監督管理部門可以提起生態損害賠償型環境公益訴訟。這是因為,海洋環境監管部門具有管理職責,對于國家環境利益構成損害的,可以代表國家提起賠償訴訟。“塔斯曼海”油輪海洋環境污染案是該規定的司法實踐之一,取得良好的效果。
筆者認為,上述規定是合理的,在生態損害賠償型環境公益訴訟中,應該將此規定擴展到海洋環境保護之外的其他領域。國家環境資源管理部門,是法律規定的代表國家行使國家環境保護行政權和代表國家行使國家所有權的機關,提起生態損害賠償型環境公益訴訟,應該作為其履行職責的重要形式之一。因而,應賦予國家環境資源管理部門環境公益訴訟的原告資格。事實上,最高人民法院新近出臺的《關于為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務的若干意見》,首次明確支持環保部門有權代表國家提起環境損害賠償訴訟,標志著環保部門作為環境公益訴訟原告主體地位的確立[17]。
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通過司法措施來維護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倘若國家環境資源管理部門在污染者因其污染行為造成生態環境損害的情況下怠于提起生態損害賠償型環境公益訴訟,那么檢察機關有監督的權力。正如有學者的觀點,“檢察機關發現問題時,可以向相應的行政機關反映,由他們采取行動,當行政機關不以回應,或者回應不恰當時,檢察機關才取而代之”[18]。筆者同意上述觀點,檢察機關可以提起生態損害賠償型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但是,這應當是在國家環境資源管理部門怠于提起訴訟的前提下提起的補充性的環境公益訴訟。
除上述兩類主體之外的其他主體,暫時不宜作為生態損害賠償型環境公益訴訟原告,但可以請求、協助國家環境資源管理部門和檢察機關提起環境公益訴訟。此種制度安排,不僅是基于對司法資源合理配置考慮,更是對有關部門環境監管職責的督促。
[1]呂忠梅,[美 ]王立德主編 .環境公益訴訟——中美之比較[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132-143.
[2]See Michael R.Anderson.Individual Rights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India,in Boyle and Anderson(eds.)[M].Human Rights Approaches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Clarendon Press,1996.200.
[3]齊樹潔,李葉丹 .臺灣環境公民訴訟制度述評 [J].臺灣研究集刊,2010,(1):84-94.
[4]李文閣 .生成性思維:現代哲學的思維方式 [J].中國社會科學,2000,(6):45-53.
[5]嚴存生 .法的生成的幾個問題 [J].華東政法學院學報 ,2002,(1):27-32.
[6][日 ]小島武司 .現代型訴訟的意義、性質和特點 [J].西南政法大學學報,1999,(1):116-118.
[7]徐祥民等 .環境公益訴訟研究——以制度建設為中心[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9.153.
[8]鄧一峰 .環境訴訟制度研究[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8.90-92.
[9]汪勁 .中國環境法治三十年:回顧與反思 [J].中國地質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009,(5):3-9.
[10][英 ]弗里德利希·馮·哈耶克 .法律、立法和自由[M].鄧正來譯 .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0.185.
[11]蘇力 .為什么研究中國基層司法制度[J].法商研究,2000,(3):82-92.
[12]楊凱 .從三起關聯訴訟看環境公益訴訟之開端[J].法律適用 ,2010,(2、3):98-102.
[13]江必新 .能動司法:依據、空間和限度 [N].光明日報.2010-02-04(9).
[14]江平 .從法律實用主義到法律理念主義——中國 30年法治進程再思考[EB].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46662.2010-08-09.
[15]江偉,徐繼軍 .將“公益訴訟制度”寫入《民事訴訟法》的若干問題的探討 [J].中國司法,2006,(6):28-33.
[16]王小鋼 .透視環境基本法中的公益訴訟 [J].環境保護 ,2010,(9):32-34.
[17]孫佑海 .推進環境公益訴訟要有新舉措 [J].環境保護 ,2010,(17):8-10.
[18]李摯萍 .中國環境公益訴訟原告主體的優劣分析和順序選擇[J].河北法學,2010,(1):21-25.
(本文責編:潤 澤)
Research on the System Generation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L itigation:Several Recent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L itigation Cases
L I Yi-song,SU Sheng-li
(Law School,Hohai University,Nanjing210098,China)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EPI L)is an effective prescription for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failure,but there exists critical defect in nowadaysChina’s EPI L research.So we should learn from the theoryof generative thinking and law generation when we launch an EPI L research,which lead to gender the system generation research of EPI L.We should also stick to the conservative attitude and progressive ideaswhen we promote the EPI L research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generation. In judicial,the orderly advancement of EPI L should put emphasis on three aspects,which are developing the public interest protection function of private interest litigation,combingwith the idea of active judicial and tentatively judicial practice. In the legislation,we should choose an appropriate EPI L legislation mode and select plaintiff qualification of EPI L from the stereotype angle.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EPI L);generative thinking;system generation;judicial advancement;legislation advancement
D922.6
A
1002-9753(2011)04-0088-09
2010-10-12
2010-12-31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金項目 (09YJC820025)“論生態制度文明的建設路徑”;河海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基金項目(2008420911)“河海大學研究生精品課程建設項目”(2084-H0800303);河海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項目 (2010B18414)“農村環境法制建設的基礎理論探究”。
李義松(1963-),男,教授,博士后,河海大學環境法研究所所長,中國法學會環境資源法學研究會教學研究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法學會環境資源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研究方向:環境法、法理學。